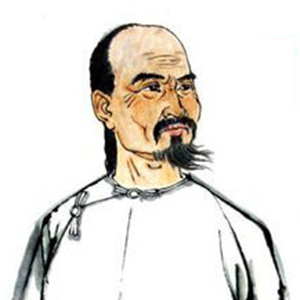这首小令前三句点明主旨,分别从空间和时间,极言家乡路途遥远。中间三句皆是作者的眼前之景,无不映照着他那颗伤感的旅人之心。最后两句写各种声音交织一起化作离愁,致使作者一夜无眠。全曲缠绵悱恻,呜咽低回,读来令人哀愁如缕,感叹不已。
“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小令开篇即直写故乡的遥远和行旅的孤寂,从而引出第三句“倚篷窗自叹飘泊命”的深沉喟叹,“城头鼓声,江心窗声,山顶钟声”三句,表面上全是写景,然一片孤寂烦闷之情,却寓于这“鼓声”、“窗声”、“钟声”之中。这是一种以动写静的手法,独自一人在孤舟之中,又是夜深的江上,孤独寂寞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静极时,便越发显得这“鼓声”、“窗声”、“钟声”的响亮。反过来,这声音也越发显得夜深江上的寂静。此情此景搅起了游子的无限身世之感与思乡之情,以至再也按捺不住这一腔愁绪,便冲口而出“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全篇寓情于景,以景衬情,渲染寂寞悲凉的气氛,表达了失意惆怅的情怀。四、五、六三句,语气平淡而意蕴隽永。“城头鼓声”,暗示时光流逝,使人易生光阴蹉跎的感慨,“江心窗声”,象征人生旅途的险恶,使人感发“世途风波恶,人间行路难”的浩叹;“山顶钟声”,则显然和唐代诗人张继所听到的寒山寺夜半钟鸣一样,使人深感客中的凄凉和惆怅。这三种声音,构成一部情调悲凉的交响乐章,发人遐想。另外,曲词的语言朴实而凝炼,工整而有节奏感。
古诗中反映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的《观刈麦》、张籍《野老歌》、皮日休《橡媪叹》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打麦》不落窠臼,内容更丰富,艺术上颇多创造。
这首诗集中抒写了农民的终生劳苦,流露出强烈的恤民情怀,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懑。全诗可分为两段,从开头到“敢惮头枯面焦黑”为上段:
“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在北。”诗名“打麦”,开头就直承题意。但不是正面描写农民劳动场面,而是用相互回应的一片打麦声,侧面取影,写出了紧张艰苦的工作情景。接着作者撇开打麦,蓦然跳跃到打麦以前的收割。“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这里用夸张手法描写麦子成熟之速,目的是突出麦收的刻不容缓,渲染了农民抢收的紧迫性。“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鹖旦夜鸣催人,风雨将至,不抢收则颗粒无获。这两句进一步渲染出抢收的紧张气氛,引出下面对收麦的正面描写:“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只写妇女,实际上却已包括丁壮,笔墨简洁。捋青随即成束,既写出田家动作的熟练、紧凑,也写出神情的亢奋、紧张。白居易《观刈麦》说“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与之相比,此诗抓住了收麦场面中的特定动作,刻画更为准确。“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把农民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夜无安眠,朝无少息,劳作很辛苦,但农民却以苦为乐。这里面有面对劳动果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年成尚好,虽然所得无几,但不至于饿死道旁。这是凄楚的喜悦,辛酸的微笑。
这段通过对收麦环境、劳动场面和农民心理的描写,充分反映了田家生计的艰辛。
下一段从“贵人荐庙已尝新”到结束,由回顾收麦跳跃到展望食麦。“贵入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荐庙即献于家庙作祭品,醴是甜酒。贵人们雍容尝新,饱食有余,和田家的不曾入口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出耕者不食,食者不耕的对立。“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不耕者饱食却还有余,力耕者无食被迫售粮,田家的饥馁不言而喻,两者的对比又深入了一层。
麦秋结束,劳作未歇,诗人构思又跳跃到打麦后的插禾:“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这里写插禾只是一笔带过,不再作具体描写,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打麦和插禾,虽然一为农事之末,一为农事之始,但贯穿始末的是送不走的“辛苦”二字。田家的辛苦又要随着插禾周而复始了。结尾结而不断,首尾相衔,内涵丰富。
张舜民一贯重视民生疾苦,《画墁集》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而此篇尤为突出。诗中强调了农民的终生劳苦,内容比前人开拓得更广。
此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诗题说“打麦”,却忽而收麦、忽而食麦、忽而插禾,以打麦为联系中心,结构跳跃动荡,又有章法可寻,对主题的表现有重大作用。
由于作者热悉农村生活,因此在描写农村环境及劳动场面时,形象真实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描写贵人神态,着墨无多,却十分传神。两种形象的对比,互相映衬,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诗中使用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参差,自由洒脱,避免板滞,很有乐府风味。诗中换韵三次,平仄交押,仄声的短促峭急,突出了农民的劳苦;平声的悠长平和,刻画了贵人的雍容自得。
整篇诗不用典实,不用生僻字,质朴平易,任情而往,在宋诗中颇具特色。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