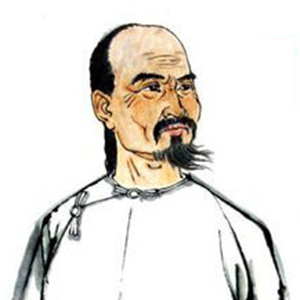《野歌》在李贺的诗作中别具一格。诗的开头两句:“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表象地看是写仰天射鸿的高超射技,实际上是借此喻指诗人凭借出众才华来到京都准备在应举考试中摘冠折桂。其中“弓”、“箭”喻指诗人的文学才华,诗人要仰望的天街是京都,诗人要射落的“鸿”是要折桂中举。诗人以形象化的比喻描绘出自己的理想宏愿。事实上,凭着令位尊名重的文学家韩愈大为赏识的文学才华,诗人要应试中举犹如“仰天射落衔芦鸿”一般,容易得手。可正在诗人踌躇满志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嫉妒诗人才华的举子,对他进行诽谤,说他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同音,他应当避父亲的名讳,不该参加礼部的考试,甚至有人攻击他“轻薄”。这一意外的打击使诗人无缘中举,只得懊恼地回到家乡。
诗的三、四句“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正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排解郁结在心头的苦闷与悲愤的一种方式。一方面,遭谗落第,仕途受阻,诗人自然会产生沮丧、懊恼、悲怆之情,诗人自然会有不遇之感,有愤懑要发抒。另一方面,此时的诗人虽遭受意外的人生挫折,但内心依然充盈着入仕的锐气,期望冲破困境,寻求光明未来。所以,他很快从颓唐中振作起来,如同在《开愁歌》中以“临岐击剑”、解衣贳酒、“壶中唤天”的狂放方式抒发仕进受阻的激愤一样,诗人以肥衣冲风、带酒晚歌的洒脱方式表达对嫉妒、诽谤自己的可恶小人和听信谗言、草率取士的礼部考官的极大愤慨。应该说,中举的期望值越高,希望越大,落第的打击会越大,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成的愤慨也就越强烈。诗人这种特有的洒脱方式正是内心强烈愤慨的自然渲泄。不唯如此,“麻衣黑肥冲北风”中的“黑”与“北”二字也值得特别关注。“黑”字隐约给了诗人一种环境过于压抑和阴森的感觉,“北”风让诗人敏感于世风的炎凉,人情的冷漠。置身于如此压抑和阴森的社会环境,面对如此炎凉的世风、冷漠的人情,诗人依然肥衣冲风、饮酒高歌,其感情何其沉郁愤激,其气概何其慷慨豪迈!如此开怀畅饮,长时间纵情高歌,一个豪放、洒脱的诗人形象便宛然如立眼前。
诗的五、六句“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是诗人不甘沉沦的自勉。尽管自己落第与别人折桂的不同遭遇(“枯荣不等”)令人沮丧、懊恼,造成这种不公平命运的礼部考官(“天公”)理当受到责怪,然而诗人相信总有一天会“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挐云”(《致酒行》)。在他心目中,严冬过后终将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蒙蒙。”他能够乐观自信地在困境中唱出“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的诗句,迸发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呼声。正因为诗人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他在遭谗落第回到家乡的同年秋天(元和三年九、十月间)再次来到洛阳寻求政治出路,冬天西去长安求仕,第二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春天谋取了奉礼郎一职,当上了从九品上的小京官,终于开始了他并不适意的政治生涯。
整首诗扣题叙事,前四句叙事,后四句抒怀。因事抒怀,叙事抒怀,紧密关联。叙事之中有援箭引弓、仰天射鸿、肥衣冲风、饮酒高歌的形象描写,有箭飞弦响、大雁哀鸣、北风呼啸、诗人高歌繁多声响的奏鸣渲染。抒怀之时有感叹不遇、不甘沉沦的内心表白,有寒风变春柳、枯柳笼轻烟的艺术遐思。叙事之中以形象的描写、声响的渲染抒泄身受压抑、才志不得伸展的强烈愤激,抒怀之时以内心的独白、艺术的遐思表达出乐观、自勉之情。愤激之中呈现出狂放、豪迈、洒脱的形象,自勉之时犹见积极用世、奋发有为之志。这样,诗人受压抑但并不沉沦,虽愤激犹能自勉的情怀充溢在诗的字里行间,让人读来为之欣慰和感奋。
此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草堂诗余别集》、《古今词综》等都题作“离情”,而《草堂诗余别集》还注云:“一作春怀”。由此看来,这些恐均非原题,是后人据词作内容添加的;此外,“春怀”与“离情”确也概括了词作的主要内容。从词作的内容与风格来看,这首词当写于词人婚后不久,夫妻小别,李清照独居时。
“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开首三句,词人放眼室外,由春景落笔。但见初春时节,春风化雨,和暖怡人,大地复苏,嫩柳初长,如媚眼微开,艳梅盛开,似香腮红透,到处是一派春日融融的景象。词人前期生活虽然没有大的波折,但以其独具的才情、细腻的情感,以及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悟、强烈的关注,常有出人意表之想。表现在词作里,就是经常慧心独照,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暖日晴风”似还不足以表达春天到来的特征,而紧接以“柳眼梅腮”(此句历来被称为“易安奇句”),则使到来的春天更直接、更形象。李商隐在《二月二日》一诗中有“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苏轼在《水龙吟》词中描绘柳叶情状是“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看来女词人受此启发,抓住两个极具特点的事物,写出春天的生机。第三句的“已觉春心动”,从语意上看,是对春天来临总的概括,实亦是自己怀春之情已动之流露。词人游春、赏春,目睹良辰美景,必有所思,这句也暗启后二句词人所抒发的情思:“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女词人的细腻、敏感的思绪与感悟进一步强化,面对如此大好春光,自然便联想到自己独处深闺,孤栖寂寞,这与往日和丈夫赵明诚一齐把玩金石,烹茗煮酒,赏析诗文的温馨气氛形成强烈反差。一个“谁与共”,道出此刻词人内心的苦涩。紧接着词人用一个细节来进一步形容自己内心的苦涩,泪水流淌,脸庞上的香粉为之消融,心情沉重以致觉得头上戴的花钿也是沉甸甸的。
词作的下片,词人以细微的笔触,紧承上片末句,着重刻画自己具体的闺中寂寞生活。“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春暖天晴,春装初试,然而词人却足不出户,去观赏那美好的春景,却斜倚在山枕上,以致把精美的钗头凤给压坏了。“山枕”,即檀枕,因其如“凹”形,故称山枕。词人不出户观赏春景,是因怕良辰美景触引伤感之情,二是表明其心境郁闷,慵懒至极。一个“斜”字,也暗示词人慵懒、无精打采。末二句:“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愁本无形,却言“抱”,可见此愁对其来说有多“浓”,多重,更何况是“独抱”,此情更是难堪。“无好梦”,是说现实很寂寞无聊,想在梦中去寻求慰藉,但却始终无法进入梦乡,直至夜阑人静之时,仍剪弄灯花,以排遣愁怀。“犹”字写活了词人百无聊赖的情态。此外,剪弄灯火,古时妇女常藉以卜数夫君之归期。这两句写得极为细致、生动,看似毫不经意,如叙写生活本身,实是几经苦炼,没有生活经历和深厚的艺术功力是无法写就的。清词论家贺裳评这两句为“入神之句”(《皱水轩词筌》)。
全词从白天写到夜晚,刻画出一位热爱生活、向往幸福、刻骨铭心地思念丈夫的思妇形象。
这首诗从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时间与空间的对照来表现今昔之感,并以冷静幽远的笔墨,抒怀“弃官归乡、淡于名利”的归隐之志。全诗用典自然,对仗工整,境界辽阔,感情激荡。
首联破题,从山河形胜落笔。赤壁扼守着通往荆州和襄阳垒的道路,因而成了古代兵家争战之地,三国时修筑的战争营垒依稀可辨,山川依然,地形奇险。“故垒”自然是用了苏轼“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的名句。这两句虽为写地理,但“依然”、“故垒”等词已引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
颔联则巧妙地运用了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和苏轼《念奴娇》中“大江东垒,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句子,貌似写景,其实隐寓曹操在此兵败而周瑜得胜成为英雄的历史画卷。“乌鹊南飞”和“大江东垒”是万古如斯的自然景象,但在作者笔下借用了典故的联想而各自带上了丰富的意蕴,而且对仗工巧,绝垒斧凿之浪,可见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
颈联则以时间和地理自然成对。孙权、刘备、周瑜、曹操这些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流传千年,赤壁一战奠定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眼前的山河即是当年历尽无数战斗的地方。出句是缅怀历史,对句是即目所见;表现古今时代的纵贯,山河遗迹的感喟,于真自然过渡到尾联的自我抒怀。
此日经过赤壁,多少英雄已成陈迹,只有在明月照耀的江上,时时传来渔翁的晚唱。“唱沧浪”云云自然是用了《孟子》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意思。与萧散自在的渔父相比,那些在政治上曾一度风云显赫的人们也显得可怜可叹了。结尾这两句不仅与前六句的宏阔气象形成一鲜明对照,以冷静幽远的笔墨结束全诗,令诗意波折,更具回味;同时也与诗人此时弃官归乡、淡于名利的心境暗合,从而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