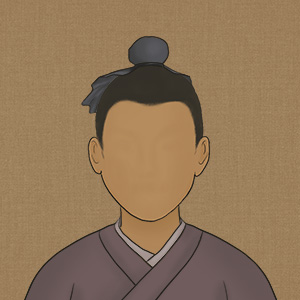此诗为寓言诗,写雌雄双燕历尽艰险,生死不渝的“爱情”。一对恩爱燕子相依相伴,快乐幸福,不料一场大火降临,雄燕不幸身亡,雌燕憔悴伤心,回旋不去,非常伤感,凄切而动人。此诗用以寄寓人类爱情之忠贞。“令人羡”为全诗之眼,是联系人与燕的纽带。
李白这首乐府取材比较随意,虽然提到“柏梁”、“吴王宫”,但都是信手拈来,并无所指。时序也是错乱的。按“柏梁失火去,因入吴王宫”语意,似乎先有西汉柏梁殿失火,后有春秋吴王宫焚烧,其实西汉在春秋之后。可见这首乐府是随意而写,可能是李白应景之作,并非有感而发,因此在艺术上少有可圈可点之处。
第一句的散文结构是:一个被放逐之臣,从猿啼声中一路南去。“逐臣”是主语,“过”是动词。“猿声”是宾语的精简,概括了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过的是巴东三峡,这个“客”过的是湘西五溪。有人说,诗句不讲语法,这是错的。诗句也有一定的语法,不过它和散文不同,为了平仄、对仗或押韵的方便,它的语法结构可以有极大程度的变易,甚至往往连动词也省掉。读诗的人,仍然应该从语法观点去推求作者的造句艺术。
第二句“回看”二字是照应上句的“过”字,这个被降谪的官员,愈走愈远,深入五溪苗家所住的区域,就不免常常回头看看来路。来路上只是一片秋草,早已望不到家乡,于是不禁泪落沾巾。下面二句说,这一段旅程尽是在寒天、暮雨、不见人迹的空山中。夜晚了,总是在苗家歇宿。“蛮”是古代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当时少数民族所住的地区,都是荒野的山区,故有“蛮荒”之称。作者设想这个“客”深入蛮荒,以蛮家为逆旅主人,是最不幸的遭遇。湘西的秋雨是整天整夜连绵不绝的,为什么作者偏说是暮雨呢?这是为了与下句挂钩,引出此“客”在暮雨中向苗家借宿的诗意。吴山民评此诗曰:“一诗酸楚,为蛮、主二字挑出。”即以为此诗末句写出了贬官的酸楚之情。这是古代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今天我们读此诗,就不会和古人有同感了。住在兄弟民族的家里,有什么可酸楚的呢?
韩翃所作七言绝句不多,但大多是佳作,胡应麟最称赏韩翃的七绝,他在《诗薮》内篇中举出“青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急管昼催平乐洒,春衣夜宿杜陵花”、“晓月暂飞千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等五六联,以为是“全首高华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陈妙语,行以唐调耳”。他又举出“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万木中”、“寒天暮雨空山里,几处蛮家是主人”这二联,以为“自是钱、刘格,虽众所共称,非其至也”。这一段评论,反映出胡应麟所喜爱的是秾丽的句子。骨子里仍是梁陈宫体,风格却是唐诗。这种诗句之所以“非初非盛”,因为初唐则还没有唐调,盛唐则已排除宫体。而在中唐诗人,渐渐地又在唐调中纳入宫体诗的题材,成为一种秾艳的律诗。这个倾向,发展到晚唐的李商隐,温飞卿而达到了极度。至于“柴门流水”、“寒天暮雨”这样的句子,还是清淡一派,属于钱起、郎士元的家数,而且还不是其中最好的,所以胡应麟似乎不很喜欢。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前四句自比李杜。韩少孟十七岁。孟诗多寒苦遭遇,用字造句力避平庸浅俗,追求瘦硬。与贾岛齐名,故有“郊寒岛瘦”之称。韩诗较孟粗放,所以以韩比李,以孟比杜。这里虽未出现“留”字,但紧紧扣住了诗题《醉留东野》中的“留”字,深厚友情自然流露,感人至深。
五至八句对二人的处境现状和性格作了比较。“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诗人在过去的诗中曾以“雄骜”二字评东野,即说他孤忠耿介,傲骨铮铮。“白首夸龙钟”,一“夸”字即写“雄骜”。紧接着韩愈写自己,“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韩承认自己有点“滑头”,比起孟来有时不那么老实,所以能周旋于官场。在东野这株郁郁高松面前,自惭有如青蒿。意思是说,我今在幕中任职,不过依仗一点小聪明,比起孟郊的才能,实在是自愧弗如。
最后一段,祝愿二人友谊长存。我十分崇拜孟郊,我愿做驱蛩,负孟避祸。孟郊这样做下去,我和孟郊的才能相差悬殊,犹如“寸莛撞钜钟”。我愿变为云,孟郊变为龙,世间虽然有离别的事,但我们二人如云龙相随,永不分离。
本诗以“醉”言出之,肆口道来,设想奇僻,幽默风趣;开篇即表示对李、杜的向往,既表达了与友人惜别之情,又可看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与自信。
全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多次用典丰富而含蓄地表达对孟郊的推崇,如《易经·乾卦·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希望自己和孟郊变为云和龙。同时作者借“醉酒”用“夸龙钟”与“稍奸黠”形容孟郊与自己,足见两人感情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