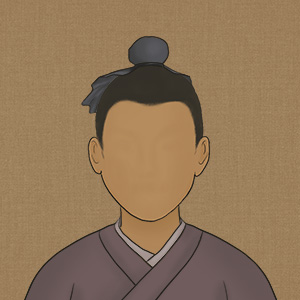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诗中的“粤人国”,本指广东,因秦末赵佗曾建南越国,封为南越王。赵鼎曾被贬至潮州,因此此处“粤人国”应指潮州。赵鼎在潮州五年,即绍兴十至十四年(1140-1144),至潮州时是绍兴十年闰六月,故此诗应为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所写。
此诗虽题为《寒食》,但写的是从寒食到清明。前两联写的是当时民间风俗。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记其时江南风俗:“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成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曲幽,亦青青可爱。……从人家上冢者……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冢者尤多”从此诗可得知,南宋时潮州民间在寒食节也有插柳的习俗,即使偏僻村落也不例外,只是没有禁烟寒食,而清明节却像东汉末襄阳隐士庞德公一样携带女儿上山扫墓(即“上冢”)。
后两联在记事中寄寓抒情。颈联写所见:汉唐帝王的陵墓连粗粝的麦饭也没有人祭拜,而山溪野径之间开满梨花。尾联写所感所闻:我还是开怀畅饮吧,醉后卧倒在青苔之上,不必去管城头上傍晚吹起的军号。
通过清明郊游,作者悟得了不少哲理:权贵、富贵不过是短暂的、无常的,而人间确实永恒的、常新的。我还是得醉且醉吧,天下世事我不能管,也不必去管。这种心态看似消极,但却是作者当时处于贬谪逆境中的苦闷、痛楚心情的反应。
其实,赵鼎是不屈的。他在由潮州移吉阳军的谢表中曾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说:“此老倔强犹昔!”(《宋史》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