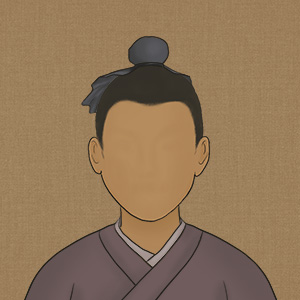这首诗首句写诗人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遇到能休息的地方便休息;次句写江水中的白珋已经消失了,水波粼粼,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后两句即景抒怀,三句自称不是逢秋就会伤感的一般文人;末句采用拟人的手法,写听凭傍晚的秋山相对发愁。诗写得富有韵味,显示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气质。
诗的起笔突兀,一开始就指出:不论是南去北来,还是北去南来,诗人总是想去就去,想休息就休息,无优无虑,恬然适意。诗的第二句紧承首句写道:“白蘋吹尽楚江秋。”诗人象是回答说,正是在萧萧秋风把白蘋都吹落了的深秋季节才如此这般说来。他身处秋气潇杀、万物凋零的深秋季节,丝毫没有悲哀凄凉的感觉,反而无优无愁,安然处之。本来,诗人得休便休已经够洒脱了,再有后一句萧瑟景象的衬托,就更显示出超尘脱俗的气质。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悲秋”的传统。一到秋天,西风瑟瑟、枯叶飘零,这萧条凄清的景象极易引发诗人对不如意的人生大兴悲叹之辞。早在战国时期,楚人宋玉作《九辩》,第一句就叹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而此诗作者能如此逢秋而不悲,随遇而安、怡然自得。诗的前两句在叙述诗人不寻常的举止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问号。
诗的三、四句紧扣首二句之意、“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在这里,诗人以道人自比,表现出诗人对闲适味道。飘逸、淡泊无求境界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能够“南去北来休便休”,就是因为他不是见秋生悲的“悲秋客”,而是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道人。因此,当众人对秋生悲时,诗人自然无悲可言,“一任晚山相对愁”。此时,作者远远望去,楚江两岸的山脉凄清寥落,像是在飒飒秋风中相对发愁。晚山本来不会悲愁,在超脱淡泊的道人看来,晚山也不会悲愁。只有在悲秋人眼里,晚山连同周围的一切才看上去象是都在悲叹哀伤。在此,诗人没有直接去写愁容满面的“悲秋客”,而是通过“悲秋客”眼里所看到的秋暮中凄凉悲伤的景物来写“悲秋客”,这样写,更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的潇洒飘逸。
程颢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他这首诗就有些谈禅(佛教道理)的味道。但诗人并不是真的那么旷达,真的能超凡脱俗。其实他写要“休便休”,恰恰说明他对“南去北来”已经感到疲倦,渴望守着家人过宁静安逸的生活;他写“白蘋吹尽楚江秋”,可见他对秋天的到来是敏感的;他写“晚山相对愁”,恰恰反映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愁。所以欣赏诗歌,既要看诗歌中的议论,更要看诗歌中所描写的形象。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