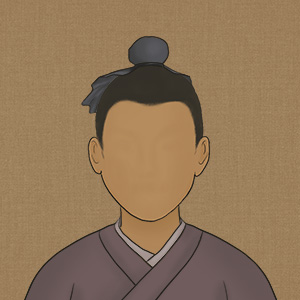《行路难》为乐府旧题,古辞不存。《乐府解题》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续晋阳秋》说:“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行路难》词多悲哀之音。
此诗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四句为第一层,写游子思妇,两个方面同时着笔,而以秋夜闻雁声贯串。以孤雁哀鸣写游子思妇,这是古诗中常用的手法。如曹丕《杂诗》:“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又说:“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此诗颇有化用曹诗的地方,而曹诗又是从借鉴《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来。诗的首句以“君不见”起,是《行路难》乐府题的常格。从孤雁发于“关外”,远度“扬越”,由北而南,知此时正是深秋节令。“孤雁”一语虽已成为这类题材的凝固意念,但它对游子或思妇说来,仍是一种心理反射。而“酸嘶”与之呼应,也是从人即游子、思妇的感受说起。第三句“空城客子心肠断”,第四句“幽闺思妇气欲绝”,都从夜闻“孤雁”而来;一个“心肠断”,一个“气欲绝”,一种相思,两处相关,而雁声则为传情之物。
以下两层分写思妇、游子。第五句至第十句写思妇。思妇因怀人夜不能寐,一个人孤独地在庭前踱着步,不知不觉,已过了深夜。忽然低头看见罗衣上已结满霜华,便用衣袖轻轻拂了几下,可是仍无意回房。她抬眼望望天空,许久天上连一颗星星也看不见,这工夫却见浮云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轮满月,洒下遍地清辉。人说月圆是亲人团聚的吉兆,以前她自己也总是盼望月圆时,可是月亮一次次圆了又缺了,征人却始终未归;多少年过去了,“夜夜遥遥徒相思”。尽管如此,思妇的一片痴情终不歇。“望望”,是望了又望,望了又望,望穿双眼。此篇写思妇怀人之苦,情境、意蕴并没有什么特别。它与传统不同的地方,在于表现技巧。如《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其意象有某种集合性,其表情方式也基本是直接抒发,不假缘饰。此篇则有所不同。其情感则是从景物的变化及人的具体行为中见出。此种情况,以“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为特著。这样不仅形象鲜明,而且更含蓄蕴藉。第九句和第十句“寄我匣中青铜镜,倩人为君除白发”,更显得情意深长。青铜镜在匣中珍藏多年,本是为待游子的归来,可是游子总不见归来,这青铜镜留在匣中就没有什么作用。青铜镜本是为照青鬓朱颜,可如今,他大约已添了白发了,于是想到寄镜。不言悲凉之意,自是悲从中来。“倩人为君除白发”,表现思妇对游子的体谅之情,细意委曲。这两句诗意紧扣上句的“情不歇”三字。
第十一句至第十四句为第三层,写游子。“行路难”三字,用乐府点题之法;重复之,加重感情的抒发。“行路难,行路难”,如一声声悲怆的叹息。以下二句是“行路难”一语的落脚点。“夜闻”“汉使度”,表明游子流落胡中。因多年羁留异国他乡不得回归故土,闻汉使而遽兴故国之悲思。结尾句著“忆长安”一语,与第二层呼应,以见出两情如一,上扣第一层闻鸿“肠断”、“气绝”。
《行路难》为乐府旧题,古辞不存。《乐府解题》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续晋阳秋》说:“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行路难》词多悲哀之音。
此诗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四句为第一层,写游子思妇,两个方面同时着笔,而以秋夜闻雁声贯串。以孤雁哀鸣写游子思妇,这是古诗中常用的手法。如曹丕《杂诗》:“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又说:“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此诗颇有化用曹诗的地方,而曹诗又是从借鉴《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来。诗的首句以“君不见”起,是《行路难》乐府题的常格。从孤雁发于“关外”,远度“扬越”,由北而南,知此时正是深秋节令。“孤雁”一语虽已成为这类题材的凝固意念,但它对游子或思妇说来,仍是一种心理反射。而“酸嘶”与之呼应,也是从人即游子、思妇的感受说起。第三句“空城客子心肠断”,第四句“幽闺思妇气欲绝”,都从夜闻“孤雁”而来;一个“心肠断”,一个“气欲绝”,一种相思,两处相关,而雁声则为传情之物。
以下两层分写思妇、游子。第五句至第十句写思妇。思妇因怀人夜不能寐,一个人孤独地在庭前踱着步,不知不觉,已过了深夜。忽然低头看见罗衣上已结满霜华,便用衣袖轻轻拂了几下,可是仍无意回房。她抬眼望望天空,许久天上连一颗星星也看不见,这工夫却见浮云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轮满月,洒下遍地清辉。人说月圆是亲人团聚的吉兆,以前她自己也总是盼望月圆时,可是月亮一次次圆了又缺了,征人却始终未归;多少年过去了,“夜夜遥遥徒相思”。尽管如此,思妇的一片痴情终不歇。“望望”,是望了又望,望了又望,望穿双眼。此篇写思妇怀人之苦,情境、意蕴并没有什么特别。它与传统不同的地方,在于表现技巧。如《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其意象有某种集合性,其表情方式也基本是直接抒发,不假缘饰。此篇则有所不同。其情感则是从景物的变化及人的具体行为中见出。此种情况,以“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为特著。这样不仅形象鲜明,而且更含蓄蕴藉。第九句和第十句“寄我匣中青铜镜,倩人为君除白发”,更显得情意深长。青铜镜在匣中珍藏多年,本是为待游子的归来,可是游子总不见归来,这青铜镜留在匣中就没有什么作用。青铜镜本是为照青鬓朱颜,可如今,他大约已添了白发了,于是想到寄镜。不言悲凉之意,自是悲从中来。“倩人为君除白发”,表现思妇对游子的体谅之情,细意委曲。这两句诗意紧扣上句的“情不歇”三字。
第十一句至第十四句为第三层,写游子。“行路难”三字,用乐府点题之法;重复之,加重感情的抒发。“行路难,行路难”,如一声声悲怆的叹息。以下二句是“行路难”一语的落脚点。“夜闻”“汉使度”,表明游子流落胡中。因多年羁留异国他乡不得回归故土,闻汉使而遽兴故国之悲思。结尾句著“忆长安”一语,与第二层呼应,以见出两情如一,上扣第一层闻鸿“肠断”、“气绝”。
据晚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述,刘采春是中唐时的一位女伶,擅长演唐代流行的参军戏。元稹曾有一首《赠刘采春》诗,赞美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就是《啰唝曲》。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九《乐曲》云:“啰唝犹来罗。”“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据说,“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可见当时此曲歌唱和流行的情况。
《全唐诗》录《啰唝曲六首》,以刘采春为作者。此曲在佳作如林的唐代诗坛上赢得了诗评家的推重。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中说:“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绪之‘打起黄莺儿’……刘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嘉运所进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寄意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更称此曲为“天下之奇作”。这类当时民间流行的小唱,在文人诗篇之外,确实另有风貌,一帜别树,以浓厚的民间气息,给人以新奇之感。其写作特色是:直叙其事,直表其意,直抒其情,在语言上脱口而出,不事雕琢,在手法上纯用白描,全无烘托,而自饶姿韵,风味可掬,有司空图《诗品》所说的“不取诸邻”、“着手成春”之妙。“那年离别日”是这组诗的第四首。
这首诗写夫婿逐利而去,行踪无定。张潮有首《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所写情事,与这首诗所写有相似之处。“朝朝江口望”,一心望夫婿归来,而不料愈行愈远。这正是望而终于失望的原因,正是每次盼到船来以为是夫婿的归船、却总是空欢喜一场的原因。正如李鍈在《诗法易简录》中所分析:“桐庐已无归期。今在广州,去家益远,归期益无日矣。只淡淡叙事,而深情无尽。”长期分离,已经够痛苦了;加上归期难卜,就更痛苦;再加以行踪无定,愈行愈远,是痛苦上又加痛苦。在这情况下,诗中人只有空闺长守,一任流年似水,青春空负,因而接着在下一首诗中不禁发出“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的近乎绝望的悲叹了。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达,嫁作商人妇的少女越来越多,因而有《啰唝曲》之类的作品出现,而闺妇、行人之所以听到此曲“莫不涟泣”,正因为它写的是一个有社会意义的题材,写出了商人家庭的矛盾和苦闷。
中唐宰相权德舆有诗《八月十五日夜瑶台寺对月绝句》:“嬴女乘鸾已上天,仁祠空在鼎湖边。凉风遥夜清秋半,一望金波照粉田。”据宋·宋敏求《长安志图》所绘的唐太宗昭陵图,在陵域范围之内,有“瑶台寺”、“广济寺”、“澄心寺”、“百城寺”、“舍卫寺”、“升平寺”、“证圣寺”、“宝国寺”等。又据《金石萃编》记载:“瑶台寺,则《昭陵图》有之,在昭陵之西、澄心寺之南也。”据今考古,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处。此诗当是权德舆于昭陵所写。查其诗中之意,则与某位公主有关。
“嬴女乘鸾已上天”。“赢女”,指秦穆公之女弄玉。萧史教弄玉吹箫引凤,后来二人乘凤鸟而去。此句以弄玉成仙比喻公主去世。
“仁祠空在鼎湖边”。“仁祠”,明·杨慎《艺林伐山·仙陀》:“佛寺曰仙陀,又曰仁祠。”在此当指瑶台寺。“鼎湖”,本为古代传说黄帝乘龙升天处,后借指帝王。如清·吴伟业《圆圆曲》“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此句指公主死后,空留下瑶台寺在唐太宗的昭陵旁边。
“凉风遥夜清秋半”。此句扣题,点明写诗之时是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月夜。
“一望金波照粉田”。“金波”,月光。“粉田”,脂粉田,即公主的汤沐邑。此句再次点明季节,及瑶台寺与公主的关系。
全诗大意:公主不幸去世了,只留下瑶台寺还在昭陵旁边。今天晚上正值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清秋月夜,明亮的月光照着这座用公主的汤沐所得造的寺庙
那么,此诗中提到的公主是谁呢?
此诗既然写于昭陵,则公主当是唐太宗的姐妹或者女儿。查《新唐书·公主传》,唐太宗的姐妹与女儿中,葬地与佛寺有关者有二:一、比景公主,始封巴陵……显庆中追赠,立庙于墓,四时祭以少牢。二、晋阳公主……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又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第五百九十三,《唐瑶台寺碑》:许敬宗撰,诸葛思祯正书。贞观十八年。”则至迟到贞观十八年,瑶台寺就已经存在,则此庙与比景公主无关。再据《新唐书·公主传》,“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与“粉田”之意正合,则晋阳公主的葬地极可能就在瑶台寺附近。
当然,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算是很外围了,比起同母姐妹们,离昭陵主峰似乎太远,不符合晋阳的身份。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当时认为女子未及笄而亡的有戾气,不能葬在家族墓地,只能葬在佛寺中,用佛法化解戾气。所以二凤在昭陵边修佛寺,并且把小犀牛葬在那里,其实已经是在打擦边球,没办法再近了。
这首诗是吊古怀乡之佳作。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泛览眼前景物,即景而生情,诗兴大作,脱口而出,一泻千里。既自然宏丽,又饶有风骨。诗虽不协律,但音节浏亮而不拗口。真是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传说李白登此楼,目睹此诗,大为折服。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严沧浪也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此为第一。足见诗贵自然,纵使格律诗也无不如此。历代写黄鹤楼的诗很多,但崔颢的一首七律,人称最佳,请看他是怎样写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黄鹤楼》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主要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
一是意中有象、虚实结合的意境美。诗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仙人跨鹤,本属虚无,现以无作有,说它“一去不复返”,就有岁月不再、古人不可见之憾;仙去楼空,唯余天际白云,悠悠千载,正能表现世事茫茫之慨。诗人这几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登黄鹤楼的人们常有的感受,气概苍莽,感情真挚。
二是气象恢宏、色彩缤纷的绘画美。诗中有画,历来被认为是山水写景诗的一种艺术标准,《黄鹤楼》也达到了这个高妙的境界。首联在融入仙人乘鹤的传说中,描绘了黄鹤楼的近景,隐含着此楼枕山临江,峥嵘缥缈之形势。颔联在感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抒情中,描绘了黄鹤楼的远景,表现了此楼耸入天际、白云缭绕的壮观。颈联游目骋怀,直接勾勒出黄鹤楼外江上明朗的日景。尾联徘徊低吟,间接呈现出黄鹤楼下江上朦胧的晚景。诗篇所展现的整幅画面上,交替出现的有黄鹤楼的近景、远景、日景、晚景,变化奇妙,气象恢宏;相互映衬的则有仙人黄鹤、名楼胜地、蓝天白云、晴川沙洲、绿树芳草、落日暮江,形象鲜明,色彩缤纷。全诗在诗情之中充满了画意,富于绘画美。
前人有“文以气为主”之说,此诗前四句看似随口说出,一气旋转,顺势而下,绝无半点滞碍。“黄鹤”二字再三出现,却因其气势奔腾直下,使读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急忙读下去,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叠出现,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诗人好像忘记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试看:首联的五、六字同出“黄鹤”;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第四句又用“空悠悠”这样的三平调煞尾;亦不顾什么对仗,用的全是古体诗的句法。诗人未必是有意在写拗律,但他跟后来杜甫的律诗有意自创别调的情况也不同,是知之而不顾,如《红楼梦》中林黛玉教人做诗时所说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在这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去进行实践的,所以才写出这样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此外,双声、叠韵和叠音词或词组的多次运用,如“黄鹤”、“复返”等双声词,双声词组,“此地”,“江上”等叠韵词组,以及“悠悠”、“历历”、“萋萋”等叠音词,造成了此诗声音铿锵,清朗和谐,富于音乐美。
此诗写得意境开阔、气魄宏大,风景如画,情真意切。且淳朴生动,一如口语,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一首诗不仅是崔颢的成名之作、传世之作,也为他奠定了一世诗名的基础。下这样的结论绝不是哪一个人,更不是我硬要往开封人脸上贴金。《唐诗三百首》是后人对唐诗的选集,就把崔颢这首诗列为七律诗中的第一首。可见对此诗的器重。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颢此作,为之敛手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有人说此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但我以为也决非全部子虚乌有,李白写的有关黄鹤楼的诗,我手头就有两首:一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另一首为《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虽都与黄鹤楼有关,然皆另有所托,并非完全写景。同时他的《鹦鹉洲》前四句“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句法何其相似。其《登金陵凤凰台》诗亦如此,都有明显仿崔诗格调的痕迹。因此,既如“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两句非李白之言,承认崔诗绝好,对于李白来说还是可以认定的。《沧浪诗话》(严羽)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虽然有争议,如胡应麟称杜甫的《登高》为古今七律之冠,但也确是代表大家意见的中肯之语。这样一来,崔颢的《黄鹤楼》名气就更大了。
以丰富的想象力将读者引入远古,又回到现实种种情思和自然景色交融在一起,有谁能不感到它的凄婉苍凉。这首诗历来为人们所推崇,被列为唐人七律之首。
传说李白壮年时到处游山玩水,在各处都留下了诗作。当他登上黄鹤楼时,被楼上楼下的美景引得诗兴大发,正想题诗留念时,忽然抬头看见楼上崔颢的题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