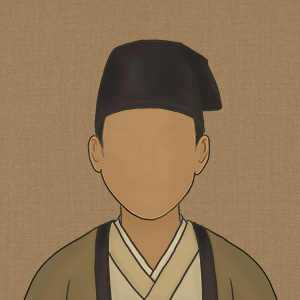春秋多佳日,而“山亭水榭”的风光当分外迷人,但词人却以极冷漠的笔调作出此词,因为“良辰美景奈何天”,消除不了“凤帏”中之“寂寞”——独处无郎,便没有什么赏心乐事可言。“凤帏”句使人联想到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名句:“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有意味的是,词人使“愁闷”与“颦眉”分属于“新”“旧”二字。“旧”字以见女主人公愁情之久长“新”字则表现其愁情之与日俱增。一愁未去,一愁又生 ,这是“新”;而所有的愁都与相思有关,这又是“旧”。“新”“旧”二字相映成趣,更觉情深。
辗转反侧,失眠多时,于是乃有“起来”而“临绣户 ”似乎是在期待心上人的到来。然而户外所见,只不过“时有疏萤度”而已,其人望来终不来。此时,女主人公空虚寂寞的情怀,是难以排遣的。在这关键处,词人又却又写出了一丝安慰,也算是自慰吧!词人给她一点安慰,一轮缺月,高挂中天,并赋予它人情味,说它因怜悯闺中人的孤栖,不忍独圆。“多谢”二字,痴极妙极。同是写孤独情怀,苏东坡在圆月上做文章 :“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朱淑真则在缺月上做文章“ 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移情于物,怨谢由我,真有异曲同工同妙。此词最有兴味之所在正是结尾两句。
上阕中“夕阳谁唤下楼梯,一握香荑”,夕阳西下时分,伊人从楼上被人唤出,下得楼来与人相亲,她的手指,白嫩如荑。“一握香荑”并非说她手里握着一把香草,此句乃是对伊人形貌的刻画,正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用柔嫩的白茅芽比喻美人的手指,描绘庄姜之美。古代男女相约,十分不易,但是伊人下得楼来,却忍笑伫立,一语不发,叫人摸不着头脑。“回头忍笑阶前立,总无语、也依依”三句,是描绘女子的神情:本该见情郎了,她却回头忍笑,婧婧地在阶前倚立,静默无语;但即使没有言语,在情郎眼里,也还是那样楚楚动人。描写二人相会时,词人从女子落笔,写得精致活泼,数十字之间将伊人的形貌神情,心波暗涌,情人间且亲且嗔的复杂心态写得清透,读来惟妙惟肖。
下阕道破伊人忍笑伫立,一语不发的原因。“笺书直恁无凭据,休说相思”,她嗔怪情人信中相约却失约,故假意娇嗔说:书信中的期约竟如此不足凭信,你误期爽约,请你不必再说对我的相思了。但不是真是“休说相思”。“劝伊好向红窗醉,须莫及、落花时”,大约是看见情人慌乱着急,自己心下又不忍,遂以俏皮的口吻转口来抚慰情人珍重春光好沉醉,不要因为犹豫而耽误了两人相处的好时光,言语间隐有“有花堪折直须折”的雅骚之意,含情女子的曲款心事,不言而喻,而彼此且亲且嗔的复杂心态,亦活灵活现。精准的用词中,看得出其中缱绻的情意,离愁,离恨,相爱,相守,爱情之中的种种,纳兰尽悉把握词中。生命犹如朝露,虚幻间便很快度过了一生,如果不及时把握,那悔恨的将会是自己。
这首《落花时》虽写情人幽会,但细致入骨,周身春光亦仿佛流转不定,眉目相照时只见缱绻未露轻薄,其风流蕴藉处颇有北宋小令遗风,言辞殊丽,一似月照清荷。珍重而亲昵,这是纳兰性德风骨心境高于一般市井词人的地方。
这诗真实记录了作者刚入半百之年的一时心态。
诗开头四句写出游的缘由。张衡《思玄赋》说:“开岁发春。”随着新岁来临,诗人已进入五十之年(有的刻本“五十”作“五日”,未可从)。古人说:“人上寿百岁。”(《庄子·盗跖》)由此常引出人们“生年不满百”的慨叹。进入五十,正如日已过午,岁已入秋,是极足警动人心的。孔融就曾说过:“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论盛孝章书》)首句用“倏”,意也正同,都表现出不期其至而已至、亦惊亦慨的心情。五十一到,离开回归空无、生命休止的时候也不很远,(《淮南子·精神训》:“死,归也。”《说文》:“休,止息也。”)要“念之动中怀”了。于是,在初五那天景气和美的良辰,他作了这次出游。
次节“气和天惟澄”以下八句,充分就“游”字着笔。在一碧如洗的天幕下,游侣们分布而坐。山水景物,一一呈献在眼前:近处是微流中的彩色鱼儿在嬉游,空谷中鸣叫着的鸥鸟在高飞。作者用较华采的笔墨着意写出游的、飞的都那样自得,空中、水底无处不洋溢着生机,这其中自然也含着他的欣喜和向往。再放眼远远望去,湖水深广,曾(通“层”)丘高耸,也构成佳境,令人神驰意远。特别是这曾丘(指庐山边上的鄣山),不仅使人联想到昆仑灵山的峻洁(《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淮南子》说:“昆仑有曾城,九重,高万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树在其西”);而且它“旁无依接,独秀中皋”(尽管它不如昆仑山曾城的真有九重),顾瞩四方,无可与比拟者,也足以对人们的人格修养有所启示。序中说:“欣对不足,率共赋诗。”因为这曾丘的诱发,才给人间留下这好诗。
三节“提壶接宾侣”四句,写出好景诱人,邻里欢饮,使诗人不禁兴起“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的感念。这是对人生、对美好事物——诗中所写的风物之美、人情之美、生活之美无限热爱、执着的人自然会产生的想法,作者把人们心中所有的感念,以朴素自然的语言真率地吐露了出来。
结尾四句,写出酒至半酣,意适情遥的境界。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而作者却以高昂的意气唱出“忘彼千载忧”,他的人生观是超脱的。他又说:“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本有旷达胸怀、又加以“中觞纵遥情”的作者所发出的对良辰、美景、佳侣、胜游的热情赞叹,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颓废之歌是迥然异趣的。
《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