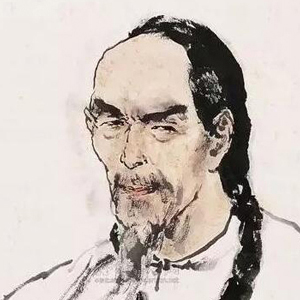本首诗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晚年的作品。此诗写作者游黄鹤楼时听笛的经历,抒发了诗人满腔的迁谪之感和去国之情。前两句写作者的生活遭遇和心绪,捕捉了“西望”的典型动作加以描写,传神地表达了怀念帝都之情和“望”而“不见”的愁苦;后两句点题,写在黄鹤楼上听吹笛,从笛声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景象,借景抒情,使前后情景相生,妙合无垠。
西汉的贾谊,因指责时政,受到权臣的谗毁,贬官长沙。而李白也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被加之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所以诗人引贾谊为同调。“一为迁客去长沙”,就是用贾谊的不幸来比喻自身的遭遇,流露了无辜受害的愤懑,也含有他的自我辩白之意。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没有使诗人忘怀国事。在流放途中,他不禁“西望长安”,这里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国运的关切和对朝廷的眷恋。然而,长安万里迢迢,对迁谪之人来说十分遥远,充满了隔膜。望而不见,诗人不免感到惆怅。听到黄鹤楼上吹奏《梅花落》的笛声,他感到格外凄凉,仿佛五月的江城落满了梅花。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人巧借笛声来渲染愁情。江城五月,正当初夏,当然是没有梅花的,但由于《梅花落》笛曲吹得非常动听,使诗人仿佛看到了梅花满天飘落的景象。梅花是寒冬开放的,景象虽美,却不免给人以凛然生寒的感觉,这正是诗人冷落心情的写照。同时使诗人联想到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历史传说。由乐声联想到音乐形象的表现手法,就是诗论家所说的“通感”。诗人由笛声想到梅花,由听觉诉诸视觉,通感交织,描绘出与冷落的心境相吻合的苍凉景色,从而有力地烘托了去国怀乡的悲愁情绪。所以《唐诗直解》评此诗“无限羁情笛里吹来”,是很有见解的。清代的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唐诗别裁》卷二十)这首七言绝句,正是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见长,使读者从“吹玉笛”、“落梅花”这些眼前景、口头语,听到了诗人的弦外之音。
本首诗也有其独特的艺术结构。诗写听笛之感,却并没按闻笛生情的顺序去写,而是先有情而后闻笛。前半捕捉了“西望”的典型动作加以描写,传神地表达了怀念帝都之情和“望”而“不见”的愁苦。后半部分才点出闻笛,从笛声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景象,借景抒情,使前后情景相生,妙合无垠。
这是诗人会试下第,从京城返家,途中题壁之作。诗人感叹科举考试的艰辛,以及饱食终日的当权者不知道朝廷已日薄西山,危机四伏,却依然迷恋着昔日的余晖,因而说出就此归隐,与美人佛经相伴,了此一生的激愤语。诗中既表现了诗人科场失意的愤懑,也流露出对国事时势的深切忧虑。全诗以比喻象征手法刻画社会现实,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深沉蕴藉,耐人寻味。
首联回顾亲身经历的两次科举考试的失败,诗人禁不住发出一声浩叹,这浩叹正如晏殊所谓“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花不尽》)的怅惘失望。但是,他并没有因失败而一并失去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学问、见识都是独步一时、自成一家的。而也许正因为是“自一家”,他才屡次落第。“莽无涯”三字把时间延伸到遥远的未来,含有无限的感慨,沉痛低徊;“纵横”则又把时间向历史深处推溯再向未来延伸,同时又把现在的一段拓宽,大有纵观古往今来、横视天下当代的气概,充满自信,深沉坚定。这两句一果一因,一叹一转,已经蕴含了全诗的大意。
颔联是全诗的警句,表面是描写此时此地所见的景与物:秋天来了,堂内的燕子还安卧不动;暮色苍茫,路旁的乌鸦依然痴恋夕阳而不归巢。实际上,只要稍微联系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句诗所隐含的深层意义,那时的清王朝正是处在这样―种秋风衰飒、暮色浓重的局势中,眼看着就有被吞没被覆亡的危险,诗人一路上或许就有许多这样的见闻。而全国上下仍像堂内燕、路旁鸦一样,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燕子是候鸟,秋冬之际必须南迁,否则,北方的冬天将冻结它的生命;乌鸦也得在天黑之前归巢,否则将遭遇“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短歌行二首·其一》)的难堪。而诗人笔下的燕和鸦,居然感受不到秋风、暮气的侵袭,感受不到冬天黑暗死亡覆没的气息,由此引发了诗人的哀叹、焦虑。“夕阳”“暮鸦”意象常见于古诗词中,确有实写景物之义,但这里的“夕阳”应该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一类,与“秋气”一起,成为王朝渐趋衰落的象征。这是诗人的深忧,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先觉者的悲哀,“自一家”的具体表现。
颈联这两句意思比较晦涩、模糊,大意是说:天生丽质而不愿以姿容媚俗的绝色女子,是得不到人的宠爱的;根底深厚而不能绽开鲜花笑脸迎人的参天古木,也不会得到众眼的赏睐。“东邻”“嫠老”似合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天下之佳人……莫若臣东家之子”及《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中“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等典故,却又难以指实。这样就导致对诗句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分歧。“东邻嫠老”“古木根深”作感慨解可,作自负解也可;“难为妾”“不似花”作伤心语可,作矜持语也可;就主体言,作诗人的自道看可,作为对方设看也可。联系全诗及其创作背景,应该说,这些理解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只有同时并存才是较为合理的解释。诗人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常为大国忧”,但因为不愿趋时媚俗,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和赏识,一再落第。现在面对周仪暐这个理解他的人,其内心活动的复杂是可以想见的,自伤自负、自怜怜人,种种情感交结一起,难分先后主次。这两句照应开头两句,是全诗所有情结的绾合。
尾联是说诗人想望着有朝一日像飞鸿那样高翔远翥,退出名利场的追逐,伴着美人和佛经,度过自己的一生。“何日”是一种期盼的口吻,而“葬”则语含酸痛。冥鸿遂迹,美人经卷,似带着一定的哲理和玄义,予人某种启迪,但同样扑朔迷离,难以指实。这两句自是愤激话。其实,由唐至清一千余年有关科举的诗中,最不能当真的就是落第诗的结尾两句。不管它是怎样的激昂慷慨,还是怎样的意志消沉,都只是一时冲动。拿龚自珍来说,虽然从这一年开始他“收狂向禅”,但并未真的一生礼佛成为高僧,况美人与经卷也是难以同时捧置在手的。这一次失败后他又多次赴举,直至一第,也并未真的“鸿飞冥冥”成为世外高人。这是他的矛盾和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剧。在“秋气”“夕阳”中,他空有救时扶世而“自一家”的心与才,却没有施展怀抱的时与世。他预感到“堂内燕”“路旁鸦”的危险,却只能希望像“冥鸿”那样独自离开,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先觉者”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