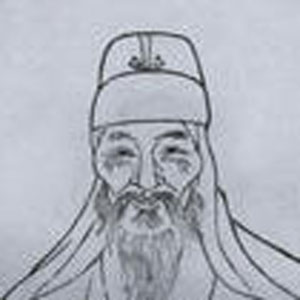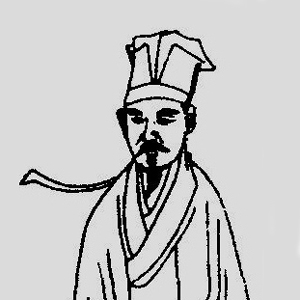这是一首咏史词,通过对战国时赵国于国都邯郸(今属河北)所筑丛台(数台连聚)遗址的描绘,抒发千古兴亡之感。词人步履旧迹,缅怀古事,明写历史人物,暗喻胸中抱负。 词的上片,分三层咏怀古事。
起句“春风赵国台荒”,先概见所咏之事,总括全篇。次句“月明几照苕华梦”,写赵武灵王事。《史记·赵世家》载:“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苕华梦”即指赵武灵王梦见“颜若苕苕之荣”的美人之事,喻帝王奢糜生活,与前句对照,明将美人之梦与国破台荒联系起来,寓意刻挚;而冠以“月明几照”,进而拉开时空距离,于千古兴亡的历史系带上,照出无数苕华之梦,照亮虚无梦境之深层,词人思绪亦随之深入。
“纵亡横破”,转入第二层,再阐兴亡之理。当日合纵连横之雄图大略,今复何在?无非“亡”、“破”而已,二字力重千钧。随纵亡横破,古赵国固荡然无存,而灭赵之强秦又安能久存?“西山留在,翠鬟烟梦”,回旋一笔,人事纷争皆随苕华之梦而去,唯有西山仍在烟云梦簇中如翠鬟高耸,迷离山色尤撩人浮想。
“剑履三千,平原池馆,谁家耕垄”,又出一层,咏平原君事。平原君,原名赵胜,赵武灵王子,惠文王弟,封于东武城,三任赵相,与齐孟尝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为四公子。惠文王九年,秦围赵都邯郸,平原君用毛遂计盟楚、救魏、破秦、存赵。“剑履”,示其名尊位显,古时帝王赐大臣特殊礼遇,佩剑朝见谓之“剑履上殿”;“三千”,指平原君食客三千人。此极写其当日豪阔之情状。紧接以昔日“平原池馆”与今日“谁家耕垄”对照,在巨大的时空跨度和跳跃的意象剪辑中进溢出强烈的盛衰之感,化用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诗意而沉重刻挚过之。
三层古事写毕,则以“甚千年事往,野花双塔,依然是,骚人咏”总束上片,对“千年事”只将“野花双塔”轻描而过,同时又以“骚人咏”贯注强烈的主观情感,充分体现出怀古诗中客观自然的淡化和主观意绪的强化并行交互的普遍的心理历程。
词的下片突发新思,由被秦所灭之古赵国联想到亡秦的英雄。“还忆张陈继起,信侯王、本来无种”,“张陈继起”,指秦末陈胜起义,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与吴广率戍卒九百人在蕲县大泽乡揭竿而起,占领陈地,陈胜自立为王,国号张楚。“信侯王、本来无种”即以千古史实确认陈胜当日所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紧接“乾坤万里,中原自古,几多麟凤”,拓开视野,展露襟怀。“乾坤”句状神州大地空间之广袤;“中原”句写华夏民族时间之亘古;“麟凤”喻治国雄才,冠以“几多”,已明见千古人才之少。而与前片对照,救赵自全的平原君、倾覆强秦的陈胜,无疑是麟凤之才。钦羡之中尤含自负之意。
“一寸囊锥,初无铦颖,也沾时用”,《史记·平原君传》:“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囊锥”喻才智终难埋没;“铦颖”,锐利的锋芒;“时用”,指政治作为。即使“一寸”小锥,亦能发挥一定作用,况天下大才,又岂能郁郁沉埋。这里流露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才观,再次表白词人穷善其身、达济天下的襟抱。词的结句,顺势推导,回视现实:“对残灯影淡,黄粱饭了,听征车动。”面对残灯淡影,旧迹荒凉,如同梦境醒来,一种由思古之幽情引发的勃郁亢奋之力随征车之“动”而动,慷慨激昂,于收处蓄以收不尽之势。唐人韩偓《驿步》诗“暂息征车病眼开,况穿松径入楼台”,息征车,游楼台,有一种悠闲静适之美;而王词既登荒台,又动征车,千年事往,入而复出,更显示出一种雄重飞动之美。
这是一首咏史词,通过对战国时赵国于国都邯郸(今属河北)所筑丛台(数台连聚)遗址的描绘,抒发千古兴亡之感。词人步履旧迹,缅怀古事,明写历史人物,暗喻胸中抱负。 词的上片,分三层咏怀古事。
起句“春风赵国台荒”,先概见所咏之事,总括全篇。次句“月明几照苕华梦”,写赵武灵王事。《史记·赵世家》载:“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苕华梦”即指赵武灵王梦见“颜若苕苕之荣”的美人之事,喻帝王奢糜生活,与前句对照,明将美人之梦与国破台荒联系起来,寓意刻挚;而冠以“月明几照”,进而拉开时空距离,于千古兴亡的历史系带上,照出无数苕华之梦,照亮虚无梦境之深层,词人思绪亦随之深入。
“纵亡横破”,转入第二层,再阐兴亡之理。当日合纵连横之雄图大略,今复何在?无非“亡”、“破”而已,二字力重千钧。随纵亡横破,古赵国固荡然无存,而灭赵之强秦又安能久存?“西山留在,翠鬟烟拥”,回旋一笔,人事纷争皆随苕华之梦而去,唯有西山仍在烟云拥簇中如翠鬟高耸,迷离山色尤撩人浮想。
“剑履三千,平原池馆,谁家耕垄”,又出一层,咏平原君事。平原君,原名赵胜,赵武灵王子,惠文王弟,封于东武城,三任赵相,与齐孟尝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为四公子。惠文王九年,秦围赵都邯郸,平原君用毛遂计盟楚、救魏、破秦、存赵。“剑履”,示其名尊位显,古时帝王赐大臣特殊礼遇,佩剑朝见谓之“剑履上殿”;“三千”,指平原君食客三千人。此极写其当日豪阔之情状。紧接以昔日“平原池馆”与今日“谁家耕垄”对照,在巨大的时空跨度和跳跃的意象剪辑中进溢出强烈的盛衰之感,化用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诗意而沉重刻挚过之。
三层古事写毕,则以“甚千年事往,野花双塔,依然是,骚人咏”总束上片,对“千年事”只将“野花双塔”轻描而过,同时又以“骚人咏”贯注强烈的主观情感,充分体现出怀古诗中客观自然的淡化和主观意绪的强化并行交互的普遍的心理历程。
词的下片突发新思,由被秦所灭之古赵国联想到亡秦的英雄。“还忆张陈继起,信侯王、本来无种”,“张陈继起”,指秦末陈胜起义,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与吴广率戍卒九百人在蕲县大泽乡揭竿而起,占领陈地,陈胜自立为王,国号张楚。“信侯王、本来无种”即以千古史实确认陈胜当日所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紧接“乾坤万里,中原自古,几多麟凤”,拓开视野,展露襟怀。“乾坤”句状神州大地空间之广袤;“中原”句写华夏民族时间之亘古;“麟凤”喻治国雄才,冠以“几多”,已明见千古人才之少。而与前片对照,救赵自全的平原君、倾覆强秦的陈胜,无疑是麟凤之才。钦羡之中尤含自负之意。
“一寸囊锥,初无铦颖,也沾时用”,《史记·平原君传》:“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囊锥”喻才智终难埋没;“铦颖”,锐利的锋芒;“时用”,指政治作为。即使“一寸”小锥,亦能发挥一定作用,况天下大才,又岂能郁郁沉埋。这里流露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才观,再次表白词人穷善其身、达济天下的襟抱。词的结句,顺势推导,回视现实:“对残灯影淡,黄粱饭了,听征车动。”面对残灯淡影,旧迹荒凉,如同梦境醒来,一种由思古之幽情引发的勃郁亢奋之力随征车之“动”而动,慷慨激昂,于收处蓄以收不尽之势。唐人韩偓《驿步》诗“暂息征车病眼开,况穿松径入楼台”,息征车,游楼台,有一种悠闲静适之美;而王词既登荒台,又动征车,千年事往,入而复出,更显示出一种雄重飞动之美。
梅花冰肌玉骨,半霜傲雪,经冬凛冰霜之操,早春魁百花之首,以韵胜,以格高,故为历代人们所喜爱。文人学者更是植梅、赏梅看作是陶情励操之举。杨无咎这首词,借咏梅以抒发自己的情操,寄托幽思,刻画了一位生性孤傲、不随波逐流的世外高士的形象。杨无咎,南宋时画家、词人,字补之,号逃禅老人,清夷长者。高宗时,因不愿依附奸臣秦桧,累征不起,隐居而终。尤善画梅。
词作上片通过对梅花生长的环境、外在形象的描绘,着力刻画出梅花超凡脱俗 的韵致。“茅舍疏篱”,这是梅花生长之处。历来文人雅士总喜欢把他们眼中的梅花置放在清幽、远离尘世的地方,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梅花》),“春来幽谷水潺潺,的滴梅花草棘间”(苏轼《梅花二首》之一),“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卜算子?咏梅》),等等。杨无咎在这里同样也开宗明义,把他所喜爱的梅花置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无非 是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超凡脱俗,高洁自爱。“半飘残雪,斜卧低枝”两句,是以比拟手法来正面刻画梅花形象。上句写梅花之洁白晶莹,下句刻绘梅树姿态之飘逸,这句是化用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末三句笔锋一转,紧承首句,再度刻画梅花周围的环境,从而使得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清幽、高雅的意境:白云缭绕、修竹萧萧、皓月高悬、溪流潺潺。这个画面比林逋诗句的内涵更大,境界更清幽,更有特色。这些景致和意象是隐士生活不可或缺的,它们都具有隐士的生活和品格高洁的象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词人虽写梅,然而根本之点却不在于梅,这就为下片的抒情作了很好的铺垫。
下片词人笔锋转向刻写自己,一位在梅树前伫足凝思的词人形象跃然纸上。“宁宁伫立移时”,“宁宁”,神情专注貌;“移时”,谓时间经过之久,与历时、经时意同。这句是刻画词人自己在梅花树前驻足观赏、凝思。“判瘦损,无妨为伊”,意谓为了观赏梅花、从梅花那里汲取精神力量,陶冶性情,以致“瘦损”了自己的身体也“无妨”。这里看出词人对梅花的迷恋倾心程度之深。这句的写法,以退为进,与柳永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三句:“谁赋才情,画成幽思,写入新诗”。词人觉得光整日价伫立在梅花前流连观赏还远远不够,最好还能让梅花的飘逸神韵、高洁品性时刻与己相伴,于是他便祈想:谁能赋于我才情,能够把梅树的倩影与神韵描画下来、用词章把她刻画下来,成为永恒的留念?
在大自然众多的景物中,雪可谓得天独厚。她以冰清玉洁的天赋丽质,装点关山的神奇本领,赢得古往今来无数诗人的赞美。在卷帙浩繁的咏雪篇章中,白居易这首《夜雪》,既没有色彩的刻画,也不作姿态的描摹,初看简直毫不起眼,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它凝重古朴,清新淡雅。
这首诗新颖别致,立意不俗。咏雪诗中写夜雪的不多,因为雪无声无味,只能从颜色、形状、姿态见出分别,而在沉沉夜色里,人的视觉全然失去作用,雪的形象自然无从捕捉。然而,富于创新的白居易正是从这一特殊情况出发,跳出人们通常使用的正面描写的窠臼,全用侧面烘托,从而生动传神地再现出一场夜雪来。
“已讶衾枕冷”先从人的感觉写起,通过“冷”不仅点雪的存在,而且暗示雪大,因为初落雪时,空中的寒气全被水汽吸收以凝成雪花,气温不会骤降,待到雪大,才会加重空气中的严寒。这里已感衾冷,足见落雪已多时。不仅“冷”是写雪,“讶”也是在写雪,人之所以起初浑然不觉,待寒冷袭来才忽然醒悟,皆因雪落地无声,这就于“寒”之外见出雪的又一特点。此句扣题很紧,感到“衾枕冷”说明夜来人已拥衾而卧,从而说明是“夜雪”。“复见窗户明”,从视觉的角度进一步写夜雪。夜深却见窗明,正表明雪下得大、积得深,积雪的强烈反光给暗夜带来了亮光。以上全用侧面烘托,句句写人,却处处见出夜雪。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这里仍用侧面描写,却转换角度从听觉写出。传来的积雪压折竹枝的声音,可知雪势有增无减。诗人有意选取“折竹”这一细节,托出“重”字,别有情致。“折竹声”于“ 夜深”而“时闻”,显示了冬夜的寂静,更主要的是表明了诗人的彻夜无眠;这不只为了“衾枕冷”而已,同时也传达出诗人谪居江州时心情的孤寂。由于诗人是怀着真情实感抒写自己独特的感受,才使得这首《夜雪》独具一格,诗意含蓄,韵味悠长。
全诗布局井然,层层推进,从触觉、视觉、听觉三个层次叙写,一波数折,曲尽其貌其势、其情其状。结尾句以有声衬托无声,使全诗的画面静中有动、隽永清新,真切地呈现出一个万籁俱寂、银装素裹的清宁世界,诗人彻夜无眠的孤寂也表露无遗。这首小诗充分体现了诗人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特色。全诗诗境平易,浑成熨贴,无一点安排痕迹也不假纤巧雕琢,这正体现白居易诗歌一贯的风格。
论及史祖达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应属周姜这一流派。周邦彦秦观乃至柳永词都描写过歌妓,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
“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着,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
“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动作变化,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感受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问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下面递入遍访旧家门巷打探消息,与篇首暗中连接。浑灏流转,一气直下,转折处十分空灵。“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旧家,从前。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问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问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果然得到的消息,却是伊人随闲花的凋谢而消逝了。“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既是曲笔,将沉痛感情,曲曲传出;又是大笔,既小结前文,又包扫前文,截住感情的波涛,使未了之情,暂时煞住。其情之痛之切令人回味不尽。一结,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个特点。上片写最后访问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的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
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问,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想象的极大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问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此词气格之浑成,完全可以继承周邦彦。
此词写一女子登楼远眺、盼望归人的情景,表现了她从希望到失望以致最后的“肠断”的感情。
这是一首小令,只有二十七个字。“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一句一字闲不得”(《白香词谱笺》)。起句“梳洗罢”,看似平平,“语不惊人”。但这三个字内容丰富,给读者留了许多想像的余地。这不是一般人早晨起来的洗脸梳头,而是特定的人物(思妇),在特定条件(准备迎接久别的爱人归来)下,一种特定情绪(喜悦和激动)的反映。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以“炉薰阖不用,镜匣上尘生。绮罗失常色,金翠暗无精”之类的描写来表现思妇孤寂痛苦的生活和心情。本篇用法有所不同,离别的痛苦,相思的寂寞,孤独的日子似乎就要过去,或者说她希望中的美好日子似乎就要来到,于是,临镜梳妆,顾影自怜,着意修饰一番。结果是热烈的希望之火遇到冰冷的现实,带来了深一层的失望和更大的精神痛苦,重新又要回到“明镜不治”“首如飞蓬”的苦境中去。这三个字,把这个女子独居的环境,深藏内心的感情变化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吗?
“梳洗罢”,隐含着女主人公盼归的期望,如果不是有这份心情在,她可能就会象温庭筠在他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词中所说的“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了。“女为悦己者容”,这容是为了心上人才有意义的,正因为她期望中丈夫会回来,希望他看到自己的美好容貌,所以她才会认真梳洗。一个“罢”字之后,紧接“独倚”,反映了女主人公急切的心情――她黎明即起,刚一梳洗完毕就匆匆的赶去江楼了。一个“独”字,不仅说出了她的孤独,隐含着她与心上人的分离,而且也与下面象征分别的“白苹洲”(详解见下)遥相呼应。
“过尽千帆皆不是”,写出了她希望与失望交替的过程。远处每有一船现影,她便引颈长望,心儿随着船的渐行渐近而渐渐紧张,希望也渐渐高涨,可是船到楼头无情地继续前行,当她意识到这并不是她等待的船儿时,她的失望情何以堪!
“斜晖脉脉水悠悠”,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早上满腔的期望都随落日渐渐黯淡。这斜晖尚且脉脉含情,无限同情女主人公不幸境遇,为什么她盼望的人却如此薄情寡义,弃她于不顾呢?那悠悠流去的水,是女主人公心中不尽的柔情,是她一日日逝去的青春年华,不也是她绵绵不绝的无限愁情么?
“肠断白苹州”,在愁情满怀、斜晖渐去的时候,女主人公的目光偏偏又遇到了他们当年分手的白苹州,这怎么能叫她不肝肠寸断呢?朱光潜认为“把‘肠断白苹洲’五字删去,意味更觉无穷。”因前几句已写出一个倚楼等待离人归来却一再失望的思妇形象。“斜辉”句景中有情,足以给人无限联想的空间,再以“断肠”涂饰,便一泻无余,神形俱失,遂成败笔。这是很有道理的。
词是注重作家主观抒情的艺术形式。这首小令,情真意切,生动自然,没有矫饰之态和违心之语。词中出现的楼头、船帆、斜晖、江水、小洲,这些互不相干的客观存在物,思妇的由盼郎归来的喜悦到“肠断白苹洲”的痛苦失望,这些人物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作家经过精巧的艺术构思,使之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形象。作家的思想感情像一座桥梁,把这些景物、人物联系了起来,而且渗透到了景物描绘和人物活动之中,成了有机的艺术整体,使冰冷的楼、帆、水、洲好像有了温度,有了血肉生命,变得含情脉脉;使分散孤立的风景点,融合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艺术画面;使人物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的心理活动完美统一地显示出来。这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思妇的怨和恨,血和泪,深深地感动了作家;在这些似乎平静的字句中,跳动着作家真挚热烈的心。
这首小令,像一幅清丽的山水小轴,画面上的江水没有奔腾不息的波涛,发出的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连落日的余晖,也缺乏峻刻的寓意,盘旋着一股无名的愁闷和难以排遣的怨恨。还有那临江的楼头,点点的船帆,悠悠的流水,远远的小洲,都惹人遐想和耐人寻味,有着一种美的情趣,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这首小令,看似不动声色,轻描淡写中酝酿着炽热的感情,而且宛转起伏,顿挫有致,于不用力处看出“重笔”。
思妇题材写的人很多,可说是个“热门题材”,但这首小令,不落俗套,很有特色。这也是个软题材,但这首小令不是软绵绵的,情调积极、健康、朴素。在有着绮靡侧艳“花间”气的温词中,这首小令可说是情真意切,清丽自然,别具一格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