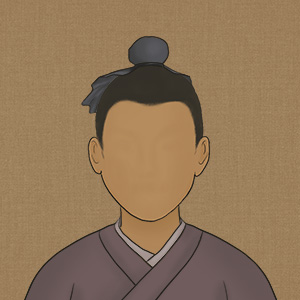此诗前六句写闺妇冬夜空房独宿,因而触物伤心的苦景。“青楼”,指涂饰青漆的楼房。如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本诗首句即从曹诗化出。富家楼阁,本该是宾朋络绎,且临大路,更当有车马喧闹;然冠以“寂寂”二字,则其室内室外一片清静无声、冷落寂寥之状可想而知。故首句不仅点出地点,而且入手扣题,为下文描写闺怨预示了环境气氛。次句既点明时令是冬季,在那雕画着花纹的窗子外面,但见白雪纷纷飘舞;又通过“纷纷白雪”,烘托出闺妇那凄凉的心境和纷乱的思绪。第三句承上仍写室外,少妇无聊地守着窗儿,孤寒之感已然袭上心头;当她望见池上鸳鸯双双偎依,雪寒之间犹有一丝亲热温暖,更是不免“人而不如鸟乎”之叹。故第四句一转,由室外转写室内,由鸳鸯双联想到自己孤独。你看她,情不自禁地回顾室内:空荡荡的闺房中,唯有那罗帐里面的苏合香,在默默地燃烧(“然”同燃),平添了几分房栊空寂的气氛。一个“空”字,生动传神,既渲染出环境的虚空,也暗示出人物心境的空寂。在这寂寞的重压之下,她反而感谢那道屏风解人情意,将那撩人愁思的窗外明月遮障,令自己不至于由于月圆人不圆而弥加哀怨。她的心情也扭曲了:明明是害怕黑暗孤寂,不敢熄灯,她却恨那盏青灯冷酷无情,惨淡的碧火直射着孤眠之人,愈增其形影相吊、茕独凄惶的苦楚。这二句用拟人的笔法,移情入景,将思妇的凄楚,写到极为委婉深曲。
“辽西”二句,忽又荡开一笔,将空间推移至几千里之外,设想边塞丈夫的情景。这位闺妇由眼前江南的“纷纷白雪”,自然联想到丈夫所处塞北的严寒:由长期的音沉信杳,自然想到路遥难通的缘故。她想:辽西边境早已是天寒水冻,冰天雪地,那里的春光恐怕极少停驻吧;蓟北塞外,离江南相隔好几千里,即使丈夫托鸿雁传书,但由于千山万水的阻隔,音书也很难送到啊!二句从对面着笔,设想对方的寂寞相思和雁书难寄,不仅表现出彼此的心心相印,而且把闺妇的痴情思念再度推进了一层。
结尾二句,写闺妇殷切地期望以及深沉的忧虑:她希望丈夫早日度过关山,回到自己身旁,以慰己心;她提醒丈夫应当时刻想到,妻子虽正处在青春妙龄之际,妻子虽正处于青春妙龄之际,然而韶华易逝,红颜易衰,正如桃李花开,只能保持短暂的鲜艳妍美一样,随着春归,它又将凋谢零落。因此,千万要珍惜青春,不要错过时光。二句又由边关收到眼前闺房,与前文关合呼应。运用了暗喻和夸张的手法,愈见得思妇忧愁之重与盼归之切。
此诗所写景物皆是闺妇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感,因而无不饱含闺妇强烈的感情色彩,成为其内心的物外表现,堪谓情景交融,形神兼备。通篇对仗工整而又自然。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
清代赵翼《瓯北诗话》说陆游入蜀后“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这些倡言恢复的诗篇主要抒写收复失地的愿望,壮志难酬的悲言、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苟安投降的不满。在英雄壮举的幻想中表达始终不渝的爱国深情。《宝剑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首,也是颇有特色的一首。它以别致的构思、平实的语言,把爱国深情表达得深婉蕴藉、悱恻动人。
“幽人枕宝剑,殷殷夜有声。”“幽人”是诗人理性的化身,“宝剑”是诗人理想的寄托。诗人的形象是这二者的统一。“枕”字连接“幽人”与“宝剑”,表明诗人时刻不忘统一国土,随时准备参战杀敌。第二句从幽人的感觉写宝剑的声音,至于宝剑为何发声,暂搁不提。“人言剑化龙,直恐兴风霆。”紧承剑有声,借神话传说进一步想象:剑会变龙,龙能兴起风雷。而那些随遇而安的人们总怕打破平静,于是,不思发奋的人们由于害怕风雷顿起而千方百计禁锢蛟龙,使其不得伸展。“不然言狂虏,慨然思遐征。”诗人进而赋予龙以思想情感,说它如果不是被压制,就会因憎恨狂虏的侵犯而言然远征。实际上这是喻指诗人犹如一条被锁着的龙,渴望施展呼风唤雨之功、发挥雷霆万钧之力,报效国家,了却宿愿。这是第一层,以叱咤风雷的巨龙自喻,表现诗人对实现壮志的热切愿望。同时暗示出诗人不能如愿以偿的原因,为下一层写劝慰和不平作铺垫。
“取酒起酹剑,至宝当潜形”写幽人劝慰宝剑藏匿形迹。紧接着回答为何要“潜形”:“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是以反语来发泄诗人的郁言不平之气。幽人劝慰宝剑的:“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这两点理由都含有诗人言疾怨恨的情绪,后者甚于前者。“胡为鸣不平”,极其有力,在结构和意义上都有重要作用,宝剑发声是在鸣不平,回答了开头的问题,使首尾对应,结构完整。 此是诗中引人遐思的强音,是诗人情感升华、照亮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诗的第二层,幽人从现实出发安慰宝剑,抒发诗人壮志难酬的不平之鸣。
从结构和意境上看,这首诗的构思颇为别致。借物抒情,情含物中。剑本是一种武器,但在爱国者的心中它成了诗人杀敌报国、引动文思的触发物。诗人饱满的爱国热情又使剑具有了生命和性格,成了萌发创作激情、引起想象、表达理想的凭借。
触及与杀敌有关之物,即生报国之思,非独《宝剑吟》。在被人推为陆游压卷之作的《长歌行》中有“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在《老马行》中有:“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而在《宝剑吟》中,诗人见剑生情,情又幻化成意象。把剑拟想成龙,再借龙自喻,婉转曲折地表达了诗人难以遏止的不平之情。联系诗人的经历,这不平之情是多方面的:有“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的壮志不遂的不平之情;有“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的对国家前景忧虑的不平之情;有“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的言恨投降派的不平之情;更有“丈夫有志苦难成,修名未立华发生”的蹉跎光阴的不平之情。种种复杂强烈的不平之情若率直抒写,易生抽象叫喊之感,有锋芒毕露之嫌,无跌宕起伏之美。同时,激烈率直地写不平之情,还可能触犯统治者而遭祸。于是,这首诗就移情于物,多所想象。让想象在构思中充分发挥作用。不过这首诗的想象与陆游其他爱国诗歌的想象又有所不同。不是通常的结合诗人生活经历和抗战愿望来想象,而是像屈原、李白那样借神话传说构造想象世界。
这首诗从独特的构思之中,把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更显得含蓄蕴藉,曲尽其情。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宝剑有声比喻壮心不已,在想象中流露出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迷惑、感情与理智搏击的痛苦。宝剑是明喻,是对“心未平”的烘托和强调,不是贯穿全诗的完整清晰的艺术形象。作者运用借喻兼拟人的手法,使宝剑作为一个鲜明的抒情形象贯穿全诗,与幽人的形象一起构成一个有丰富复杂性格的形象,即诗人的自我形象。这首诗的意象是按空间顺序,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连接两个充实而生动的画面,诗人的形象隐蔽在幽人与宝剑的背后。诗人的爱国激情就熔铸在这独特的构思之中。
这首诗构思别致,而语言却很平实,通篇没有豪壮华丽之语,也无生硬晦涩或故作姿态之感。语言平实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修辞、音韵方面。作者善于生动灵活地运用普通词语如“枕”“化”,等在诗中既起连接作用,又有神韵,使幽人、剑、龙成为活的形象,引起联想。把“言慨”一个词,拆开来用在两句中,使诗句气势贯通、情意激切,从中可看出诗人的用字之功。不造奇拗语句、注重意思的简洁明快;句子内部词序不颠倒,句式通俗自然如口语;句与句之间衔接紧凑,结构上细针密缕,而意象疏朗雄阔,留下想象的余地又不使人徘徊停驻。诗人还善于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用比喻比拟,加强意境的奇幻含蓄之美;用反诘、反语,犀利有力,极尽言懑揶揄之情态;注重音韵、声调,抑扬顿挫,富于音乐美。语言上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该诗的通俗易懂。
中秋之夜,诗人独自在翰林院夜值,面对一轮明月,想起了远谪江陵的好友元稹,关心他能否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能否同赏明月,寄托了对友人的无限牵挂与思念之情。全诗巧妙采用对写手法,由诗人自己所见实景联想到友人的处境,表达委婉含蓄,尤其是“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在里外故人心”一联,对仗工整,感情深沉诚挚,真切动人。
古往今来,有无数诗人在十五的月亮上做文章,而所有这些诗文都有一个共同主题——思念亲友、盼望与亲友团圆。应该说主题和题材的接近使得这类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陈陈相因之作,但也确实留下了一些清新可人的典范之作。白居易此诗虽然比不上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也算是上乘之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诗歌的颔联:“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在里外故人心。”对仗工整,形象鲜明,既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又容易让人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三五夜中新月色”与“二在里外故人心”的关系至少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在此月色下诗人产生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其二则是此明亮的月色就像诗人思念朋友的心情一样纯洁真切。“二在里外故人心”这句本身也有三种可能的理解,其一是诗人思念两在里外故人的心情;其二则是两在里外的故人思念诗人的心情;其三则是相隔两在里的两个朋友之间的相互思念的心意。这些不同理解的可能性增添了诗歌的可读性,也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从而使得读者比较容易进入到诗歌的再创造中去。
“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这两句也是清新出色的诗句。就在诗人欣赏这皎洁的月色之时,却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因为身在地势低下的江陵而有可能看不到月色,这种心理真可谓细腻。而这还只是表面的意思,其深层意义则是朋友现在被贬江陵,远离朝廷,已经感受不到皇帝的光辉和恩泽了。
此外,全诗在整体气氛的营造上也颇为成功,诗人着力在阴、冷、深等方面做文章,其意不在烘托月色的明亮,而在渲染诗人和自己朋友的阴冷、凄凉的心情。这种冷色调的画面是适于表现诗人深沉之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