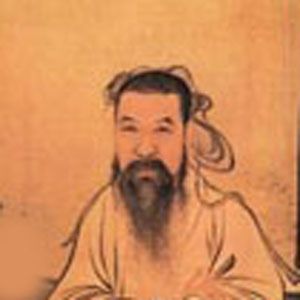傥有长毂动,何忧折箠笞。
似闻当宁叹,颇牧今何之。
岂惟一方痛,其势又类腓。
策士仍三年,侧席收六奇。
谁当挽天河,洗出中兴碑。
傥有长毂动,何忧折箠笞。
似闻当宁叹,颇牧今何之。
岂惟一方痛,其势又类腓。
策士仍三年,侧席收六奇。
谁当挽天河,洗出中兴碑。
这是马致远写的一支表达身处天涯,心系故园的“断肠人”羁旅乡愁的小令,与《天净沙·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支曲子将诗词中常有的意境和手法引入曲中,然又自出机杼地描写了特有景色中的特定氛围:雨夜、孤舟、渔灯中离家万里的旅人在点点滴滴的雨声里情不自禁流下“几行清泪”,这使读者也不由得产生强烈的共鸣,情景交融,语简意深,堪称马致远散曲小令中的佳作。
此曲开篇“渔灯暗,客梦回”两句写在水上过夜的情景。潇湘自古为鱼米之乡,故以“渔灯”二字开头,巧妙地抓住了“潇湘夜”的特点。同时,一个“暗”字奠定了全曲暗淡感伤的气氛。“客梦回”的“客”系作者自指,此字为下文的思家作了铺垫。“梦到什么,作者未写。梦回人醒,却是孤舟夜雨,故下面紧接”一声声滴人心碎“。这句写对深夜雨声的感受。
“孤舟五更家万里”写了离家之远,孤身之苦。“孤舟”照应“鱼灯”,“五更”照应“梦回”,“家万里”照应 “客”。这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写出了远离家人的旅客在深夜的孤独寂寞之感,是为“心碎”之第一层烘托和具体内容的揭示。
“是离人几行情泪”,再写出思家的痛苦,它是“心碎”的第二层烘托。闻雨伤心,离情顿生,乃是古代诗词常用的手法。马致远将这种诗词中常有的意境和手法引入此曲,然后有自出机杼,将雨、泪、情、景融为一体。语简意深,堪称马致远散曲小令中的佳作之一。
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此词上片抒依依惜别之情,并设想别后自己一人的孤苦凄哀;下片自悼身世,更为悲苦。此词哀婉沉痛之极,几令人难以卒读,艺术上创造性地运用了二十余处叠词。
此词起三句,是写眼前景,抒此时情,点出夕阳残照的背景:“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正是暮色苍茫时分,斜阳一抹,欲落未落,残照丝丝,闪烁未消,人在这种境界中分别,心绪正如微云寸寸飘忽,感情还若残照丝丝不断,真如南唐后主李煜所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用“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二句具体描画人在将离未离之际的欲语无言,魂不守舍。于极度哀伤中,仿佛灵魂都已出窍,正闪闪摇摇,漂荡游离,无所依托。抬眼看去,
“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山山水水依旧,人已在山山水水中渐去渐远,望断山水却望不见人,那种惆怅、那种悲苦、那种失落、那种凄凉,实在是“人间没个安排处”。
“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三句,把此时此地的离愁别恨、凄苦难捱推及今后的岁岁月月“只似今朝”,也可谓情到深处反无言了。上片于写景中抒发离别时的留恋不舍,微云、残照、山山、水水皆被一片愁云惨雾所弥漫,实为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天空、地上充溢了诗人的不尽离思。
下片历写离别后的凄冷忧伤,以遥问青天而青天不应劈空而来,千言万语尽在此一问中。“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自意中人离去,双卿孤独无依,内心苦楚无处言说,“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从此无人管顾、无人痛惜,任双卿独自憔悴,黯然销魂;“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再无人欢欢喜喜、情切切意绵绵地看双卿偷素粉学化妆时的情景了。这几句与李商隐《无题》诗中“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同义,应是诗人与意中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时的趣事,难以忘怀,不忍忘怀。词至末三句“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结出生生世世,此情不泯,夜夜朝朝,凄苦依旧的一片痴情。
这首词写景处,景景有情,写情处,情情难抑,虽从女方立意,而两情坚贞历历可见。全词几乎句句都用叠字,读起来,仿佛听到诗人在悲悲切切地诉说,呜呜咽咽地呢喃,言虽尽而意不绝。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背景和本事,现在难以考证确切。从"春风倚棹阖闾城"句知道,此诗当作于今苏州城。从目前考知的史料看,作者一生中曾有过两次离苏州,一次是被贬为南巴尉时。一次是赴淮西鄂岳转运史判官时。被贬南巴在唐肃宗至德三年初,诗中"春风"、"春寒"句证明,作诗时是在冬末春初,时间与被贬南巴的时令相吻合。又诗末有"青袍今已误儒生"句。印证其作于遭贬之后,郁郁不得志之时。此外,青袍又称青衿,按唐朝的服饰制度,三品官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每品又有正、从和上、中、下之别。南巴尉属从九品下,正好服青。由此推断,此诗大约作于至德三年初,诗人第一次被贬,行将赴任之际。
这首诗气韵流畅,音调谐美,景物描写细腻委婉,耐人寻味。诗中抒情,于惜别中流露出愁哀,使人感到深沉凝重。"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水国指苏州一带,因这一带多江河水流而名。这一联说,在春风乍起的时节,诗人将起程作万里之行,船停靠在苏州城外,故友严士元前来送别。二人执手相向,百感交集。回首往事,瞻念前途,心中就象水国变幻莫测的天气,忽晴忽阴,忽好忽坏,还不时带些初春的寒意。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阴落地听无声。"这两句诗,从字面上看,明白如话,但细细体味,会觉得韵味无穷。雨细得让人无从感觉,直到衣服由潮渐湿,方才知道。这种自然景象,只有"水国"常有。阴儿落地,皆因春风春雨所致,前后相承,互为因果。此联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对床夜语·卷三》云:"人知刘长卿五言,不知刘七言亦高。……散句如‘叹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细雨湿衣看不见,闲阴落地听无声。’措思削词皆可法。"对这两句诗,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主客谈笑之间,忽略了客观环境的变化,偶然才发现雨已湿衣,阴已落地。笔者以为这种解释不确。诗中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阴落地听无声。"一"看"一"听",表明作者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在探求。他看过,听过,然而一无所获。我们知道,残阴落地,是十分零乱的,声音之微;一般也是听不到的,倘或落阴有"声",倒是奇事。那么作者何以如此下笔呢?试推想来,大概二人谈话之中,触及心中不快之事,默然相对。在这暂短的沉寂中,感到衣服已润湿,方知下着细雨,努力去望天空,却是一无所见。看到阴办在纷纷飘落,认真去听,却也听不到半点声响。这里应是写一种极静的环境,以这种静反衬出二人心中的不静和无限忧郁。这样理解,全诗的气氛与作者的心境才统一。此外,作者将要远行,对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所以观察的格外细致。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这是写作者想象中的景象,由儿体的细写转向宏观景致的粗描。薄暮夕阳下,孤帆远去;湖南碧草如茵,愈发勾起作者的情思。应该说,这情思是非常复杂的,有对朋友、亲人的思念,有对仕宦生涯变化无常的感慨,也有对前程黯淡、事业无成的忧愁,还有孤帆远行的寂寞,总之,作者设想着旅途上的景况和自己的心情。
"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东道可指严:七元,即东道主的省称;亦可指东路上的故交相识,与作者的南行相照应。临行之前,关照朋友,若遇到打听我的知己,请转告他们,我已被"青袍"所误。儒生,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代称。按古代传统观念,渎书人当以匡世济国为己任。有一颗成就事业的勃勃雄心。但而今诗人一领青衿,官微职卑,满腹雄才大略无以施展,仕途生涯坎坷不平。从这句诗中,我们看到诗人这里既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时,也是对朋友们的劝诫,抒发了自己久抑心头的忧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