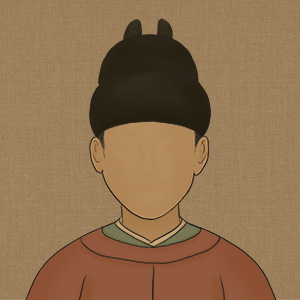上阕描写春游的所见所感。开端从春景写起。“与客携壶”,开头便是借酒浇愁。“梅花”两句交待时令,已到仲春,更兼风雨,摧残梅花情景可知。情亦如花,倍受间隔。“自语”“啄”“度”将鸟儿的可爱情态描摹得栩栩如生。由这美丽的春光,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春衣的描写。词人身上穿着的春衣,都是恋人用白晰柔嫩的手亲自剪裁的,那衣服上至今还残留着一些断线残丝。词人将恋人的手比做柔荑,娇艳动人,令人产生无限美好的遐想。“再见无路”表达的是一片无奈的心情,与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都城南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阕则描写故地凝思。“凝伫”二字看似写状态,实则写心情。在物是人非之时重游旧地,或属无心,或似有意,管不住双脚似的来到曾经良辰美景的庭院,但见人去楼空。在美人门前呆呆且久久地凝望。往事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八字以清淡萧条之笔写现下孤寂心态,更反衬昔日的风流。“系马垂杨”写当年潇洒神色,俊逸风采。一个’但”字,又勾回现今。“认郎鹦鹉”写常来常往之熟稔,而今垂杨依旧,无马可系,只剩一片凄凉。此处鹦鹉或许一如往常地在招呼来客,但对词人来说,却已事过境迁,人面不知何处。“扬州梦觉”化用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表达了和杜牧相似的感情历程。“彩云飞过”或象征过去的那段美好恋情,或象征昔日的爱人,如今都化为陈迹,再也寻访不到了。这里词人一片痴心,都化作对燕子的喃喃私语,流露出无限的深情。“吟袖弓腰”,以局部代表整体,从中可以想象出伊人身姿的曼妙。“倩梁间燕”,这富有情致的一笔。结尾几句自伤自叹,空怀悲戚。
此词写追怀旧情。上阙由眼前风雨摧花、耳边幽禽独语、衣上残茸半缕,引出对旧情的思念和相见无路的怅恨。下阙以“凝伫”承上启下,旧游处仅见垂扬、鹦鹉,又感慨今日物是人非;虽知人去梦醒,却又欲罢不能,而向梁间燕子殷勤寄语;最后明知多情误人,虚度年华,仍在苦涩中咀嚼昔日的甜美。全词从细微处着笔,以小见大,以景衬情,回环蕴藉。这首词虽是伤春怀人之作,然而读后并不觉得沉重,清新的语言,婉转的情调,使它成为描写思念之情的动人佳作。
此篇通过孤儿对自己悲苦命运和内心哀痛的诉述,真实有力地描绘了了社会的人情冷漠与人们道德观念的扭曲,揭露了社会关怀与信任基础解体前的黑暗与冷血,是一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染力的优秀诗作。
全诗分为三部分:一、首三句孤儿慨叹自己偶然生在世上,偏偏数他命苦。“遇”是“偶”的假借,“遇生”意思谓偶然而生。以慨叹之语带起全篇,一开始就引人进入充满悲剧气氛的情境之中。二、“父母在时”至“当兴校计”,历叙孤儿年年月月、无休无止地遭受兄嫂种种虐待,是诗的主体部分。三、“乱”词以孤儿不堪兄嫂折磨的绝望心绪作结,既贯连第二部分的叙事,又与第一部分慨叹之词遥为呼应。
其中第二部分又可分为这样三段:
第一段从“父母在时”至“孤儿泪下如雨”。孤儿的生活以父母去世为界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乘坚车,驾驷马”,未必完全是实际情形的写照,更可能是孤儿在留恋昔日安乐生活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映象,但也说明了他当年在家中娇子的地位。父母死后,他即刻沦为兄嫂不化钱雇用的奴婢仆役。“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是诉说他行贾路途遥远。“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正写出他一路上餐风宿露的艰辛。可是寒冬腊月回到家中,他却“不敢自言苦”,兄嫂的冷酷和孤儿的畏惧,由此可见。前人指出:“苦极在不敢自言。”(谭元春评语,《古诗归》卷五)深中其微。回家后,孤儿得不到片刻休息,兄嫂又将一大堆繁重的家务推到他身上,刚在“高堂”置办好饭菜,又赶紧奔向“殿下堂”去照管马匹。“行”意思是复,“取”通趋,意谓急走。用“行取”二字将“办饭”和“视马”二件活连在一起,于不间断中更显出促迫和匆忙,如见孤儿气喘吁吁不堪劳累之状。孤儿生活从“乘坚车,驾驷马”沦为“行贾”、“视马”,今昔对照异常鲜明,这比单单状说诸般苦事,更能激起心灵的震荡。
第二段从“使我朝行汲”至“下从地下黄泉”。孤儿冒寒到远处取水,朝出暮归。他双手为之皴裂,脚上连双草鞋都未穿,踩着寒霜,心中哀切。更有甚者,覆盖在寒霜下的荆棘无情地扎进他的腿,拔去后,其刺却折断在胫肉中,剧痛难忍,这使孤儿更加悲哀,泪涕涟涟(“渫渫”,水流貌;“累累”,不断)。兄嫂只把他当作供使唤的工具,从未关心过他的寒暖,他冬天没有短夹袄御寒,夏天没有单衣遮体。诗中“足下无菲”、“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三个“无”字概括了孤儿一年四季衣着褴褛不完的苦状。他的生活毫无乐趣,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如果说第一段“泪下如雨”尚表现为一种哀感,第二段“下从地下黄泉”则已经转为厌生,这表明孤儿的心绪朝着更消沉的方向作了发展。
第三段从“春气动”至“当兴校计”。阳和流布,绿草萌芽,从寒冻中苏醒过来的大自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孤儿的生活却依然是那祥困苦,三月里他要采桑养蚕,六月里又要收菜摘瓜,这是言其大端。诗歌接着叙述收瓜一事,笔笔生哀。孤儿受兄嫂驱迫去收瓜是一悲;年幼体弱,不堪其劳,致使瓜车翻倒,此又一悲;路人不予相助,反而趁机白吃其瓜,此更是一悲。孤儿本当斥责路人不义之行,然身单力薄,不足与之抗衡,只好转而苦苦哀乞于人;然而,值此社会崩溃之际,谁还跟你讲仁义道德、仁义亲爱,不仅不帮忙反而乘乱抢瓜,社会的冷漠与人情的淡薄可见一斑。这也是对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警示吧!作者如此周详委折,描写入微,极状孤儿悲苦,严厉抨击了社会与人性的黑暗面,是汉乐府成功运用细节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突出的一例。
这一段与最后的“乱”词叙事连贯,并反映出孤儿心理的进一步变化。孤儿哀乞路人还他瓜蒂,好让他带回家去点数,冀望因此而减轻兄嫂对自己的贵罚。“独且急归”,是说孤儿要(“独”即将要)赶快回家去,以便在兄嫂风闻覆瓜之事前向他们说明事由。然而当他走近居地,已听见兄嫂“譊譊”怒骂声——他们已经得知此事,不会再听孤儿的解释,等待他的凶毒的后果可想而知。孤儿在投诉无门的境况下,再一次想到已故的父母,想到轻生,这与前面“父母已去”和“下从地下黄泉”相互回应,同时也表现出孤儿覆瓜之后,其心理由侥幸到绝望的急剧转变。
全诗采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较完整地反映出孤儿命运的线型流程。作品艺术上的这种构思与主人公孤儿的身份正相适宜,因为孤儿的痛苦不仅表现在他平时干活的繁重劳累,还反映在他无人可与诉说,无人愿与交谈的孤独处境;他的痛苦也不单是来自一时一地突发的事端,在长年累月供人驱使和遇到的大量琐碎细事中都无不伴有他哀痛的泪水。故作者选择自述方式,通过许多生活琐事来反映孤儿痛苦的一生,更具有真实感。
此诗还有一个特点,讲述者话题中心比较分散。一会儿写不堪兄嫂使唤,一会儿写他自己体貌瘦羸龌龊,衣饰不完,一会儿写郁结心头的悲怆怨怒,这三部分内容依次出现构成一个周期,整首诗主要就由它们回复迭现的变化而组成。孤儿话题中心的分散,一方面反映了他因痛苦而变得烦乱无绪的心境,另一方面,这种讲述方式正是智力尚弱的未成年人谈话的特点,与他的年龄恰好相合。
作品语言浅俗质朴,句式长短不整,押韵较为自由,具有明显的口语型诗歌的特征。
词中吟咏的油灯结花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古来题咏灯花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张林的这首词却能不落俗套,新颖别致,读来饶有情味。
上片刻画灯花,连用五个比喻,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灯花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的千种姿态、万种风情。
“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白玉枝,指白色的灯芯草。前两句说,灯蕊在不经意间结花,它最初如花蕾般含苞待放。“金粟”,桂花的别名,这里形容灯花。韩愈《咏灯花同侯十一》云:“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此种比喻在灯花描写上用得是最为普遍,本词是以它来描摹灯花初结成时的形状。下面三句,句句比喻,形容灯花的三种不同景象。“半颗安榴,一枝杏,五色蔷薇”。安榴,即石榴。石榴来自西域的安国,由张骞出使时带回,故又名安石榴。灯花越结越老,形状不断变化,它先是碎小如桂花,继而大如绣球般的石榴,再变成鲜艳浓的杏花,最后变得如蔷薇花般色彩绚烂斑驳。“半颗”、“一枝”、“五色”,这三个数量词,从小到大,依次递增,既写出了灯花的变化过程,将其各种姿态刻画地生动形象。
上片可说是用实笔摹绘灯花由初绽到盛开的过程,下片则是以虚笔来称赞灯花之美,简直可称巧夺天工。
“半须羯鼓声催。银釭里、春工四时。”羯鼓,用唐南卓《羯鼓录》记载的唐玄宗敲击羯鼓,催开含苞欲放的柳杏的典故。唐玄宗此举在于夸耀人工能巧夺造化,而本词则反其意而用之。银灯(釭即银灯)。里点燃的灯芯草会结花,它并不需要人工的催唤,好像其中自有造化的四时功能。作者从另一方面赞美灯花的富于变化,似有造化之功。“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灯蛾扑火,与蝴蝶灯花,两者本来并不相干,但灯草既成灯花因而兼具两者的特点。作者有意将它们联系起来,并主要侧重蝴蝶戏花的方面。因此,运笔就将蝴蝶戏花加以此附。灯花既然是花,就应是蝴蝶戏嬉之物。有趣的是,灯蛾竟然学起蝴蝶来,不断地在灯花周围蹁跹飞舞,作者运笔俏皮,貌似揶揄灯蛾,却灵巧传神地赞美了灯花的丽若群芒。
这首词运用博喻手法,写得奇巧生动,俏皮有趣。虽无深情远意,但较之其他咏物词讲穷比兴寄托、笔致幽深、多愁善感的格调来,可算是别具一格,清新隽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