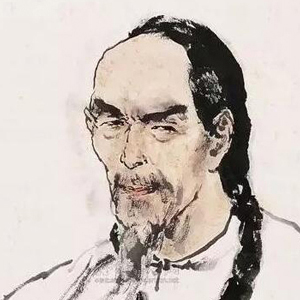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这首诗首联由西村思往事;颔联写进山时的情况;颈联写入西村后所见所闻;尾联写看到景色后触景生情。这首诗场景描写细致,意境优美。西村是诗人旧游之地。这次隔了多时旧地重游,自不免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他观赏着沿途风光,时而引起对往事的回忆。
首联由西村思往事。西村群山环绕,仿佛是桃源世界。他还清楚记得当年游赏时敲门求水解渴的情景。
颔联写进山时的情况:走过柳树簇拥的小桥,就要勒转马头拐个弯,前面临水数户人家便是西村。对于摆脱尘世喧嚣的山水深处,诗人是心向往之的。他另有《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绝句:“数家茅屋白成村,地碓声中昼掩门。寒日欲沉苍雾合,人间随处有桃源。”也把数家的小村视为桃源。此诗这两句富于动感,景物组合巧妙。“高柳簇桥”,似乎尚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而在“初转马”以后,眼前便是“数家临水自成村”,就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写法颇为接近。这不仅回应了首句“小桃源”三字,而且从山回路转中展示了这一桃源境界。
颈联写入西村后所见所闻:周围树木茂密,不见啼鸟,但闻鸣声。当年来游之处,已是坏壁颓垣,自己醉书于上的诗句,也已斑斑驳驳,布满青苔。诗人觉得,眼前这情景很动人,值得怀恋,应当写一首诗留作纪念。
于是转入尾联。正当诗人吟哦之际,抬起头来,只见空中有几缕纤云,一弯新月。在此风景清佳的黄昏时刻,清诗自会涌上心头。
作为一首纪游诗,此诗的特点在于能够不为物累,脱去形似,用渗透感情的笔墨去捕捉形象,将自己深切体验过的、敏锐感受到的物象写入诗中,几乎每一笔都带感情。
常人写这类题材,大致是先叙湖上景致,然后因景抒情。而作者却不循常套,起笔不谈游湖,而先从身世感慨人手。首三句“天风吹我,予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气势宏大,姿态超迈。作者不说自己出生杭州,却说自己是被天风吹落于此的。他是天上的谪仙,身在人间,神在天表,只不过西湖风光的清丽令他满意,他才不想返回天界。这三句,才写到作者的诞生,但却已将他的自命不凡、高视阔步、超凡绝俗之态写出,一种豪迈飞扬的气概,跃然纸上。有这三句定下基调,下面几句就看似惊人而实无足惊奇了。“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之所以说他只是北京城中一个客居的弱冠少年,却不说仕途不得志之苦、不抒少年意气,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首往事时有无限苍凉迷茫,就是因为他是谪仙,胸襟广、目光远,所思者大。“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像樊哙那样建功立业、像驺奭那样立言传世,乃是无数古人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他却说那些都不是他的平生之志,也因为他是谪仙,来到人间乃是为了大济苍生、重振乾坤。战场上的一刀一枪,书堆中的寻章摘句,他当然是夷然不屑的。不过,他这番心比天高的志向抱负,常人是不会懂得。“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就连坟地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地下有知,也肯定会笑作者全然打错了算盘。阅尽人世的小小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论了。
词至上片末尾,豪情已转为孤独之感。过片才写到游湖。“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但他笔下的西湖,乃是与他心境相合拍的西湖,他满怀清愁,所以刚刚看到“一抹”斜阳、“半堤”春草,这愁怀就顿时被惹逗起来了。斜阳芳草,自古都是伤心物,作者在此并未超越前人,但连用了“一抹”、“半堤”、“才见”、“顿惹”,词情便有无限含蓄,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接下“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前者用曹植《洛神赋》“罗袜生尘”之典,后者语本苏轼《前赤壁赋》“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歌。既是泛舟湖上,自不免极目远望,但作者所望也不同凡俗,他望的是“美人”——理想的化身。然而,“何处觅”、“予怀孤寄”,他未能望到理想的归宿所在,满腔情怀亦不知何处吐泄。
词至此,已由豪迈而入孤独,由孤独而入忧愁,由忧愁而入怅惘。经此几番情感转折,终于唤出了全篇的名句:“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怨”,是指他胸怀大志却无人领会、无处施展的怨愤;“狂”,是指他心中汹涌澎湃的狂潮,这狂潮中有高超的见识、有宏大的构想、有急切的愿望,包含之多,实难尽言。欲怨之去,就吹上一曲缠绵悠远的箫乐,让那怨愤随风飘逝;狂来奈何,就舞出一派熠熠生辉的剑光,让心潮在浩荡剑气中暂趋平伏。这一箫一剑,其中包蕴了作者多少失望和希望、痛苦和兴奋;抚起箫、挥起剑,这中间的滋味,令作者魂为之销。相形之下,功名、文名的“两般春梦”算不得什么,就让它们随着橹声飘荡进云水之间。
这首词全盘托出了少年龚自珍的雄心、抱负和自信、自负,是龚词的代表之作。其中核心的箫、剑二句,尤为后人所称道。有人说,这两者分别代表优美和壮美,而作者一身兼有之,实乃不世出之奇才。有人说,这两者代表了作者个性的两个方面,一深远,一宕落。龚自珍一生的行事,亦可以“吹箫”、“说剑”括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他虽然自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似乎剑已涩、箫已折;其实,这仍然只是在“吹箫”而已。上引二句出自《己亥杂诗》,而他在同一组诗中大声疾呼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依然是“说剑”的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