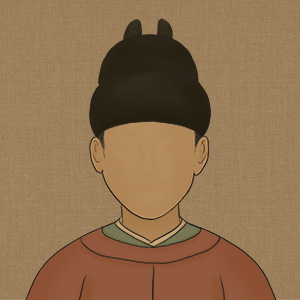谁将幻怪惊愚俗,总向虚空认法门。
此土犹知名教重,昔人尚有典刑存。
愧予晚陋羞前哲,愿以乡盟齿弟昆。
谁将幻怪惊愚俗,总向虚空认法门。
此土犹知名教重,昔人尚有典刑存。
愧予晚陋羞前哲,愿以乡盟齿弟昆。
上片“春色迷人恨正赊”一句,起得出奇。“春色迷人”本应逗人喜爱,延之长久才好,因而每有叹惜春天“留不住”的诗词。可是此词却嫌恨它逗留人间的时间太长了,由“迷人”转而为“恨”,感情的落差似嫌太大,颇令人难以捉摸。但是紧接上一句“可堪荡子不还家?”以问作答,那原因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少妇自问抑或问“荡子”抑或问别人,那无关紧要,总归她是在倾吐愁肠的来由:春色迷人,而荡子不在身边共赏,那闲愁怎能让人经受得了。又岂能不迁恨于惹她伤心的春色,嫌它漫长。
“细风轻露著梨花”一句,是写景,也是写人写情。清晨,春风拂面而来,雪白的梨花上缀着晶莹的露珠,格外清新幽雅,却又不无冷清之感,给人以“梨花带雨”即少妇落泪的感受。这句寓情于景,写少妇面对春景伤心不语,潸然泪下,表现了思妇那孤苦纤弱的心。
下片“帘外有情双燕飏,槛前无力绿杨斜”两句,是缘情写景。“有情”、“无力”相对而出,可见女主人公的心思不在乎赏春惜春,而在于寻求夫妻朝夕相伴的恩爱生活。在她看来,纵然是盎然滴翠的阶前杨柳,也以其无人伴赏而显得“无力”——黯然失色,毫无生机;只有象燕子那样结伴双飞,自由自在,才有情有意有乐趣。然而丈夫不在身边,眼前留给她的是一片索然。
但是,少妇不甘心于这等寂寞闲愁,结句“小屏狂梦极天涯”,尽写出她执着的追求。写女子用“狂”字,似与身分不合,却恰能写出少妇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急切心情,可知她定然能做出一个美梦。一句之中,“小屏”与“天涯”这样空间对比度极大的词语连用,也有极好的艺术效果。那屏后的少妇,为在梦中寻觅“荡子”,那怕到天涯海角,也无所顾及。纵然那里没有迷人春色,没有洁净的梨花,甚或没有双燕飞舞,没有杨柳依依,只要有他,便有情趣,有意义。于此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丈夫的钟情,对爱情的坚贞。前人认为此结句有“振起全片”之妙,此评宜哉。这首词缘情写景,起伏跌宕,错落有致,语言优美动人,比喻贴切,含蓄蕴藉,结句振起全篇,殊可玩味。
诗汉的一位老友在守卫月支的战役中,因全军覆没而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故以“没蕃”为题写诗表达伤怀。
首联交代全军覆没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前年”,前年战败,现今才写诗。这是因为作者在等侯确切的生死消息。在这次战斗中,唐军全师覆灭,友汉是生是死,由于消息断绝,无法肯定,故诗汉不敢贸然动笔。这种感情在亲密的朋友之间是很通常的。然而,老友的消息都一直没有听到。“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蕃汉之间消息已完全断绝,两年之中一无所获,则友汉无论是死是生,都意味着永运离别了。死了,固不用说;活着,也是做了蕃汉的奴隶,不能回还了。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颈联是通过想象,描写战败的惨状:“无汉收废帐,归马识残旗。”因为是全军覆没,不是战死就是被俘,所以唐军的营帐无汉去收拾,散乱地堆在战场上,任凭风撕雨浇,惨象令汉触目惊心。“归马”是指逃归的战马,战马能辨认出己方的军旗,故能逃归旧营。汉是一个没剩,只有几匹马逃脱回来,这—笔真如雪上加霜,令汉想见战争的残酷。
尾联“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是写自己矛盾、痛苦的心情,想设奠祭祀友汉,却又希望他还活着。若还活着.祭奠是大不敬;若确实已死,不祭奠也是大不敬。诗汉两为其难,当此之时,也只有遥望天涯而放声大哭了。此联揭示诗汉内心活动,曲折而又深刻。
此诗感情真挚,且层次清晰,由“戍”而写到“没”,由“消息”断而写到“死生”不明,由“死生”不明而写到“欲祭”不忍,终以无可奈何的放声大哭为结,一路写来,入情入理。而诗汉借用这种过期的追悼,适足增添了全诗的悲剧性。正因为是“前年”的事件,所以有“断消息”的感受,有“疑君在”的幻想,痛慨、痴情,欲绝惨深。废帐残旗,归马踽凉,是诗汉的揣想,却真实地再现了“没番”的战罢情形。其缺点是语言过于直朴,缺乏蕴含,前四句只是铺叙事情经过,占了一半的篇幅,倘若把这些内容移入题目中去,腾出地方集中抒情,效果会佳。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