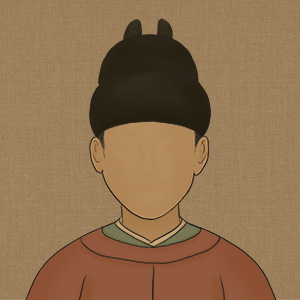这首词先描写了柳的风姿美态,再写其得宠于一时,颇为风光的情形。全篇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渲染了御沟柳得意神情。明是咏写御沟柳沐浴皇恩,成为帝王生活的点缀,实则却是讽刺那些小人得志者或一些得宠之人。
御沟之柳,描写如人,如婀娜轻柔的女子。作者抓住其“栽培得地”来写,因柳近皇宫,所以说它“占春多”。写柳树的影映水时作者用笔很细,着色很新,细细的柳丝影映水中,好像轻丝细罗织成,染得水波一片淡黄。当然,光有美丽还不够,还得要皇帝宠爱才好。下片写柳的媚态,写柳近皇宫,得福得吉祥得天独厚。
此词赋咏御沟柳沐浴皇恩,成为宫廷升平生活的点缀,其实蕴含着词人自己的仕进之想。由于供奉内廷的身份,毛文锡的词作经常流露出贵族享乐的情趣。这首词带有鲜明的皇家气派,宣扬“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栽培得地近皇宫,瑞烟浓”,柳枝的依附高门,恰正是毛文锡人格精神的形象写照。
这首诗首句写诗人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遇到能休息的地方便休息;次句写江水中的白珋已经消失了,水波粼粼,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后两句即景抒怀,三句自称不是逢秋就会伤感的一般文人;末句采用拟人的手法,写听凭傍晚的秋山相对发愁。诗写得富有韵味,显示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气质。
诗的起笔突兀,一开始就指出:不论是南去北来,还是北去南来,诗人总是想去就去,想休息就休息,无优无虑,恬然适意。诗的第二句紧承首句写道:“白蘋吹尽楚江秋。”诗人象是回答说,正是在萧萧秋风把白蘋都吹落了的深秋季节才如此这般说来。他身处秋气潇杀、万物凋零的深秋季节,丝毫没有悲哀凄凉的感觉,反而无优无愁,安然处之。本来,诗人得休便休已经够洒脱了,再有后一句萧瑟景象的衬托,就更显示出超尘脱俗的气质。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悲秋”的传统。一到秋天,西风瑟瑟、枯叶飘零,这萧条凄清的景象极易引发诗人对不如意的人生大兴悲叹之辞。早在战国时期,楚人宋玉作《九辩》,第一句就叹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而此诗作者能如此逢秋而不悲,随遇而安、怡然自得。诗的前两句在叙述诗人不寻常的举止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问号。
诗的三、四句紧扣首二句之意、“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在这里,诗人以道人自比,表现出诗人对闲适味道。飘逸、淡泊无求境界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能够“南去北来休便休”,就是因为他不是见秋生悲的“悲秋客”,而是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道人。因此,当众人对秋生悲时,诗人自然无悲可言,“一任晚山相对愁”。此时,作者远远望去,楚江两岸的山脉凄清寥落,像是在飒飒秋风中相对发愁。晚山本来不会悲愁,在超脱淡泊的道人看来,晚山也不会悲愁。只有在悲秋人眼里,晚山连同周围的一切才看上去象是都在悲叹哀伤。在此,诗人没有直接去写愁容满面的“悲秋客”,而是通过“悲秋客”眼里所看到的秋暮中凄凉悲伤的景物来写“悲秋客”,这样写,更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的潇洒飘逸。
程颢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他这首诗就有些谈禅(佛教道理)的味道。但诗人并不是真的那么旷达,真的能超凡脱俗。其实他写要“休便休”,恰恰说明他对“南去北来”已经感到疲倦,渴望守着家人过宁静安逸的生活;他写“白蘋吹尽楚江秋”,可见他对秋天的到来是敏感的;他写“晚山相对愁”,恰恰反映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愁。所以欣赏诗歌,既要看诗歌中的议论,更要看诗歌中所描写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