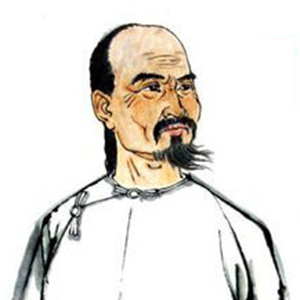“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街西紫牡丹。”开头写残春时节,富贵之家趋之若鹜争相观赏牡丹。唐代京城长安有一条朱雀门大街横贯南北,将长安分为东西两半。街西属长安县,那里有许多私人名园。每到牡丹盛开季节,但见车水马龙,观者如堵,游人如云。诗作选择“长安”、“街西”作为描写牡丹的背景,自然最为典型。作者描写牡丹花开时的盛景,只用“春残”二字点出季节,因为牡丹盛开恰在春暮。作者并没有着力写紫牡丹的美,甚至没有对紫牡丹的形象做任何点染,单从“豪贵”对她的态度着笔。豪贵们耽于逸乐,“无日不看花”,桃杏方尽,牡丹又开,正值暮春三月,为“惜春残”,更是对牡丹趋之若鹜。以争赏之众,衬花开之盛,“惜春残”一笔确实收到了比描写繁花似锦更好的艺术效果。次句“争”字用得很妙,不但暗示了牡丹的姿色绝伦,而且突出了赏花者的迷狂之态。
以上使用侧面描写,着意渲染了紫牡丹的名贵。看似与题目无关,实则为后面展开对白牡丹的描写作了有力的铺垫。“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一个“别”字,引出了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玉盘,冷露,月白,风清,再加上寂静无人的空园,与上联描写的情景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对白牡丹的形象刻画虽只是略加点染,但显然倾注了作者满心的爱悦和同情。用“玉盘”形容盛开的白牡丹,生动贴切。月夜的衬托和冷露的点缀,更增加了白牡丹形象的丰满。“承露冷”三字描写花的状态,既是实写夜色中白牡丹花承受着冷露的润泽,更是着意表现白牡丹冰清玉洁的品质。惟其不以秾艳撩人,自甘素淡,方显高雅脱俗。作者正是通过对紫牡丹和白牡丹这一动一静、一热一冷的对照描写,不加一句褒贬,不作任何说明,而寓意自显。为豪贵所争赏的紫牡丹尽管名贵却显得庸俗,相反,无人看的白牡丹却超尘脱俗,幽雅高尚,给人以冰清玉洁之感。诗人对白牡丹的赞美和对它处境的同情,寄托了对人生的感慨。末句“无人起就月中看”之“无人”,承上面豪贵而言,豪贵争赏紫牡丹,而“无人”看裴给事的白牡丹。即言裴给事之高洁,朝中竟无人赏识。诗题中特别点出“裴给事宅”,便是含蓄地点出这层意思。
全诗通过紫、白牡丹的对比,赞美白牡丹的高洁,以花衬人,相得益彰。短短的一首七绝可谓含意丰富,旨趣遥深。可以说,在姹紫嫣红的牡丹诗群里,这首诗本身就是一朵姣美幽雅、盈盈带露的白牡丹花。
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诗人共写了《陇西行四首》,此处赏析第二首。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