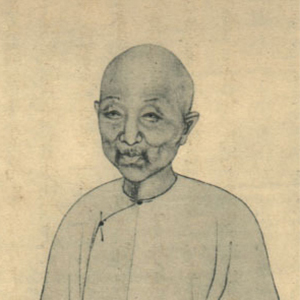秋天是草木凋零的季节.相对于人生来说,又象征着壮盛之期的逝去,垂老之年的到来。所以尽管秋光也很美,却很少有入能像唐人刘禹锡那样豪迈高唱: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康熙三、四年间,担任“江西参议”而分守“湖西道”的施闰章年交四十七、八,正将进入老年之期。“顷年在官,引疾不许”,在这样的年龄遇上阴沉的“立秋”天气,自不免要悚然畏警了:回想当年来到临江府,芷是东风骀荡的春日。倘说那时还曾满怀ff春风骑马到江城,正值繁花照眼弱”的由衷喜悦和勤于民事的几多热望的话;那么秋风数度,当诗人又在“萧水、章门三日路”的公务往返中迎来衰飒秋日的时候,却再没有多少令他欣慰的事了——岁月蹉跎,年光如流,壮盛有为的四年多,就这样,逐水”逝去。眼看就要临近老年,怎能不感到深深的怅惘?此诗开篇以“垂老”映对“秋”节,引出“年光一逝去的幽幽慨叹,正表现着许多仕人步入衰秋时共有的苦涩之情。
而且诗人又是在孤舟客宦之中。如果遇上的是“秋风兮婿姻”的晴和之日,则船行江河之间,鸥飞白帆之上,虽说也难免会感到“水阔孤帆影,秋归万叶声”的清寥,毕竟还有青峰黛峦可眺、麦气豆香可赏.现在却是“阴云”沉沉、“急雨”敲篷,诗人所见副的,便只有岸草的瑟瑟偃伏和滩舟的颠荡乱雨之景了。“阴云沈岸草,急雨乱滩舟”二旬,即从眼前实景落笔,勾勒了一幅令人犯愁的动态画面。作为诗人孤消身影的黯淡背景,恰可有力地点示,诗人此刻的心境已变得怎样阴郁和纷乱。
施闰章是一位优时悯乱之士,他的思绪,无疑要比寻常的羁旅之客深沉得多。这些年来,国家时局仍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晚明桂王虽已被吴三桂征平,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义师,却依然坚持着悲壮的抗清斗争。为了安靖东南,清政府调动重兵,屯驻江浙皖赣一带。康熙三年秋七月,还发动了钲台湾”之役。施闰章对动乱的时局颇为担忧,在《中秋对月》诗中,即发出了“好酌清尊满,休教恨白头。不知今夜月,几处战场秋”的叹息。但身为一介饱读“诗书”的文士,他对安定苍生又能有多大作为?“时事诗书拙,军储临海。
这首诗咏闺怨。全诗没有透出一个“怨”字,只描绘清秋的深夜,主人公凄凉独居、寂寞难眠,以此来表现她深深的幽怨。诗是写女子别离的悲怨,蘅塘退士批注:“通首布景,只梦不成三字露怨意。”
诗所写的是梦不成之后之所感、所见、所闻的情景。全诗象是几种衔接紧密的写景镜头,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冰簟、银床、碧空、明月、轻云,南雁、潇湘,以至于月光笼罩下的玉楼,组成了一组离人幽怨的秋夜图,渲染了一种和主人公离怨情绪统一和谐的情调和氛围。诗中虽无“怨”字,然而怨意自生。
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很含蓄。瑶瑟,是玉镶的华美的瑟。瑟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在古代诗歌中,它常和别离之悲联结在一起。题名“瑶瑟怨”,正暗示诗所写的是女子别离的悲怨。
头一句正面写女主人公。冰簟银床,指冰凉的竹席和银饰的床。“梦不成”三字很可玩味。它不是一般地写因为伤离念远难以成眠,而是写她寻梦不成。会合渺茫难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本属虚幻的梦寐上;而现在,难以成眠,竟连梦中相见的微末愿望也落空了。这就更深一层地表现出别离之久远,思念之深挚,会合之难期和失望之强烈。一觉醒来,才发觉连虚幻的梦境也未曾有过,伴着自己的,只有散发着秋天凉意和寂寞气息的冰簟银床。—这后一种意境,似乎比在冰簟银床上辗转反侧更隽永有情韵。读者仿佛可以听到女主人公轻轻的叹息。
第二句不再续写女主人公的心情,而是宕开写景。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清寥淡远的碧空夜月图: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光似水,只偶尔有几缕飘浮的云絮在空中轻轻掠过,更显出夜空的澄洁与空阔。这是一个空镜头,境界清丽而略带寂寥。它既是女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和背景,又是她眼中所见的景物。不仅衬托出了人物皎洁轻柔的形象,而且暗透出人物清冷寂寞的意绪。孤居独处的人面对这清寥的景象,心中萦回着的也许正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类的感触吧。
“雁声远过潇湘去”,这一句转而从听觉角度写景,和上句“碧天”紧相承接。夜月朦胧,飞过碧天的大雁是不容易看到的,只是在听到雁声时才知道有雁飞过。在寂静的深夜,雁叫更增加了清冷孤寂的情调。“雁声远过”,写出了雁声自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渐渐消失在长空之中的过程,也从侧面暗示出女主人公凝神屏息、倾听雁声南去而若有所思的情状。古有湘灵鼓瑟和雁飞不过衡阳的传说,所以这里有雁去潇湘的联想,但同时恐怕和女主人公心之所系有关。雁足传书。听到雁声南去,女主人公的思绪也被牵引到南方。大约正暗示女子所思念的人在遥远的潇湘那边。
“十二楼中月自明”。前面三句,分别从女主人公所感、所见、所闻的角度写,末句却似撇开女主人公,只画出沉浸在明月中的“十二楼”。《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引应劭曰:“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此仙人之所常居也。”诗中用“十二楼”,或许借以暗示女主人公是女冠者流,或许借以形容楼阁的清华,点明女主人公的贵家女子身份。“月自明”的“自”字用得很有情味。孤居独处的离人面对明月,会勾起别离的情思,团圆的期望,但月本无情,仍自照临高楼。“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诗人虽只写了沉浸在月光中的高楼,但女主人公的孤寂、怨思,却仿佛融化在这似水的月光中了。这样以景结情,更增添了悠然不尽的余韵。
这首写女子别离之怨的诗颇为特别。全篇除“梦不成”三字点出人物以外,全是景物描写。整首诗就象是几个组接得很巧妙的写景镜头。诗人要着重表现的,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具体心理活动、思想感情,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组合,渲染一种和主人公相思别离之怨和谐统一的氛围、情调。冰簟、银床、秋夜、碧空、明月、轻云、南雁、潇湘,以至笼罩在月光下的玉楼,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清丽而含有寂寥哀伤情调的画图。整个画面的色调和谐地统一在轻柔朦胧的月色之中。读了这样的诗,对诗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也许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但那具有浓郁诗意的情调、气氛却将长时间留在记忆中。
回到诗题。“瑶瑟怨”不仅仅暗示女子的别离之怨,同时暗示诗的内容与“瑟”有关。“中夜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籍《咏怀》),写女主人公夜间弹琴(瑟)抒怨也是可能的。如果说温诗首句是写“中夜不能寐”,那么后三句可能就是暗写“起坐弹鸣琴(瑟)”了。不过,写得极含蓄,几乎不露痕迹。它把弹奏时的环境气氛,音乐的意境与感染力,曲终时的情景都融化在鲜明的画面中。弹瑟时正好有雁飞向南方,就像是因瑟声的动人引来,又因不胜清怨而飞去一样。曲终之后,万籁俱寂,惟见月照高楼,流光徘徊。弹奏者则如梦初醒,怅然若失。这样理解,诗的抒情气氛似乎更浓一些,题面与内容也更相称一些。
这首词虽然是容若无聊之时所写,但所写的内容依然离不开一个“愁”字。“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在夜晚起风的时候,吹动了护花铃铛,在碧山亭里的人听到了这铃声。远山之中,小小的亭子中,站着一个满怀愁绪的人。他独自想着心事,忽然听到风吹动铃铛,发出声响。那声响如此孤寂,简直要比独站山中还要孤寂。
这是容若心事的开头,他站于亭子中央,沉默望山,郁郁往事缠绕在容若心头,无法散去。本就十分忧愁,偏偏还听到了那孤寂的铃声,更是愁上添愁,更何况这山中的泉水声、雨声相互夹杂,混杂到一起,更是让人不忍去听。
“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这是一句写实的词句,更是一句无可奈何的阐述。但是词人却无处可躲,世界之大,无处清静。容若有着独一无二的才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他不为所累,想要遗世独立,可是照此看来,他如何能够独立,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出世者自说自话的一个圆满的谎言罢了。
容若这首词,上片是写山间声响,下片则是开始了对现实的抒情。“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自己的心究竟能告诉谁。“无聊心绪”,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一个天真忧郁的男子,在最好的年华,却是已经往事萦怀。
只怕只有这世间难得的真情,会让他动心,在春日里,容若只身立于山中的亭子下,看着远山,听着寂寞的声响,伤怀。仅此而已。容若就是这样,简单地生活着,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都不需要理由。
“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这份忧伤或许入梦可以缓解,但是那山中的响声,又生生地将梦叫醒。找不到一个毫无烦忧的地方,这也是纳兰疑惑的地方。
孙竞称周紫芝的《竹坡词》“清丽婉曲”。这首《鹧鸪天》可以安得上这个评语。词中以今昔对比、悲喜交杂、委婉曲折而又缠绵含蓄的手法写雨夜怀人的别情。上片首两句写室内一灯荧荧,灯油将尽而灯光转为暗红,虽说是乍凉天气未寒时,但那凄清的气氛已充溢在画屏帏幕之间。这里从词人的视觉转到身上的感觉,将夜深、灯暗而又清冷的秋夜景况渲染托出。
“梧桐”二句,写出词人的听觉,点出“三更秋雨”这个特定环境;此系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词意:“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满满,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词直接写雨声,间接写人,这首词亦复如此。这秋夜无寐所感受到的别离之悲,以雨滴梧桐的音响来暗示,能使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感受更富感染力量。所谓“满满声声是别离”,与欧阳修的“夜深风竹敲秋韵,万满千声皆是恨”(《玉楼春》)异曲同工,都是借情感对声音的反应表达由此构成的心理影响。那“空阶滴到明”和“满满声声是别离”,同样都是为了更深入地刻绘出别离所带来的悲苦心情。
换头“调宝瑟”三句展开回忆,犹记当年两人相对而坐,伊人轻轻调弄弦索,自己则拨动着金猊炉中的香灰。两人低声唱起那首鹧鸪词,乐声悦耳,歌声赏心;这恐怕是聚首期间最难忘的一幕了。联系着这段美妙往事的纽带是这支鹧鸪词,仍然是音响,不过这是回忆中的歌声和乐曲声,并非现实中的秋雨声。下片回忆中的欢乐之音与上片离别后的凄凉雨声,构成昔欢今悲的鲜明对照,真是袅袅余音只能引起悠悠长恨了。
结末“如今”两句,是使词意转折而又深化的着力之笔。“如今”两字,由“那时”折回眼前。那时同唱小调,如今却独居西楼,唯闻风声萧萧,雨声滴滴;“不听清歌也泪垂”,以未定语气呼应上片末句,显示了词人心头的波涛起伏;自从别离以后,经常闻歌而引起怀人的伤感,记忆中的美妙歌声无时不萦回耳际,而在今夜那风雨凄凄、“万满千声皆是恨”的情况下,即使不听清歌也就足以使人泪下而不能自止了。这里转折词意,也是为深化词意,暗示出从曲终人不见、闻歌倍怀人到不听清歌亦伤神的内心感情变化,以悬念方式道出对伊人的情之深,思之切。
周紫芝在另一首《鹧鸪天》词的小序里指出:“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体制者。”可以拿晏几道的《鹧鸪天》来作一比较:“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上片写昔年相逢于豪筵之前,下片叙别后思念。末两句先直说今夜重逢,本为久别再见,应该十分欢欣,只因以往失望次数太多,反而相对而不敢相信。一个“恐”字,转折词意,把惊喜怀疑的神情表现无遗,不仅道出相逢前相思之苦,而且通过疑真为梦,反映了目前的相逢之乐更是不同寻常。这种写法是直说而仍有转折,有感情起伏。
两者相比,这首词所采用的手法,如昔与今、喜与悲、正面说与反面说等等手法,做到委婉曲折而又含蓄深沉,确乎从小晏词变化而来。特别是末尾两句,以“如今”作为“昔与今、喜与悲”的转折词,以否定语气点出别离之苦,再相见之难,较直说更易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