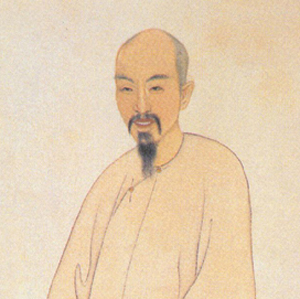《度关山》一诗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其内容讲的是执政者要勤俭、爱民、守法。曹操用法严峻,有犯必纠,这是一种法家精神,他反对滥用刑罚,提出要依法而行。曹操提倡节俭,《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不好华丽,后宫衣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俭为共德”是作者极力提倡的。
此诗开头直接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凸现了诗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接着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贤明,制定法规,全国统一,以奢侈为大恶,以俭朴为美德。退昏庸,举明智,官吏尽职,百姓安定,人口繁息,设立刑狱,执法正当。人与人之间,退让不争,上下相同,彼此亲爱。
全诗表达了诗人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思想,诗人并写两面,一是通过叙述古代君主治民的法则,认为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二是通过尧舜之间的对比,提出纠正“侈恶之大”的方式,即“俭为共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从中可见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愿望。
这首诗在内容上,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蕴涵着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在写作上,除了采用正面颂扬的形式之外,“嗟哉后世”八句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比,肯定了民本思想,揭示了奢华造成的后果。
这是一首以近于俚俗的语言写成的相思之作。与同类题材不同的是,这首词中词人与恋人可能是因了一点小事呕了气,于是二人“轻分手”了。如今,他深悔自己当初的轻率,独自度着难捱的长夜,内心涌起一浪一浪的情感波澜。
柳永抒情往往上片铺叙景物,下片为内心独白。而这首词景语仅“床前残泪烛”一句,余皆情语,则所抒之情倍觉突出、充盈,亦可见此情非由外物触起,实是无时不萦系心中。上片以“梦觉清宵半”开头,先点明时间乃“夜半”,主人公的情状难以再眠。于是以下借“银箭”、“残沿烛”、“鸳被”三种意象写事叙情,三种意象与主人公的行动紧紧联在一起,“银箭”在这里代指古代计时漏壶滴漏的声音,它表示时光在一秒一秒地缓慢行进,此刻,词中的主人公正屈着指头细数这单调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深夜无眠的寂寞无聊。蜡烛已将燃尽,烛泪将残,表示夜已深,只有烛泪“啼红”相伴主人,进一步写出主人公的孤单。“鸳被”本象征男欢女爱,而今,主人公却是“孤眠”,昔日的欢爱自是不堪回首,所以一人在被中“展转千余遍”,任凭它是“数重”,仍觉“不暖”,再次写出词人内心的凄凉。三种意象成为叙事叙情的关键物。在上片中,三种意象又以直接写情写事的句子相串联。首句直写主人公夜半即醒,难以再眠,引出第一个听觉的意象“银箭";长夜不眠再出现第二个视觉意象“残泪烛”,视觉听觉的双重意象引出“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的情语,直抒旧日欢情带来而今无限的愁恨。从旧日欢情联及“鸳被”这一意象,于是“展转千余遍”,“孤眠不暖",写尽孤独寂寞的难耐。
下片直抒其情,先以“堪恨还堪叹”一句总写这一段不了情缘引发的种种情味,然后分写内心的层层情感波澜。后悔“当初不合轻分散”是为一层,此句化用许岷《木兰花·小庭日晚花零落》:“当初不合尽饶伊,赢得如今长恨别。”虽用典,亦写实;“厌厌独自”一人,盼伊人盼得“眼穿肠断”是为二层,前一层不过后悔而已,此时却已经相思成病;由于“眼穿肠断”而想到昔日的“深情蜜意如何拚”是为转折后的一层;再想及当日虽有重聚的“后约”,但毕竟而今“片时难过”,是为再转折后的一层;直至“怎得如今便见”是最后深悔当初又盼今后的最后一层。一层进一层,一浪高一浪,把内心的百转千折细细密密地铺展开来。这种相思虽然说不上有什么价值,但在词中表现得自然真切,很富有生活气息 。
生活中,一对相恋的人因为偶然的小事而分手,分手后又后悔当初决定的草率者,并不少见。抛开词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词中抒发的情感还是能引起人共鸣的。
七夕是中国传统节令之一,相传在七夕的晚上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据《荆楚岁时记》记载,这天晚上,妇女们纷纷以彩色线穿七孔针,于庭院中陈列瓜果乞巧。民俗流风所及,七夕也成为六朝诗人咏歌的热点。除了歌唱牛郎织女外,“七夕穿针”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梁简文帝萧纲诗“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刘遵诗“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柳恽的《七夕穿针》,虽然题材也是传统的闺怨,但比起前面各家来,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意境也开拓得较深。
诗歌发端“代马秋不归,缁纨无复绪”,且不提七夕穿针,而先说明丈夫从军代地(今河北、山西北部),妻子独处闺中,各色衣裳,无心料理。然而瞬间已到七夕,须为丈夫打点冬装,于是归结七夕穿针这一诗题:“迎寒理衣缝,映月抽纤缕。”旧注引《周礼·春官》中“中秋夜,击土鼓、吹豳诗以迎寒”解释“迎寒”,似乎牵强。这两句诗使用修辞中的“互文格”,即“映月迎寒,抽纤缕理衣缝”,在月光下迎夜凉、穿针孔、缝衣衫。单纯的穿针娱乐变为实际的裁衣寄远,于是民俗与社会问题浑融浃洽,天衣无缝。下文便描写女主人公飞针走线时的容貌神情。“的皪寒睇光,连娟思眉聚。”的皪,光亮鲜明。连娟,纤细弯曲。眼波媚丽,奈何凝寒远望;眉山春妍,只是紧蹙不舒。全无佳节兴致,更添独居抑郁。这是人物的正面描写。接着诗人再从侧面对环境进行渲染:“清露下罗衣,秋风吹玉柱。”玉柱,这里代指筝瑟等乐器。罗衣沾露,只为伫立已久,可见时已夜深。秋风拂弦,可见心绪撩乱,置琴不顾。清露点点,微响悠悠,两句勾勒出一片凄清氛围,蕴含着恍惚失神的人物形象。结尾转到人物心理:“流阴稍已多,馀光亦难取。”一夜光阴大半流逝。残夜馀光欲留无计。寥寥十字,辞约义丰,既是慨叹牛郎织女欢会短暂;又是自伤良宵虚度,比之牛郎织女,尤为不及。这两句将节日与日常生活收束合一,将人生感慨与神话传说收束合一,将世间凡人与天上星宿收束合一。神韵超远悠渺,耐人寻味。
此诗的人物描写,堪称细腻。随着时光的推移,由夜晚到中宵再到残夜,或是穿针缝衣的举止,或是颦眉含寒的神情外貌,或写幽清环境,或状嗟伤心绪,移步换形,内涵充实。从而使整首诗歌也显得清隽雅丽,卓然出群。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说的,“柳吴兴诗如月华既圆,云散相映,光气满足。”(《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五)
李煜另一首《望江南》(多少恨)用的是以反写正的艺术手法,以乐来反衬苦,笔意有曲婉之感。但这首《望江南》(多少泪)则不同,是直笔明写,正见正写,直抒胸臆,坦吐愁恨的艺术手法,因而有愈见沉痛之感。二词可同读,对作者的忧思愁恨则体会更深。
“多少泪”即“多少恨”之续写,“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后,悲情更苦,离恨更深,作者再也无法自制,只能任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了。眼泪纵横当不是抽泣哽咽,而是激情难收,也许有号啕之举,但是,泪可流,“心事”却不可说,一是满腔悔恨无法说,二是故国情怀不能说,自伤之情、囚居之苦,片言俱现,作者心中愁苦跃然纸上。不但“心事”不可说,连往日可以寄托情思的凤笙也不能吹起,这种痛苦和不自由是非常地残酷。古人悲思不可解,常有“欲将心思付瑶琴”(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之想,而这情此景,作者却连这一点奢望都不敢有。况且,凤笙向来为欢歌之用,于此时吹奏,对李煜来讲,只是徒增感慨、更添思忆而已,所以一句“休向”,使作者的幽居无奈中又多添了几分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乎,“肠断更无疑”但是惟一的结局了。这首词正是李煜入宋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真实写照。
全词与“多少恨”同调,取笔不同但取意同。这首词直接写作者深沉痛苦,描摹细致,语言直朴,较“多少恨”有更直入人心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