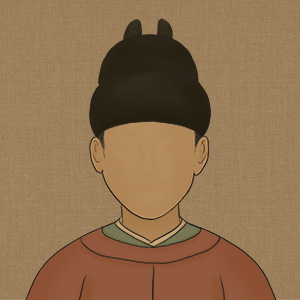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诗的前六句写离别时的送别场面,运用顶真修辞手法,将这几句一线贯穿。接连出现两个“离声”和“涕零”。增强了诗的缠绵悱恻之情。给诗定了沉郁的基调。诗的首句,借用惊弓之鸟的典故,用以比喻“倦客恶离声”——久倦羁旅的游子最厌恶、最害怕的便是离歌之声,勾出倦客恶离别的心理状态。为突出其表达效果,连用两个“恶”字来充分烘托游子极度厌恶、畏忌远行的气氛,既增强了类比性,也加重了感情色彩。但是,“恶”之偏至,这就是人世间之所以有不幸的一个原因吧。第三句的开头便用“离声”二字顶上,声情之急,节奏之紧,直令人难以喘息。“离声”一出,不仅去者伤情,就连送行的宾客和驾车的仆夫亦不禁潸然泪下,诚所谓“一曲离歌两行泪”,“天涯去住各沾巾”。此情此境,行子更难自持,只见他伤心落泪,挥泪而去,去去又回,依依话别。这几句由声而写到情,由己之情写到宾御之情,由宾御之情再回到己之情,回环往复,层层递进,把那种两情互感的情绪、场景和气氛,表现得一气贯注,淋漓尽致,以上将离情写足。下面两句说片刻的分离都会使人难受,何况是远游异乡的长久别离呢。叙议结合指出如此离伤的原因。应该说这个议论也是充满真情实感的,所以谭元春说它“甚真甚真,有情人之言”(《古诗归》)。因果相依,不着痕迹地为诗的上一段作了小结。同时,“异乡别”又为下一段写离乡远行之况作了准备。这种“住而未住”、“藕断丝连”的转接方式,很像词中的“过片”。可以想见词中的一些艺术手法,在诗人的创作中早有实践,只不过没有明确地上升为一种文学形式(词)中的自觉的艺术法则。
诗的第二段说车儿在漫漫长途上远行,颠簸摇晃了一天,又是日落黄昏,夜幕笼罩了静寂的大地,眼看周围的人家都掩门入睡了,可是远行的游子直到半夜才盼得一顿晚餐。黑夜里,听着野风呼号,草木哀鸣,更令人肝肠寸断。这几句由白天而写到夜晚,其间有人、有事、有景、有情,脉络清晰,丰而不杂,将行役之苦写得历历在目。“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两句引向对游子征途中苦难生活的描述。“遥遥征驾远”以下六句,游子驱车不停地走向遥远的地方,白日杳杳又到傍晚了。这个时候,在家的人早已关起门来唪觉,而在外的游子,午夜还在做饭。野外的寒风吹动草木,发出萧萧的声响,游子不由悲从心生,肝肠欲断。诗人这几句诗,写出了漂泊天涯,流浪江湖游子的真实感受。“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两句,诗人运用平常的事物,从衣、食这两个角度做比,写出游子在外的“酸”、“苦”,耐人寻味。这里突然插入两个比喻——吃梅总觉得酸,穿着葛麻布衣总是难以御寒的——这必然之理人人皆懂,然其酸、寒之状,他人难言,而只有食者、衣者自知。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必然”与“自知”。行役之苦,只有行子自知,自伤自苦,真切深刻,更为感人;而“必然”又为下文设置了前提,食梅苦酸,衣葛苦寒,一如人情苦别,乃事之必然,无法回避。即使在宾朋满座,丝竹盈耳之时,忧伤的游子亦无法表现出一丝欢颜,正是“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张谓《送人使河源》)。有时候自己也想长歌自慰,但其结果呢,只有引来更深长的愁恨。这就意味着不论客观环境如何,亦不论主观努力如何,行子之愁,愁不可销。诗人总是力图透过离愁表象的描述,以回折顿挫的笔法,将诗思引向更深刻更概括的情理之中;诗中的比喻用得灵活生动、自然贴切,有的能领起全篇,有的则能网络上下,在情理表达,叙事逻辑,章法结构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四句诗人满腹忧愁,坐于席上,即便丝竹满座,仍不能忘掉忧愁。要唱辞长歌来聊以自慰,哪知更牵动起心中的悲苦。可这仅仅是“长恨”的开始,日后苦难“万端”会源源不断涌来,腹中悲苦,难于化解,足见其悲苦之深重。
诗歌开篇就用了一个新奇惊人的比喻,把疲于奔波的人对再一次起程比为惊弓之鸟。鸟是因为身体受伤,而人则是心里受伤。因此,当受伤的心再一次听到别离之声,立时紧张而痛苦,完全没有宴饮的心情。再想到自己别离后的遥遥征程,曾经奔波的情景一时跳入脑海。而在傍晚时分,更是令人心碎。别离之后,一边是亲友家人的无尽孤独,一边是游子茫茫的征途。想到这些,再好的东西,都无法下咽,再动听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那忧伤的心情,那痛苦的脸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开解了。最后,诗人说,本想振作起来,唱一支歌,自我宽慰,但未曾想到,长歌未尽,憾恨之心再起。这首诗诗人巧妙化用典故,合理运用顶真修辞渲染烘托气氛,格调沉郁,感情真挚。
此词咏七夕。上片遥念仙侣欢会。先写新秋夜色。凉月横舟,银河浸练,碧空如洗。次写双星相会。桥倚高寒,鹊飞碧空,绵绵离恨,欢情几许;千秋今夕。下片抒发感怀。夜色沉沉,独感岑寂,回忆昔日,亭榭穿针,金鸭香袅。而今玉徽尘积,新凉半枕。窗外泪雨,檐前犹滴。不禁感慨万千。
全词构思精巧,抒情细腻,情景交融,真挚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