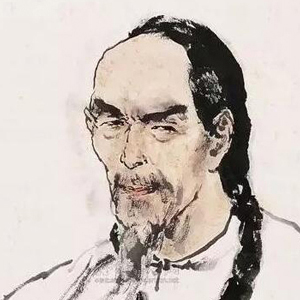这首词上片由梦阑起,接以幻象的描绘,表达了痴情思念的哀伤。下片由物及人,写物是人非的伤情。全词抒情委婉深挚,一波三折,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由梦阑起,接以幻象的描绘,表达了痴情思念的哀伤。
首句“欲话心情梦已阑,镜中依约见春山”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悲凉之感。梦已醒,词人与情投意合的妻子生死两隔,把唯一能相会的希望寄托在梦里,词人多次提到梦中与亡妻相会。可是此次,正要与妻子说说知心话,谁料话未及说,梦就醒了,只剩孤独的身影,冰冷的黑夜,让词人无比惆怅。醒来后词人再无睡意,看看四周的摆设依然,在镜子里好象看到了妻子的倩影。
下句“方悔从前真草草,等闲看”写词人的心理活动,“悔”字是词人情感和心理的写照,词人后悔的是在妻子生前没有认认真真地欣赏她、关心她,没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下片对句益发沉重,由物及人,写物是人非的伤情
环佩只应归月下,钿钗何意寄人间”,容若连用两个典故,并反用其意,说旧时故物何必再见,徒然惹入伤感,不能自拔。这样的话,自是“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愈见其心情沉痛。这两个典故同时还点明:伊人已逝,心期难再。词义到此而明朗,自是为卢氏的悼亡之作无疑。
末句“多少滴残红蜡泪,几时干”明说蜡烛流泪,实指自己泪涟;明问蜡泪几时干,实叹自己伤痛几时能淡。词句暗用义山之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所以,问蜡泪几时干实属明知故问,容若明明知道蜡烛要等到成灰之时泪才会干,也明明知道自己要等到生命结束之日才会停止对亡妻的思念。
常人写这类题材,大致是先叙湖上景致,然后因景抒情。而作者却不循常套,起笔不谈游湖,而先从身世感慨人手。首三句“天风吹我,予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气势宏大,姿态超迈。作者不说自己出生杭州,却说自己是被天风吹落于此的。他是天上的谪仙,身在人间,神在天表,只不过西湖风光的清丽令他满意,他才不想返回天界。这三句,才写到作者的诞生,但却已将他的自命不凡、高视阔步、超凡绝俗之态写出,一种豪迈飞扬的气概,跃然纸上。有这三句定下基调,下面几句就看似惊人而实无足惊奇了。“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之所以说他只是北京城中一个客居的弱冠少年,却不说仕途不得志之苦、不抒少年意气,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首往事时有无限苍凉迷茫,就是因为他是谪仙,胸襟广、目光远,所思者大。“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像樊哙那样建功立业、像驺奭那样立言传世,乃是无数古人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他却说那些都不是他的平生之志,也因为他是谪仙,来到人间乃是为了大济苍生、重振乾坤。战场上的一刀一枪,书堆中的寻章摘句,他当然是夷然不屑的。不过,他这番心比天高的志向抱负,常人是不会懂得。“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就连坟地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地下有知,也肯定会笑作者全然打错了算盘。阅尽人世的小小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论了。
词至上片末尾,豪情已转为孤独之感。过片才写到游湖。“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但他笔下的西湖,乃是与他心境相合拍的西湖,他满怀清愁,所以刚刚看到“一抹”斜阳、“半堤”春草,这愁怀就顿时被惹逗起来了。斜阳芳草,自古都是伤心物,作者在此并未超越前人,但连用了“一抹”、“半堤”、“才见”、“顿惹”,词情便有无限含蓄,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接下“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前者用曹植《洛神赋》“罗袜生尘”之典,后者语本苏轼《前赤壁赋》“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歌。既是泛舟湖上,自不免极目远望,但作者所望也不同凡俗,他望的是“美人”——理想的化身。然而,“何处觅”、“予怀孤寄”,他未能望到理想的归宿所在,满腔情怀亦不知何处吐泄。
词至此,已由豪迈而入孤独,由孤独而入忧愁,由忧愁而入怅惘。经此几番情感转折,终于唤出了全篇的名句:“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怨”,是指他胸怀大志却无人领会、无处施展的怨愤;“狂”,是指他心中汹涌澎湃的狂潮,这狂潮中有高超的见识、有宏大的构想、有急切的愿望,包含之多,实难尽言。欲怨之去,就吹上一曲缠绵悠远的箫乐,让那怨愤随风飘逝;狂来奈何,就舞出一派熠熠生辉的剑光,让心潮在浩荡剑气中暂趋平伏。这一箫一剑,其中包蕴了作者多少失望和希望、痛苦和兴奋;抚起箫、挥起剑,这中间的滋味,令作者魂为之销。相形之下,功名、文名的“两般春梦”算不得什么,就让它们随着橹声飘荡进云水之间。
这首词全盘托出了少年龚自珍的雄心、抱负和自信、自负,是龚词的代表之作。其中核心的箫、剑二句,尤为后人所称道。有人说,这两者分别代表优美和壮美,而作者一身兼有之,实乃不世出之奇才。有人说,这两者代表了作者个性的两个方面,一深远,一宕落。龚自珍一生的行事,亦可以“吹箫”、“说剑”括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他虽然自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似乎剑已涩、箫已折;其实,这仍然只是在“吹箫”而已。上引二句出自《己亥杂诗》,而他在同一组诗中大声疾呼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依然是“说剑”的雄姿。
此诗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嗣子不肖而叹息,尾联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词精警凝炼,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