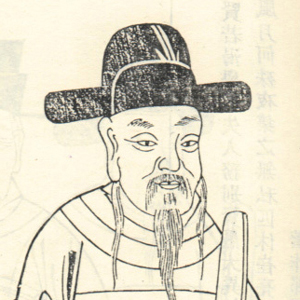此词是一首离情词。当是托为妓女送别情之作。送者有意,而别者无情,从送者的角度来写,写尽其痴人痴情。
“留人不住”四个字将送者、行者双方不同的情态描绘了出来:一个是再三挽留,一个是去意已决,毫无留恋之情。“醉解兰舟去”,恋人喝醉了,一解开船缆就决绝地走了。“留”而“不住”,又为末两句的怨语做了铺垫。
“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二句紧承“醉解兰舟去”,写的是春晨江景,也是女子揣想情人一路上所经的风光。江中是碧绿的春水,江上有婉转的莺歌,是那样的宜人。当然,景色的美好只是女子的想象,或许更是她的期望,即使他决然地离开了她,她也仍旧希望自己的情人在路上有美景相伴,可见痴情至深。“过尽”两个字,暗示女子与恋人天各一方的事实,含蓄透露出她的忧伤。
“碧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情人已经走了很久,不见踪影,但女子依旧站在那里。堤边杨柳青青,枝叶茂盛繁多,千丝万缕,依依有情,它们与女子一起伫立于碧口,安静凝望远方。古人有折柳枝送别的习俗,所以“枝枝叶叶”含有离情的意思,此处即借杨柳的枝叶来暗示女子黯然的离情。
“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所表达的感情非常激烈。女子负气道:“以后你不必给我寄信了,反正我们之间那犹如一场春梦的欢会没有留下任何凭证,你的心里也没有我的位置。” “画楼云雨”四个字道出了女子与男子曾经的美好过往,只可惜男子决然绝情。相守的期盼落空之后,她只有怀着无限的怨恨选择放弃,从特意提及“锦书”可知,女子内心并不想如此决绝,只是无可奈何罢了。
这首词在技巧上运用了很多对比方法:一个苦苦挽留,一个“醉解兰舟”;一个“一棹碧涛”、晓莺轻啼,一个独立津碧、满怀离情;一个意浅,一个情深,让人一目了然。在结构上,亦是先含情脉脉,后决绝断念。结尾二句虽似负气怨恨,但正因为爱得执著,才会有如此烦恼,所以更能反衬出词人的一片痴情。总之,此词刻画细腻,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一个女子痴中含怨的微妙心理。
此诗是看到眼前景物而抒写作者的愁怀:江边的丛草每天在生长起来,都在唤起我的愁绪。巫峡中泠泠流水,也毫无人情,惹得不能开怀。白鹭在盘旋的水涡中洗浴,你们有些什么愉快的心情呢?一株性独的树正在开花,也只有你自己高兴。这四句是描写一个心绪不好的人,看了一切景物,都烦恼得甚至发出诅咒。“世情”是唐宋人俗语,即“世故人情”。“非世情”或作“不世情”,即不通世故人情。在这句诗里,可以讲作“不讨好我”。“底”字也是唐宋俗语,用法同“何”字,是个疑问词,即现代汉语的“什么”。“分明”二字与杜甫在别处的用法有些不同,意义较为含糊。大约强调的是“自”字。现在释为“自己高兴”,还是揣测,恐怕似是而非。
诗的前四句写景,后四句转到抒情。诗人说,十年来兵荒马乱,使南方成为黑暗的地区,我这个异乡来的旅客,衰老在夔州性城中,很想回长安去,可不知渭水秦山,这一辈子还能再见不。因为人已老病,而路上仍然是豺虎纵横。最后两句愁的是人民生活的艰辛,自己也无法还乡。
这首诗意义很明显,没有曲折隐晦之处。前四句虽然写景,但与《登高》《返照》二诗的前四句不同。作者已在写景之中表现了自己的“愁”,不是客观的写景了。每一句的艺术手法都表现在下三字。“暗”字也是杜甫的独特用字法。末句“虎纵横”是指上文的“十年戎马”。《杜诗镜铨》引张璁说:“虎纵横,谓暴敛也。时京兆用第五琦十亩税一法,民多流亡。”浦江清《杜甫诗选》亦用此说作注,以为末句是“借喻苛政”。这是从诗外去找解释,大约脑子里先有一句“苛政猛于虎”,看到杜甫的“虎纵横”就附会到苛政上去。于是再从唐史中寻找当时有什么苛政。于是找到了第五琦的新税法。不知杜甫诗中屡次以豺虎比兵灾。此处的“虎纵横”显然是照应上文的“十年戎马”,杜甫应该不会忽然丢开上文而无端扯到第五琦的苛政。毛大可论读《西厢记》的方法说:“词有词例。不稔词例,虽引经据史,都无是处。”读诗也是这样。诗也有诗例,不从诗中去求解,而向诗外去引经据史,决不能正确地解得这首诗。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一首诗中,偶尔有一、二处平仄不合律谓之失粘。失粘之病,有时是作者平时读字音不准,弄错了平仄;有些是故意的,这就称为拗句。《愁》这首诗全是拗句,这就是吴体。这种拗法,只有在七言诗中出现,它们是律诗的形貌与古诗的声调的混血儿。
此诗的前四句写秋夜天宇和金陵远景。起首二句:“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绳。”一问一答,天真活泼,明快自然,饶有民歌风味。诗人仰望秋空,看到在这寥廓空明的天宇上远远地闪烁着两颗银亮的玉绳星。三四两句写玉绳星照耀下的金陵城。诗人放眼远眺,但见玉绳星斜斜地、低低地嵌镶在建章宫高大的楼阙旁边,发出格外耀目的光芒,对着整个金陵古城。这四句从大处落墨,先写天空,后写地面,连接自然,展现出碧海般的青天,白玉般的明星,以及星光照耀下的金陵城巍峨宫阙的剪影,境界空阔高远,正融注了诗人秋夜泛月时那种萧散自然、风流自赏的意绪。如果更深细地品味,这四句诗已隐隐透露,出怀念前代诗人谢朓的情思。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中,有“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等写景佳句,李白诗的三、四句,显然是有意点化了谢诗,借以寄寓对谢朓的缅怀、追慕。而且,这两颗璀灿的玉绳星,一颗斜照建章阙,一颗耿对金陵城,仿佛具有象征的意蕴。它们在浩渺秋空中互相映照,仿佛正是谢朓、李白这两位古今相通、精神契合的天才诗人的化身。
中间四句写秋江月色。这里“汉水”借指长江。诗人不说“长江”而说“汉水”,是为了避免同下句“霜江”字面重复和音声相混。在板桥浦信步泛月的李白,俯视着脚下的大江,但见清澄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像是一条银光闪烁的白练。此刻,谢朓描写大江黄昏美妙景色的诗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自然跳上心头。对景吟诗,使他产生一种悠然神远的感变,仿佛自己已超越古今的界限,同小谢一起联袂步月,同赏秋江美景,推心置腹地纵论人生、品评诗文了。李白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与古人神游的幻想境界里,以致忘怀了一切。他久久地凝望着明月逐渐西斜,月光如乳汁般倾泻在长江之中。直到月落星隐,天将破晓,朝雾弥漫洲渚,寒气侵袭发肤。这四句写秋江月色,明丽皎洁,清幽飘逸,动静相生,空灵迷人。而在这幅秋江月色图中,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这里表现出他的神态和心绪的变化:先是缅怀遐想古人,继而是与古人神游的畅快,接着是从遐想中醒悟过来发觉古人不可得见的寂寞与怅惘,这四句妙在不是静态的寓情于景和情景交融,而是从时间和景色的变化之中暗示出诗人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不着痕迹,纯乎天籁。
最后四句点明题旨,直抒胸臆。诗人在板桥浦自斟自酌,没有知音同欢共饮,虽追慕谢朓,但毕竟相隔数百年,谁也不能把古人找回来。而在当今现世,像谢玄晖这样才华高妙、志趣相投的人,是很难得再遇到的。想到这里,诗人深深感到孤独寂寞,挥杯洒酒无心再饮。一股悲凉抑郁之气,充满了他的胸中。结句暗用梁代诗人江淹《恨赋》“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句意,而融化无迹,如同己出。至此,诗人不仅婉曲尽致地抒写了对古人的缅怀遐思,而且借痛感斯人之不可复遇,宣泄出世无知音的深沉感喟。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