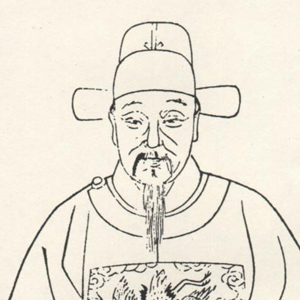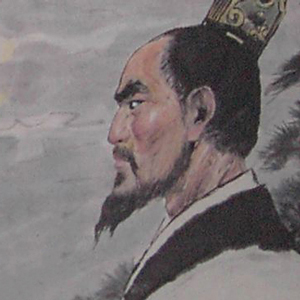也许是长久偏安于江左的青山绿水,不闻飞骑击虏、角声马鸣之故吧,南朝稍有壮心的文人士子,往往热衷于汉人出塞千里、勒铭燕然的军戎生涯和辉煌业绩。因此,仿“古诗”、叙汉事,借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慨,也成了他们作诗的一大爱好。范云这首诗,正以“效古”为题,倒转时空,把自身带入了六百年前边塞征战的戎马倥偬之中。
诗之开篇以粗放的笔触,勾勒了塞外严冬的苍茫和凛冽:“寒沙四面平”写浩瀚的飞沙,在翻腾如浪中猛然静歇,填平了四野起伏的丘谷。运笔静中寓动,极富气势。“千里飞雪惊”则又动中见静,让荒寂无垠的瀚漠,刹时被纷扬的飞雪所笼盖,境界尤为开阔。一个“惊”字,表现诗人的主观感觉。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塞外景象,正如《楚辞·招魂》所述:“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令人心骇而骨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诗人恍已置身于顶盔贯甲的汉卒之中,正冒着风雪,向茫茫阴山、皑皑交河进发。“阴山”横亘于今内蒙古境内,往东遥接内兴安岭。山上本来草木葱茏,而今在狂烈的寒风袭击下,时时可见高大树枝的摧折;“交河城”则远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正是车师前王的治所。此刻在雾气缥缈之中,它竟像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阴山到交河城,空间相距远不止千里。诗中却以“风断”、“雾失”两句,使之近若比邻。如此巨大的空间转换,不仅表现了塞外瀚漠的辽阔,更为活跃在这一背景上的士卒征战生涯,增添了几多壮色和扑朔迷离之感。
以上四句重在写景,豪情万丈的出塞健儿,似还只在背景中若现若隐。自“朝驱左贤阵”以下,他们终于大显身手了。“朝驱左贤阵”一句,写的是飞将军李广亲自指挥的一场激战。据《史记》记载,当时李广率四千骑出右北平,迎战匈奴左贤王十倍于己的骑兵。李广布圆阵拒敌,“胡急击之,矢下如雨”,“吏士皆失色”。而李广“意气自如”,执大黄弩射杀匈奴偏将数人,终于坚持到援军到来,突围而出。“夜薄(迫近)休屠营”抒写的,则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一次胜利远征。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一时名震遐迩。这两次战役,在时间上相隔五、六年。诗中却以“朝驱”、“夜薄”使之紧相承按,大大增添了塞外征战的紧张态势,将出征健儿勇挫强敌的豪迈之气,表现得痛快淋漓!接着“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二句,又回射上文,抒写主人公先后追随前将军李广、嫖姚校尉霍去病屡建奇功的经历。语气沉着,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身为名将部属的深切自豪感。
以上一节描述出塞千里、接战强虏的英勇业绩,读来令人神旺。不过,军戎生涯除了长驱直进的胜利外,也难免有意外的失误和挫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功业显赫的名将,也仍要受到军法的惩处。“失道刑既重”,说的正是李广晚年的不幸遭遇:李广率师出征,因为无人向导而迷失道路;大将军卫青追究罪责,李广终于含愤自杀。“迟留法未轻”,则指博望侯张骞,随李广出塞,迟留后期,按法“当斩”,只是由于出钱,方才“赎为庶人”。这样的失误,虽然难免,但军法如山,不可宽贷。这又使充满英勇气概的军戎生活,蒙上了一重悲壮的色彩。唯其如此,它才更加可歌可泣;在诗人眼中,也更富于浪漫气息和奇异的吸引力。汉代的边塞征战,正是这样,以它辉煌的业绩和悲壮的色彩,写在了汗青史上。何况,这些业绩,又是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分不开的。倘若不是他的果断决策,汉代则不能有此美善旺盛(休明)的壮举。所以,诗之结尾,诗人不禁发出了“所赖今天子(汉武帝),汉道日休明”的热烈赞叹。倘若联系诗人生活的齐梁时代,朝廷积弱,只能坐看北方异族铁骑纵横,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结句又包含了无限感慨和不尽之意。
“效古诗”名为“效古”,诗中其实总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范云身为齐梁诗人,写的虽为汉代古事,但因为用了第一人称,在时序上又故意倒“古”为“今”(“今逐”、“今天子”),便在诗中造成了一种古今错综、彼我交融的奇特效果。出现在诗中的主人公,看似汉代士卒,却又融入了诗人的感情。恍惚之中,似乎不是诗人回到了汉代,倒似当年的李广、霍去病,穿过六百年的时空,奇迹般地出现在南朝,正率领着诗人,仰对瀚漠的朔雪、狂风,转战于阴山、交河。而读者呢,也恍惚与诗人一起,参加了“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的战役,为胜利的突围而欢呼,为“失道”名将的陨身而堕泪。这是一种错觉,但它的奇特效果,正是由范云这首《效古诗》的独特表现方式所造成的。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