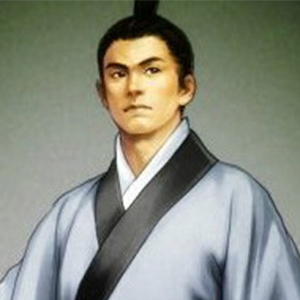这是一首访问山农的纪行六言绝句。全诗二十四字,作者按照走访的顺序,依次摄取了山行途中、到达农舍、参观焙茶和晒谷的四个镜头,层次清晰地再现了饶有兴味的访问经历。作者绘声绘色,由物及人,传神入微地表现了江南山乡焙茶晒谷的劳动场景,以及山农爽直的性格和淳朴的感情。格调明朗,节奏轻快,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句“板桥人渡泉声”,截取了行途中的一景。当作者走过横跨山溪的木板桥时,有淙淙的泉声伴随着他。句中并没有出现“山”字,只写了与山景相关的“板桥”与“泉声”,便颇有气氛地烘托出了山行的环境。“人渡泉声”,看似无理,却真切地表达了人渡板桥时满耳泉声淙淙的独特感受。“泉声”的“声”字,写活了泉水,反衬出山间的幽静。这一句写出农家附近的环境,暗点“过”字。“人渡”的“人”,实即诗人自己,写来却似画外观己,抒情的主体好像融入客体,成为景物的一部分了。短短一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仿佛分享到作者步入幽境时那种心旷神怡之情。
从首句到次句,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跳跃。“茅檐日午鸡鸣”,是作者穿山跨坡来到农家门前的情景。鸡鸣并不新奇,但安排在这句诗中,却使深山中的农舍顿时充满喧闹的世间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茅檐陋舍,乃“山农家”本色;日午鸡鸣,仿佛是打破山村沉静的,却更透出了山村农家特有的悠然宁静。这句中的六个字,依次构成三组情事,与首句中按同样方式构成的三组情事相对,表现出六言诗体的特点。在音节上,又正好构成两字一顿的三个“音步”。由于采用这种句子结构和下平声八庚韵的韵脚,读起来特别富于节奏感,而且音节响亮。
前两句可以说是各自独立又紧相承接的两幅图画。前一幅“板桥人渡泉声”,画的是山农家近旁的一座板桥,桥下有潺湲的山泉流过,人行桥上,目之所接,耳之所闻,都是清澈叮咚的泉色水声。诗中有画,这画便是仿佛能听到泉声的有声画。后一幅“茅檐日午鸡鸣”,正写“到山农家”。在温煦的阳光下,茅檐静寂无声,只传出几声悠长的鸡鸣。这就把一个远离尘嚣、全家都在劳作中的山农家特有的气氛传达出来了。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王维《新晴野望》)。这里写日午鸡鸣的闲静,正是为了反托闲静后面的忙碌。从表现手法说,这句是以动衬静;从内容的暗示性说,则是以表面的闲静暗写繁忙。故而到了三四两句,笔触便自然接到山农家的劳作上来。
“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两句是诗人到了山农家后,正忙于劳作的主人对他讲的表示歉意的话。诗人到山农家的前几天,这里连日阴雨,茶叶有些返潮,割下的谷子也无法曝晒;来的这天,雨后初晴,全家正忙着趁晴焙茶、晒谷。屋子里因为焙茶烧柴充满烟雾,屋外晒场上的谷子又时时需要翻晒。因此好客的主人由衷地感到歉意。
山农的话不仅神情口吻毕肖,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山农的朴实、好客和雨后初晴之际农家的繁忙与喜悦。如此本色的语言,质朴的人物,与前面所描绘的清幽环境和谐统一,呈现出一种朴素、真淳的生活美。而首句“泉声”暗示雨后,次句“鸡鸣”逗引天晴,更使前后幅贯通密合,浑然一体。通过“板桥”、“泉声”表现了“山”:既有板桥,下必有溪;溪流有声,其为山溪无疑。
前两句从环境着笔,点出人物,而第三句是从人物着笔,带出环境。笔法的改变是为了突出山农的形象,作者在“焙茶烟暗”之前,加上“莫嗔”二字,便在展现劳动场景的同时,写出了山农的感情。从山农请客人不要责怪被烟熏的口吻中,反映了他的爽直性格和劳动者的本色。“莫嗔”二字,入情入理而又富有情韵。继“莫嗔”之后,第四句又用“却喜”二字再一次表现了山农感情的淳朴和性格的爽朗,深化了对山农形象的刻画,也为全诗的明朗色调增添了鲜明的一笔。
六言绝句,由于每句字数都是偶数,六字明显分为三顿,因此天然趋于对偶骈俪,趋于工致整饬,绝大多数对起对结,语言较为工丽。顾况的这首六言绝虽也采取对起对结格式,但由于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进行白描,前后幅句式又有变化,读来丝毫不感单调、板滞,而是显得相当轻快自然、清新朴素,诗的风格和内容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美。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这首诗是欧阳修七律中的佳作。诗中不仅描写了三峡苍暗、明月满川的景象,揭示出峡川月夜的苍茫、辽阔、凄清之美;而且借助景物描写,抒发了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感受。这里,既有无辜被贬的深沉感慨,又有思乡怀归的惆怅之情。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自我解嘲,故作旷达。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写因贬谪之恨,而源溯到屈原,借以自喻而自慰,可终不能抑制这种生活的愁怨。“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写有如《秋色赋》,何其凄然。“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写客居异乡,苦恨经年,只有借酒消愁。最后两句在自叹自解中,也含有不可言状之凄苦。
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气象阔大,意绪苍凉。诗中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愁苦意绪笼罩全诗。其中“万树”一联,诗人从大处落墨,描绘出峡川从黄昏到静夜的景象。在这幅画面上,众多的景物如高山、丛林、溪水和明月,本已把画面装饰得既壮美又幽深,再加上“猿哀”一笔,显得更加凄怅苍凉。气象宏阔,以景逆情,进一步渲染作者谪居他乡的愁苦心情。
诗的前六句表现的是登山临水,感慨万千,各种情怀纠结于心,愁绪层层盘结,句句借景抒情,表达了内心被贬的良多沉痛:登山临水之怅恨,九回盘桓之愁肠。苍烟萦绕之万树,幽暗陡峭之峡谷,满川挥洒之明月,凄苦哀婉之猿啼。由于满怀的愁情,山水明月、烟草树木都为之黯然失色。各种愁怨喷薄而出,又何况临近年关,而自己在他乡羁旅,只能强颜作欢,借酒浇愁,以为暂时的宽慰。在悲极之中,诗人笔锋一转,不再作那儿女情长的伤心之语,而是将悲情化为临风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似乎为今日能饱览楚地奇异谲诡的风光而自豪。情绪顿然一转,于解嘲中放达,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旷达豪迈之气。后来,苏轼受欧阳修的影响,也结合自己的多舛经历,在诗歌中将这张苦极自嘲、愈见旷达的宋调发展到了极致。
全词通过一个歌者年老色衰遭遗弃的悲惨命运,道出封建社会千千万万被玩弄、遭遗弃的歌女艺妓的共同心声。
上片通过描写红歌女年轻时的盛况,反衬出年老的失意。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是歌女的语气自信而又自负。“家住西秦”是写实,因为下面有“数年来往咸京道”的句子,歌女当是住陕西附近。“赌”是比赛竞争之意。这两句是歌女述说自己的出身,自言具有多种浪漫的艺术技能,敢和人比赛竞争。
“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仍然是歌女十分自负的口气。“花柳上,斗尖新”之“花柳”代指一切歌舞艺术才能技巧。“斗”,仍是竞赛之意。“尖”,是高处,是过人之处。“新”,不是陈陈相因的旧套。合起来,这是歌女说自己多种艺术才能上敢和大家竞赛,并且比别人高超,新颖独创,绝不流俗。
“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是具体形象地夸述自己的才能如何。“偶”,有随便之意。“念奴”是唐天宝年间有名的歌女。词中歌女似乎自豪地诉说:我偶尔随便一唱当年念奴曾经唱过的歌,能让天上的行云停住,听我歌唱,足见我唱得有多么美,多么动听。“高遏行云”,语出《列子·汤问》,说古有歌者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这几句,当是失意时回忆当年得意情事所言,所以,每一句自负的话后面,都有一种反衬中的失意悲慨。自负的口气,实是自负的不平。
“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写当年得意之时,歌声一发,令众人倾倒,博得赏赐无数,不辜负自己多年的辛劳。“蜀锦”,是四川的丝织品,当时很名贵,古时歌女多以锦缠头,因借“缠头”之名指称赠与她们的财帛。
下片描写歌女年老色衰后所遭逢的冷遇,抒发词人对她的无限同情。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消魂”,是失意后凄凉冷落境遇的写照。从词里的“西秦”、“咸京道”地点上看,当是晏殊被贬知永兴时,慨叹自己的不平境遇而作的。可见作者这首词确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寓意。这首词的整个口吻都寄托着感慨。“残杯冷炙”语本杜甫《赠韦左丞》诗:“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处写歌女境遇如此可悲,令人“消魂”。
“衷肠事,托何人?”歌者因为封建社会女子没有独立的地位,盼望能找一个可以终生相托的人,盼望找到一个足以托身的所,可以安身立命,终生为之奉献而不改变。“衷肠事”,是指内心的事,这里是指终生相托的大事。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徧唱阳春”,仍是以歌女的口气自述:假如有一个知我心的人“见采”(“采”,选择、接纳),那么我将唱尽高雅美好的《阳春白雪》的曲子,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奉献给他。这虽然是一个歌女的口吻,但又体现了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报国之情。这里的“若有知音见采”之“若有”是实无,也就是悲叹找不到知音。
“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了。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歌女酒筵前唱歌,想起当年得意之时的满堂彩声,眼下却这样凄清冷落,不禁当即流下了眼泪。而当时这个筵席前,作者由歌女之悲哀,引起了自身遭贬受逐,客居外乡的悲伤。晏殊所托喻的是歌女,而歌女内心即使有悲哀,眼中有泪水,也要“重掩罗巾”,不能让人看到。“重掩”,是屡次流泪,屡次擦干。每次感到悲哀,都要强作笑颜,其悲哀就更为深重了。
这首词在《珠玉词》中是别具一格的。从思想内容看,它一反以往流连酒歌的生活、相思离别的闲愁、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反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女的不幸命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作品的风格来说,也一反以往的雍容华贵、闲雅圆融,而变得激越悲凉。这一转变或许与作者罢相知外郡的境遇有关,虽则词中没有象自居易的《琵琶行》明写“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但读者仍可以看出作者借歌女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