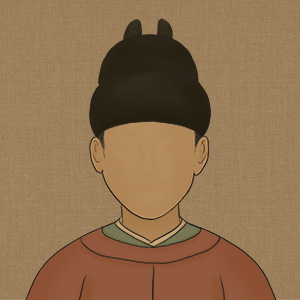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谢逸的这首五言律诗,虽承袭了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引经据典之习,却未形象枯竭,显得空乏。而是着笔于田园农桑,写得清新幽折,恬淡自然,于平淡琐事之中见生活之真淳,见性灵之逍遥。诗歌以“社日”为题,既交代了写作的背景与时间又为全诗奠定了轻松愉悦的感情基调。
首联以写景开篇,诗人用清新自然的笔墨轻描淡写,点染出一痕春色。诗人巧用叠词,“垂垂”状柳叶之态,亦指雨滴下落;“细细”写水波之纹,用语清新,形容细致。两处叠词连用,使得诗句节奏分外明快。雨染柳叶,风戏波痕,一静一动,情景交融,道出春之舒展,道出万物之生气,道出览物之悠然。
颔联写春社上的活动,煮茶品饮,烹芹为羹。虽无玉盘珍馐,管弦丝竹,但茗香沁人心脾,芹羹天然鲜美。此处用字极炼,其中“羹”为名词动用。
颈联用典。显得诗人悠然通脱,亦生活情趣盎然。谢逸在《睡起》诗云:“假贷烦邻里,经营愧老妻。”虽然能对于拮据能够坦然处之,但是面对妻子就没那么自然了。诗人由热闹的春社酒酣而归,摇摇晃晃,两手空空。此情此景,诗人如何向妻子解释皆不得而知,但应有其趣。
尾联写田园之景,亦显悠然自得,乐在其中。诗人以农事收笔,既给读者留下关于田园风光的无限遐思,又表明躬耕田园,读书悦己,淡泊处世的志向,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此诗写景细致,形象鲜明。诗人生活清贫,一茗一羹,度过春社,既不遭田父之泥饮,更无归遗细君之事;而东作方兴,正待耕耘。写来一片生机,趣味盎然,读其诗而知其人,盖不俗之士也。而杜甫、东方朔两典,亦用得贴切,皆节日故事也。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暮春时节,庭户寂寞,粉蝶穿槛,疏雨黄昏。东风送暖,落红成阵。此情此景,令人魂销。闺中人独自含愁,已无心肠料理玉炉香烟。这首词通过春景的描写,含蓄地透露了人物内心的离别相思之情。诗人以风华之笔,运幽丽之思。全词写得清新柔美,婉转多姿。
当春光消逝落红无数的时候,人们不免产生一种怅惘的心绪。莺歌燕舞、姹紫嫣红的春光给人带来生活的欢乐和美的享受,也悄悄带走人的青春年华。这首词在暮春时节风雨花飞的背景下,抒写闺中春愁,它所蕴含的春思清韵,别有一番耐人寻味的意蕴。上阕写晚天疏雨、粉蝶双飞。一般地说,春天的蜂儿蝶儿,多在日间和风日丽的花树丛中穿飞。而作者笔下的双双粉蝶,偏于晚天疏雨中穿槛而飞,其点缀寂寞庭户,反衬闺中人孤独境况的用心,不言而谕,粉蝶双飞本是无意,但在有情人的心中,顿起波澜,牵动春思:她对青春幸福的向往,对爱人的期待,通过这对比鲜明的画面暗示给读者。下阕写闺中人在期待中的失望。晚天疏雨中,天气微寒,她独倚帷帐双眸含愁,任“玉炉烟断香微”。只是当帘外闲庭中东风摇荡花树,满树花飞如雨的景象才将她从痴迷中唤醒,春光匆匆归去,不禁使她销魂荡魄。
毛熙震是花间派词人,但这首词的写景状物多用白描,清丽疏淡,情味蕴藉,与“花间”秾丽香艳、镂金错彩的风格迥异。作者写的闺中人,不描摹其体态衣妆,不明言其多愁善感,除了“含愁”一句正面点明其期待与失望,再以“玉炉”一句烘托其期待已久,相思之苦,其余各句,均于景物描写中带出她的形影与神态,这正是词论家所称道的融情入景的功力。词中所摄取的双飞的粉蝶、晚天疏雨、东风花树等景物,是最富于表现暮春清韵和闺中人春愁的典型景物,将它们和谐地组合起来,使全词有了直观的画面,具有诱人的美感,情景交融,了无痕迹。前人论词的章法,讲究“短章蕴藉”,言尽意不尽。此词就是一首情景相生、含蓄蕴藉的佳作。它那情在言外的意蕴,比起痛快淋漓的表白,更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尤其篇末“东风满院花飞”一句,形象凄艳,含蕴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