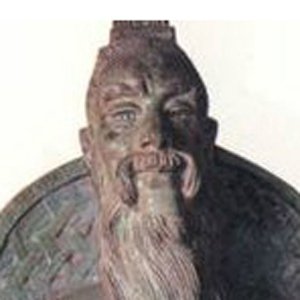此诗是作者《正乐府十篇》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大致可分为三段。
从“秋深橡子熟”至“用作三冬粮”八句为第一段,写老媪拾橡子的艰辛及用途。前四句寥寥数笔,便点出时令、地点、人物、事件和具体活动时间,勾画了一幅孤凄悲楚的荒山拾橡图。“伛偻黄发”,状出老媪筋骨累断、膏脂枯干的形象;“践晨霜”则说明老媪动身之早,天气之寒。从人物形象和动作方面,读者可以看出统治者给人民所留下的种种创伤。五到八句写橡实的拾取、制作之难和它对老媪的“宝贵”作用。一个时辰方拾一捧,一天才可勉强盈筐,拾取橡实实在很难。榛芜冈上橡树丛生,橡子本来很多,老媪起早贪晚却收效甚微,这一方面说明老媪之年高体衰,另方面则暗示出抢拾橡子的决不只老媪一人,从而能以小显大地表现出饥馑遍天下的悲惨现实。
从“山前有熟稻”至“橡实诳饥肠”等十四句为第二段,是老媪的自述,主要写老媪被逼拾橡子的具体原因。“山前有熟稻”等四句,说明老媪以橡实“用作三冬粮”并非懒惰无收,相反,她家的田间所呈现的是稻涌金浪、香气袭人、米粒如玉的一派丰收景象。“持之纳于官”等六句,则写出了导致年丰民不足、老媪拾橡实的主要原因。向官府缴纳赋税犹可,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官府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他们竟用加倍大斗收进赋税。“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是对封建社会吏治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写出了贪官污吏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的心理状态和恶迹。“农时作私债”等四句,是对上述原因的概括回答。“农时作私债”,写出了地主富户对农民的巧取;“农毕归官仓”,则写出了官府对农民的剥夺。正由于地主和官府沆瀣一气,巧取豪夺,所以才使得老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以致饿急了只好拿橡实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总之,这一段老媪拾橡子的具体原因的剖露,入木三分,把唐末统治者的凶残、狡诈和所行无忌的豺狼面目给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了。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着重写诗人耳闻目睹这黑暗现实后内心的慨恨,并对老媪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特色。首先,诗歌在思想上颇具锋芒,作者把批判矛头直指上层统治者。诗人描绘老媪霜晨拾橡图并非目的,而借题发挥,暴露封建统治者残酷榨取民脂民膏以肥己的罪恶,才是诗人的本意。皮日休的超群处,正在于他善于踏着客观描写的跳板,凌空飞剑直下,通过“吾闻田成之,诈仁犹自王”二句的主观抒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王”。在最后一段里,作者运用田成子诈仁成就王业的典故与现实作比,在于说明:田成子主观上虽然假仁假义,刁买人心,但客观上老百姓到底还是从其大斗出、小斗入上得到了一点好处,他也因此而成就王业。而当世唐朝皇帝支持贪官狡吏恣意剥夺,是连表面上的假仁假义都做不到。这样的结尾因用典而趋之含蓄。
其次,赋的手法的运用也很有特色。“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皮日休在这首诗中落笔便直截了当地写橡媪被逼拾橡子的形象和促其行动的原因,不事假借,不用比兴,没有状物绘景,没有刻意求工,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浸泡在浓烈的诗情中,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充满感情地对事情加以层层敷陈。这里,可以说,事件是骨肉,情感是血液,骨肉血液有机配合,才使诗中的形象能站能行,能歌能泣,从而收到情景逼真、深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另外,语言质朴通俗,刚健有力,叙事明晰,情发有据,用典活泼,形象生动逼真。
本诗的前半四句,传神地绘出了一幅潇湘江上的雪景图。“玉花”化用梁昭明太子<黄钟十一明启>“玉雪开六出之花”意,形容绝妙,“卷”字见出了雪花纷纷扬扬的飞舞之态。“长空”切“天”,“汀洲”切“江”;“卷玉花”是细部的、动态的观照,“白浩浩”是总体的、静景的印象:语简而意象丰富。“雁影”句表明已届隆冬的时令,又隐用雁度潇湘的本地风光来暗示“江天”所属的地域。最妙的是第四句,它不仅补明了题面中的“暮”字,而且写出了暮雪雪景所特有的那种朦朦胧胧、半幽半明的色调与风韵。后半部分,诗人在画面中安排一名生活在巴陵地区的渔翁,这名渔翁已登返棹,“寒欲归”三字,隐透出“暮雪”的影响。“不记巴陵道”既含有大雪弥漫迷蔽江路的意味,又见出渔翁对“江天暮雪”处境的顺适。“船自流”的结果,是在视野中留下了一抹渐行渐杳的痕影;这一余韵袅袅的结尾,增添了画面的动感与纵深感,传现出“江天暮雪”全景清逸超妙的风韵。全诗首尾映照,动静相间,意境高旷。诗中的渔翁因天"寒"已登返小船,却因为大雪弥漫遮住江路,忘记了回返的道路。这位渔翁索性坐睡舟中,任凭小舟随江流漂荡。
由此可以看出渔翁对"江天暮雪"处境的顺适之情。
1、人对人倒常常是这样的。最终还是要凭实力决定一切的。
2、有时候知道的东西多了,成熟了,反而唯唯诺诺,害怕很多事情,没有勇气了,其实是赞赏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的.
3、小儿因“痴”不畏虎,“虎亦寻卒去”。这样的稀奇事引起作者思考。他获得的结论是:“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惧之人,威亦无所施欤!”从这一启示说开去,对所有的艰难困苦,挫折磨练,不也应该如此认识吗?望而生畏,自伤锐气;无所畏惧,成功有望。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