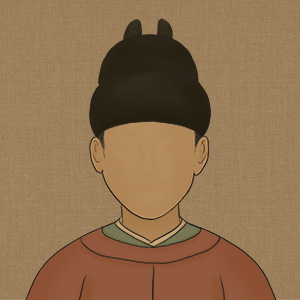这是一首悼亡诗。诗的首联写诗人心绪不佳,无心参与宴饮。颔联承上,说室内空寂,绝无人迹。颈联写王氏去世后,留下幼小的儿女,深为哀悯怜念。尾联通过描绘凄冷黑暗的环境,凸现出自己内心的痛苦。这首诗语言平易,却蕴含丰富情感。
“谢傅门庭旧末行,今朝歌管属檀郎。”两句是说,过去我在王家门庭之中,曾忝居诸子婿行列之末,参与过家庭的宴会,而今天的歌吹宴饮之乐,却只能属于韩瞻了。李商隐娶的是王茂元的幼女,故谦称“末行”。不过他最得茂元的喜爱。如果说,“旧末行”的身份所引起的是对往昔翁婿夫妇间家庭温馨气氛怅然若失的怀想,那么,“今朝歌管”所带给诗人的就只有无边的孤孑与凄凉了。“歌管属檀郎”,“属”字惨然。诗人感到,自己与家庭宴饮之乐已经永远断绝了。
颔联“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顶上“歌管属檀郎”,掉笔正面抒写悼亡。对句化用潘岳《悼亡诗》“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句意。两句以重帘垂地、长簟竟床和清尘厚积来渲染室空人亡、睹物思人。这原是悼亡诗中常用的手法和常有的意境,但此处却不给人以蹈袭陈旧之感,写得别具新意,极富神韵。诗人在恍惚中,感到妻子还在室内,不觉寻寻觅觅,下意识地到处搜寻那熟悉的身影,却发现已是人迹消逝的空房,不禁发出“更无人处”的悲伤叹息。正在这时,眼光无意中落到悄然垂地的重帘上,若有所失。看到床上积满了灰尘,过去拂拭,但定睛一看,但却是一张除了铺满的长席之外别无所有的空床。这后一个举动,不但突出了诗人目击长簟竟床时的惊悸之感,而且表现了诗人面对空床委尘而不忍拂拭的心理,似乎那会拂去对亡妻的亲切回忆。句首的“欲”字,正传出这种欲拂而未能的意态。
颈联“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写幼女稚子深堪悯念。这里分别以“嵇氏幼男”、“左家娇女”借指自己的幼子衮师和女儿。失去母亲怜爱的孩子是可怜的,自己孑然一身,在寂寞凄凉中稍感慰藉的,也只有幼男娇女,身在幽冥的妻子,想必更加系念留在人间的幼男娇女,经受着幽显隔绝无缘重见的痛苦,两句又好象是对幽冥中的妻子所作的郑重表白和深情安慰。怜念子女、自伤孤孑、悼念亡妻,这几方面的感情内容都不露痕迹地表达出来了。
尾联“愁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在秋雨西风、漫漫长夜的背景下进一步抒写因悼念亡妻而触发的深长而复杂的内心痛苦。李商隐一生的悲剧遭遇和他的婚姻密切相关。由于他娶了王茂元的女儿,遭到朋党势力的忌恨,从此在仕途上坎坷曲折。这种遭遇使得诗人的婚姻笼罩着一层悲剧的阴影,造成他心灵上深刻的创伤和无法解脱的痛苦。如今王氏虽已去世,这种悲剧阴影仍在继续。绵绵秋雨,万里西风,茫茫长夜,包围着他的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凄冷和黑暗,内心的痛苦也和这绵延不绝的秋雨一样无法排遣,和这茫茫长夜一样未有穷期。“西风”而说“万里”,“夜”而说“正长”,都写出了在黑暗的夜晚,外界环境作用于诗人的听觉、感觉所引起的感受。
这首诗对亡妻的悼念深情与其对身世的自伤融为一体,和盘托出。
这是一首描写月夜于江上听筝的小令。此曲首句从清夜入手,描摹月夜江景,为下文写情蓄势;次句写筝声打破江夜的寂静;三句转写闻筝人的神态;末句写出听筝的反应。全曲构出一幅历历分明的江夜风情画,将写景记事抒情结合在一起,情景交融,文句虽短,艺术价值却很高。
此曲第一句先写月夜江景,水月映照,空灵明净,显示出澄澈宁谧的气氛。第二句写筝的声音。在月色中,不知是谁弹起玉筝,打破四周的寂寥,添增了神秘幽婉的韵味。第三句则从听筝人的神态,以背面敷粉的艺术手法,烘托筝声所表达的哀伤感情。第四句写江涛澒洞,它像是被筝声勾起的深沉的叹息。这样的写法,又把感伤之情推进一步。
这首二十四字的小令,与白居易那首六百余言的著名长诗《琵琶行》有相似之处。同是江天月夜,同是不期而闻哀怨的音乐弹奏,这支《凭阑人》几乎可说是浓缩的《琵琶行》。只是白诗详尽地介绍了演奏的过程,弹者的身份、经历,以及听者哀怨的缘故,而小令限于容量,这一切都付阙如。但因此也造成了作品的悬念,令人遐想。筝声无端而至,哀怨无端而生,倏然以来,戛然以止,造成了全曲清凄超妙的风神。
在技巧形式上,此篇属散曲巧体之一的“嵌字体”,各句都嵌有一至二处“江”字。“嵌字体”在诗歌中已有先例,如陶渊明的《止酒》诗,二十句中就句句含一“止”字。散曲“嵌字体”的最早作品,则是元好问的《喜春来·春宴》:“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春风春酝透人怀。春宴排,齐唱喜春来。”此篇同嵌的“江”字,建立了句与句之间的内部联系。全曲出现的“江水”、“江月”、“江上”、“隔江”、“满江”的重复不仅多方位地充实了“江夜”的题意,而且表现了一唱三叹的风韵。
此首为思妇之词。开头两句,通摄全词,点明由春色引起春恨。上片主要写春色,下片主要写春恨。上下片仿佛两个相连的画面,全词情景交融。
开始两句十二字,内蕴丰富。“深闺”暗示抒情主人公是少妇,面对恼人春色,不禁情思绵绵。一个“劳”字透露出她那“为君憔悴尽,百花时”的隐痛。由“劳”瘁而怨“恨”,可见其爱之深切。“恨共春芜长”,佳在“春芜”一词含义双重面使全句意味隽永。以春草喻离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远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又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以上“春草”都是本义,没有引申之意。而“恨共春芜长”的“春芜”,除春草本义外,还隐寓行人之意,也就是说此句不仅有闺中人的怨恨随着春草不断增长之意,还含有“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人越远、恨越长之意。这就深化了诗意,即前人所谓得“句外意”之妙。下面三句写景,以具体意象补充首句“春色”,选取深闺“琐窗前”的视角写思妇所见所闻。“黄鹂娇啭泥芳妍,杏枝如画倚轻烟”两句宛如五代花鸟画,用笔工细,着色鲜艳。前一句声色并茂,以声为主,富有动势。黄鹂的婉啭娇鸣,似与满园春色而共语。后一句写杏枝倚立于淡淡烟霭中,恬静如画。这春色以黄鹂、红杏为主,缀以群芳的姹紫嫣红,一片暖色,再加上黄鹂悦耳的娇啼,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不足喻其美。少妇透过琐窗听见以上春光,当比“忽见陌头杨柳色”感触更为深婉了。上片如从思维顺序出发,触景而生情,则开头两句亦可算是逆笔。
从上结至过片,时空转换为另一个画面。张炎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词源·制曲》)“凭阑”句既自成画面,又未断意脉。原来闺中人被春色所吸引,不满足于隔窗观花,她轻移莲步,款款伫立于阑干旁,含愁凝眸。“双娥细”,以秀眉的细长以形容其青春貌美。“‘柳影斜摇砌”,是思妇凭阑所见,也是下片唯一景语,寥寥五字,一波三折,确是词的当行本色语。表层意思是柳条之影因风吹斜而摇曳于台阶,但其中还隐含摇落了杨花、杨花飘落于“砌”两层意思。这三层意思浓缩于五字句中,写得极密。五字中没有“杨花”字样,而于下文显现,是诗人匠心所在。下文思妇的内心独白,由上片的蓄势,直至此句才引发出来。从杨花的摇落,联想自己红颜将凋零,所以她痛苦地唱出了全词的最强音:“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和开头暗相呼应。她终日盼不回丈夫,怅恨之情悠然而生,于是嗔问道:“你倒是回来不回来?叫人家成天价象在梦魂中一看,跟着那漫天的柳絮,绕世界去神游寻觅!”这种奇思遐想,意味深长,倾吐出少妇的无限离愁和情思。“魂梦逐杨花”为思妇词开创了新的意境,对后代有所影响,如晏几道名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似受此词启发,又如章楶的《水龙吟·杨花》以及苏轼的和词,咏杨花而和思妇情怀相联,也似乎受到此词的影响。
《花间》词温庭筠多丽藻,韦庄多质朴语。顾敻成就不及温、韦,此词却能熔丽藻与质朴于一炉,使之疏密相间,恰到好处。
在古代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登高望远”之作,要么站在楼上,要么站在山上。或是因为站在高处,凭栏临风,衣襟摆动,发际飘摇,眼目所到之处,皆是宽阔宏大视野,此情此景此境最容易激发人的豪情气概。这豪情气概充塞胸间,若不抒发出来,定觉难受。会做诗的便将之化成诗句,会唱歌便将之化作歌声,既不会做诗也不会唱歌的,也定要对着远处哦哦啊啊吼叫几声,才觉痛快。
白居易站在庾楼之上,策动他内心的不是汹涌的豪情,而是悠远的乡情。
独凭朱栏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
首二句写明了时间、地点和景色,定下了全诗的意境。
竹雾晓笼衔岭月,苹风暖送过江春。
此二句继续写景,苹风就是单纯的指风,古人认为“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所以称风为苹风。其中后一句写得很妙,指明了季节是初春,那边的苹风一吹,便将温暖的春天送到江这边来了。
子城阴处尤残雪,衙鼓声前未有尘。
想是庾楼坐落在一座城市边(可能是江城,未作考证),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到全城景貌,包括白居易平常上班的衙门。前一句再一次揭明了季节为冬末春初,城市阴处的雪还未化尽;后一句亦再一次揭示时间是清晨,人们一天的工作还未开始,衙门口大鼓前还没有尘土飞起——说明没人在那儿活动。
三百年来庾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
末二句是点睛之笔,前面写景、写景,到结束了来这么一句感叹,戛然而止,却意蕴悠远。这望乡人中,白居易何尝不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