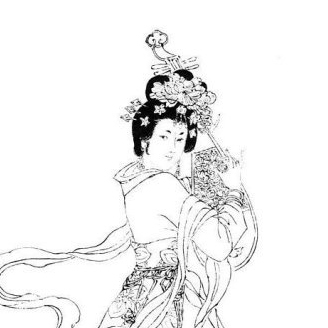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倒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倒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倒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倒,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倒,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这首七言绝句写诗人在旅途中过重阳,登高远望所见所感,抒发浓浓的思归的情怀。
首句点明题旨: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远望。九月九日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有登高的习俗。游子在外,都难免思乡思归,登高远望时,当然会遥望故乡的山川。这一句非常恰切地写出了游子此时此地的望乡动态。次句由动态转写心情,这种“归心归望”的情怀,不是直抒胸臆抒发出来,而是寄寓在“风烟”中,一个“积”字很有分量,道出了归心归望的程度。风烟有多浓多广,那么诗人的“归心归望”也就有多浓多广。这样表现了诗人的归思归望是浓浓的厚厚的。
最后两句写诗人远在他乡的高山上,和大家一起喝着节日的菊花酒,而这里与故乡身隔万里,只能伤心地望着鸿雁飞向南天。重阳登高喝菊花酒是习俗,饮酒是叙事,而游子此时思归,难免多饮几杯,借以消乡愁,这就是事中寓情;饮酒消乡愁,叙事中寄寓了乡愁之情。“鸿雁天”是写景,是鸿雁南飞之景,而诗人是范阳人,雁南飞而反衬人不能北归,这就是景中含情了。
杨慎举出此诗与王勃《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认为两诗雷同。实际上,王诗与此诗正好可以参读。王、卢的《九日》诗,虽然题材相同,构思相似,但是王诗的结句,问得痴情,问得无理而妙,表现诗入对南方生活的厌倦。而卢诗的结句,是以雁南飞反衬人不可北归的乡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艺术特色不同,非抄袭雷同可比。这两首诗,立意清新,情感真切,构思细密,结构完整,是唐人绝句中的名篇。所谓“王、扬、卢、骆当时体”也。具实卢照邻的诗,以“适意为宗”,“不以繁辞为贵”,题材广泛,深情流丽,雄劲自然,富有奇崛的幻想色彩,无论是在“初唐四杰”中还是在整个唐初诗坛,都是十分突出的。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这是交代人物、地点。人物是一个美丽姑娘,她的容貌艳丽,性格娴静。地点是“歧路间”,即岔路口,她在采桑。“歧路间”是来往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就为下文“行徒”、“休者”的倾倒预作铺垫。“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紧接“采桑”,写柔嫩的桑枝轻轻摇动,采下的桑叶翩翩飘落。这里明是写桑树,暗是写美女采桑的优美动作。景物的描写对表现人物起了烘托作用。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休,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主要写美人的服饰,也写到神情。“攘袖”二句,上承“柔条”二句,美女采桑必然挽袖。挽袖方能见到洁白的手。为了采桑,素手必须高举,这样又可见到带着金手镯的洁白而光泽的手腕。用词精当,次第井然。因为是采桑,所以先写美女的手和腕,然后写到头和腰,头上插着雀形的金钗,腰上挂着翠绿色的玉石。身上佩着明珠,还点缀着碧色宝珠和红色的珊瑚。以上几句写美女身上的装饰品,多为静态的描写。“罗衣”二句,写美女轻薄的丝罗上衣,衣襟随风飘动,是动态的描写。动静结合描写美女的服饰,写出美女婀娜的身姿和轻盈的步态。形象十分鲜明。“顾盼”二句,以精妙的字句,勾勒美女神情。美女的一顾一盼都给人留下迷人的光彩,长啸时呼出的气息,芬芳如幽兰。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不为之倾倒吗?所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行路的人见到美女停车不走了,休息的人见到美女忘了吃饭,从侧面描写美女的美貌。应该指出,曹植的这段描写,显然受了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陌上桑》描写罗敷的美貌是这样写的:“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怨,但坐观罗敷。”这是描写罗敷的美丽,并不直接描写她的容貌,而是描写她用的器物(“笼系”“笼钩”)和穿戴的服饰(“倭堕髻”“明月珠”“下裙”“上襦”)之美及“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四种人见到罗敷以后的反应,从正面和侧面来烘托罗敷的美丽。这些描写与《美女篇》的描写对比起来,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写法却不尽相同,表现了曹植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交代美女的住处,点明她的高贵门第。美女住在城南大路附近的高楼里。“青楼”“高门”“重关”,说明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而是大家闺秀。“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美女的容光如同早晨的阳光,谁不爱慕她的美貌呢?上句写美女容貌之美,可与前半首合观;下句说无人不为之倾倒,引起下文。这里写美女高贵的门第和美丽的容颜,是隐喻诗人自己的身份和才能。有才能而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为他不能不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媒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不及时送来聘礼,订下婚约呢?诗人对媒人的责怪,反映了自己内心的不平。媒人不来行聘,这是客观上的原因。而美女爱慕的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寻求一个贤德的丈夫实在很困难。这是美女主观上的原因。这是比喻志士有理想,但难于实现。美女的理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可而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他们哪里知道她看得上的是怎样的人。这是比喻一般人不了解志士的理想。“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美女正当青春盛年,而独居闺中,忧愁怨恨,深夜不眠,发出长长的叹息。这是比喻志士怀才不遇的苦闷。
这首诗通篇用比,比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诗经》、《楚辞》多用之。《美女篇》以绝代美人比喻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其实美女所喻之志士就是曹植自己。
这首诗的含意非常通俗易懂,可以用“珍惜时光”这个词来概括。这原是一种每个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它使 读者感到愿望单纯而强烈,使 人感到无比的震撼,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全诗每一句似乎都在反复强调“莫负好时光”,而每句又都有些微妙变化,重复而不啰唆,回环不快不慢,形成优美的轻盈旋律。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句式相同,都以“劝君”开始,“惜”字也出现了两次,这是二句重复的因素。但第一句说的是“劝君莫惜”,第二句说的是“劝君须惜”,“莫”与“须”的意思是相反的,这就是重复中的一些变化,但是主要意思是不变的。“金缕衣”是非常贵重的衣物,却“劝君莫惜”,说明世间还 有比它更为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劝君须惜”的“少年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诗句未直说,那本是不言自明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然而青春是非常宝贵的,一旦逝去是再也回不来的。一再“劝君”,用规劝的语气,情真意切,有很浓厚的歌味和娓娓道来的神韵。两句一个否定,一个肯定,否定前者是为了肯定后者,似分实合,虚实相生,形成了诗中第一次反复和咏叹,旋律和节奏轻盈舒缓。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则构成第二次反复和咏叹,单就诗意看,与一、二句差不多,还是“莫负好时光”那个意思。这样,除了句与句之间的反复,又有上联与下联之间的较大的回旋反复。但两联表现手法就不一样,上联直抒胸臆,是赋法;下联却用了譬喻方式,是比义。于是重复中仍有变化。三、四没有一、二那样整饬的句式,但意义上彼此是对称得铢两悉称的。上句说“有花”应怎样,下句说“无花”会怎样;上句说“须”怎样,下句说“莫”怎样,也有肯定否定的对立。二句意义又紧紧关联:“有花堪折直须折”是从正面说“行乐须及春”意,“莫待无花空折枝”是从反面说“行乐须及春”意,似分实合,反复倾诉同一情愫,是“劝君”的继续,但语调节奏由徐缓变得峻急、热烈。“堪折——直须折”这句中节奏短促,力度极强,“直须”比前面的“须”更加强调。这是对青春与欢爱的放胆歌唱。这里的热情奔放,不但真率、大胆,而且形象、优美。“花”字两见,“折”字竟三见;“须——莫”云云与上联“莫——须”云云,又自然构成回文式的复叠美。这一系列天然工妙的字与字的反复、句与句的反复、联与联的反复,使诗句琅琅上口,语语可歌。除了形式美,其情绪由徐缓的回环到热烈的动荡,又构成此诗内在的韵律,诵读起来就更使人感到回肠荡气了。
此诗另一显著特色在于修辞上的别致新颖。一般情况下,旧诗中比兴手法往往合一,用在诗的发端; 而绝句往往先景语后情语。此诗一反惯例,它赋中有兴,先赋后比,先情语后景语,殊属别致。“劝君莫惜金缕衣”一句是赋 ,而以物起情,又有兴的作用。诗的下联是比喻,也是对上句“须惜少年时”诗意的继续生发。不用“人生几何 ”式直截的感慨,用花来比少年好时光,用折花来比莫负大好青春,既形象又优美,创造出一个意象世界。
这就是艺术的表现,形象思维。错过青春便会导致无穷悔恨,这种意思,此诗本来可以用但却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成语来表达,而紧紧朝着折花的比喻向前走,继而造出“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没有沾一个悔字恨字,而“空折枝”三字却耐人寻味,富有艺术感染力。
该小令上片写水月迷濛之夜,“满城烟水月微茫,人倚兰舟唱”。在作者笔下,夜色别有一种韵味,别有一种神秘。水气与“微茫”的月色联成一气,具有一种朦胧之美。朦胧之中,采莲的少女斜倚兰舟,唱着心中的歌,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倚舟低唱之人对远方恋人的深沉怀念,情景交融,和谐一致。特别是以荷花比情人,以藕丝喻情思,不仅形象切贴,更把那种热烈缠绵的感情表达无遗。
下片写采莲人的歌声惊破了梦中聚首的鸳鸯美梦,只好深夜独卧江楼,不禁思绪滚滚,热泪潸潸,伤心莫唱南朝旧曲。这委婉地写出了男婚女恋、独梦相思之情,而且把相思的一往情深的情人之恋、故土之思、亡国之痛、兴亡之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作品的思想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该曲虽然在极小的篇幅内容却纳入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在于作品含蓄委婉的表现方法,使得全曲有了异乎寻常的内涵和表现力,体现了作者不凡的艺术手法,有着咀嚼不尽的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