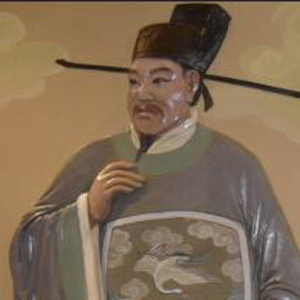此词开篇写道,铜炉里的香烟,缭绕上升,盘旋似篆文,这时候已经消散;庭院里树木的阴影转过了正午所在位置,也就是刘禹锡《池亭》诗所写的“日午树阴正”,而稍稍往东偏斜了。这几句描绘的是深锁闺房“醉沉沉”的人之所见、所感。开头三句已充分刻画了“画堂人静”。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宁静,人不会对炉中升起的香烟那么注视,看出它升起后的形态变化以至于散灭;对庭中树木阴影的“转午”,也不会感觉得出来。身在如此的环境中,她想着什么,才透出一些消息:“芳草王孙知何处?”这里是用“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句意,表明“她”是在怀念远人。“惟有杨花糁径”点明此时是杨花飘飞的暮春天气。她的情,如山涧小溪,水流缓慢,与那静悄悄的环境,很是和谐。不过从“杨花糁径”看,这春光已是“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了。“惟有”二字又表明路上只有杨花,并无他所盼望的归人。她的愁绪从中轻轻地流漾出来了。
“渐玉枕、腾腾春醒”。从方才的“醉沉沉”而仍有所感觉来看,她依依而睡并不久。“腾腾春醒”这句话说的是醒后懒散的情态,与“醉沉沉”上下照应。彼时即有“芳草王孙知何处”之感,现在梦破春醒,这种感觉岂不更深?感情的潮水将在她的心里掀起更大波澜,也许还是“醉沉沉”的好。“帘外残红春已透”,加上前面的“杨花糁径”,为什么接连不断地重复春天的归去呢?春老花残,闺中人敏锐地感觉自己的青春将逝,红颜将老。从这些看似写景的反复描述中,可以看出正渗透着人的感情。“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夫之《姜斋诗话》)。这几句的“景中情”完全达到了“妙合无垠”的地步。
“镇无聊、殢酒厌厌病”。前面的景物描绘无不寓有一个“情”字,到此句便写出女主人公残春时节的心情。这句词中的“镇”作“长”的解。这句话说的是长日情思无聊,故缠绵于酒,借以消愁。刘过《贺新郎》词曰:“人道愁来须殢酒”,就是这种状态了。结果是愁未能消,反而因酒致病,精神不振。“云鬓乱,未忺整”,说的是没有好心情去梳理零乱的鬓发。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更有“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之意。因“无聊”而“殢酒”,因酒而“厌厌病”,因病而懒妆流,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春去而人不归引起。词写到这里,已由外部描写隐约透露出人物的内心。
下阕,则完全转入女主人公自我抒情了。“江南旧事休重省”,这句劈空而来,一下启开了女主公人的心扉。那“江南旧事”,也许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温馨岁月吧,此时却是“休重省”了。是真的不愿“重省”么,还是“省”也无用,故作决绝语呢?正是这一个“休”字蕴含着说不尽的情意。接着她直率地道出了底蕴:“遍天涯、寻消问息,断鸿难倩”,说的是到处探听而信音杳然。“月满西楼凭阑久”,说的是她悄悄登上西楼,独自望着银白的月光洒满大地,痴痴地想着。“依旧归期未定”,是说他现在大概正想着回来,只是日子还没有确定,所以鸿雁没有传来书信吧。
这只是她的想象,情况是否如此,并不十分清楚。这样她又陷入了揣想中:“又只恐瓶沉金井”。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有云:“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此词根据白诗以“绳断瓶沉”作比,慨叹爱情破裂已无法弥合。“又”字意味深长,它恰与上句联系着。她本来是希望他能回来,只是“归期未定”;转而再想,愈感到没有把握,故有此“又”字。读之令人感到万转千回,心潮翻腾,柔肠寸断。
“嘶骑不来银烛暗,枉教人立尽梧桐影”。从“篆缕销金鼎”到“庭阴转午”,到“月满西楼”,到“银烛暗”,时间的脚步在静寂中前进着。她沉醉,入梦,醒来,倚阑望月,最后寄希望于万一,盼着听到马嘶声,所思念的人也许会骑着马归来吧。但直到“银烛暗”了,月落了,“梧桐影”尽了,她一直在痴痴地望着,听着,仍不见人归。这里直引吕岩《梧桐影》词“教人立尽梧桐影”,而添一“枉”字领起,语更痛切。“谁伴我,对鸾镜”,这是发自肺腑的痛切心声。“鸾镜”,是用来梳妆的。昔日鸾镜前,人影双双,也许还有过张敞画眉那样的风流韵事,然而此时独对鸾镜,着实令人柔肠寸断。这位女主人公自始至终,没有一言一语埋怨对方,直到最后,也只是婉转倾诉,连一点愠怒的情绪都没有。和婉淳雅,在思归的形象中,独树一帜。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一开头就奇峰突起,呈现异彩。裛裛,香气盛貌。虽然梅树亭亭直立,花容清丽,无奈傍路而开,长得不是地方。虽然梅花囊哀清芬,香气沁人,可是梅花过早地在十一月中旬开放,便显得很不适时宜。这正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作者的感情通过咏梅来表达。作者的品格才华,恰好正像梅花的“亭亭艳”、“裛裛香”。作者牵涉到牛李党争中去,从而受到排挤,以及长期在过漂泊的游幕生活,也正是处非其地。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二句清怨凄楚,别开意境。同是月下赏梅,作者没有发出“月明林下美人来”的赞叹,把梅花比作风姿姣好的美人;也没有抒写“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一类的颂词,赞美梅花傲霜的品格;而是手眼独出,先是埋怨“素娥”的“惟与月”,继而又指责“青女”的“不饶霜”。原来在作者眼里,嫦娥让月亮放出清光,并不是真的要给梅花增添姿色,就是没有梅花,她也会让月色皎洁的。嫦娥只是赞助月亮,并不袒佑梅花的。青女不是要使梅花显出傲霜品格才下霜的,而是想用霜冻来摧折梅花,所以她决不会因为梅花开放而宽恕一点,少下些霜。一种难言的怨恨,淡淡吐出,正与作者身世感受相映照。
写到这里,作者的感情已达到饱和。突然笔锋一转,对着梅花,怀念起朋友来了:“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想折一把梅花来赠给远方的朋友,可是仕途坎坷,故友日疏,即使折得满把的梅花也没有什么用。连寄一枝梅花都办不到,更觉得和朋友离别的可悲,所以就哀伤欲绝,愁肠寸断了。“伤离”句一语双关,既含和朋友离别而断肠,又含跟梅花离别而断肠,这就更加蕴蓄隽永。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在这里表达了他对梅花的悲痛,这种悲痛正是对自身遭遇的悲痛。联系到诗人很早就以文才著名,所以受到王茂元的赏识,请他到幕府里去,把女儿嫁给他。王茂元属于李德裕党,这就触怒了牛僧孺党。在牛党得势时,他就受到排斥,不能够进入朝廷,贡献他的才学,这正像梅花未能等到春的到来而过早开放一样。这一结,就把自伤身世的感情同开头呼应,加强了全篇的感情力量。咏物诗的最高境界是“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意思是依照事物的形貌来描绘,委婉地再现其形象;同时,也曲折地传达出内心的感情。这首诗正是这样。梅花是一定时空中盛开的梅花,移用别处不得。与之同时,又将诗人的身世从侧面描绘出来。两者融合得纹丝合缝,看不出一点拼凑的痕迹,是作者深厚功力的表现。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刘朔斋名震孙,字长卿,蜀人。曾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斗南楼原址在广州府治后城上,始建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其特色是在此地观海山之景,别具情致。
起笔二句:
极有气势,站在斗南楼上,万顷海涛,千仞云山,尽收眼底,使人视界大开,胸襟舒畅。
“黄湾”,即韩愈《南海神庙碑》所谓“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黄木湾,位于今天广州东郊黄埔,是珠江口一个呈漏斗状的深水港湾。唐宋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中外商船往来贸易均在此处停泊。
“白云”,指广州城北的白云山。“万顷”、“千仞”虽是诗词中常见之语,但用于篇首,气势尤显雄壮。
“一亭收拾”,即一楼览尽之意。据《广东通志》载:于此可以“东瞰扶胥浴日之景,西望灵洲吞纳之雄,南瞻珠海,北倚越台。森列万象,四望豁然”。
“一亭”句与首二句相衔接呼应。由于一亭览尽胜景,词人心神俱爽,暑热顿消,达到清凉境界。该句中的一个“豁”字,将词人暑热顿消的情志、精与气都表现出来。
“潮候”句,分承“万顷”、“千仞”句发挥。潮水的早晚涨落,山色的雨晴变化,这正是岭海特有的景色。“天送双眸”句,一个“送”字,便把天际的景色,轻轻移来眼底。此处上接前两句,写出景致的变化,丰富了景色的内涵。
词人眺望天边:在万顷烟波之外的遥远地方,在那波浪中起伏的无数船只,是往来穿梭的商船。“绝域”二句,写出了中外通商贸易的繁忙景象,为宋词中绝无仅有。
上阕:
主要是写眼前雄奇壮阔的景色,下阕则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风景别”三句,写出词人对故乡的自豪感。他认为,这里可以览海观山,远胜于南昌的滕王阁和徐州的黄楼。滕王阁与黄楼是古时的两座名楼,分别因诗人王勃与苏辙、秦观写序作赋而名声鹤起②。作者在题斗南楼时,比之以“滕阁”、“黄楼”,有不让前贤之意。
“胡床”句由斗南楼联想到南楼,晋朝庾亮曾于秋夜登武昌南楼,坐胡床与诸人谈咏,高兴地说:“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胡床”是当时一种可折叠的躺椅。“胡床老子”,指庾亮,这时用典借指刘朔斋。“珠玉”,比喻优美的诗文,这里指刘朔斋的原作。
“胡床”句称誉刘朔斋醉中挥笔,在南国留下美好的词章,对题目作了呼应。
词人写到这里,感情奔放,大有飘飘欲仙之意。他放怀抒发:“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石,飞佩过丹丘,”他要驾起大鹏,唤醒已化为石头的五只仙羊,在仙境中遨游。“八极”指八方之极远处,指广阔的空间。“佩”,指仙人的玉佩,传说系上它便可在天上飞行。“丹丘”,指仙境。《楚辞。远游》之“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即以“丹丘”指仙乡。
“叱起仙羊五石”一句:
来自两个典故。据《术平寰宇记》载: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分别骑着口衔六支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谷穗赠给当地人,祝他们永无饥荒。仙人言罢隐去,五羊化石。广州因此又名羊城。《神仙传》又载:有皇初平者牧羊,随道士入金华山石室中学道。其兄寻来,只见白石,不见有羊。初平对石头喝了一声:“羊起!”周围的石头都变为羊。这两个典故,一为羊化石,一为石化羊,合用在一起,使人觉受到作者随心所欲、指挥万象的豪情!
“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一句:
笔锋一转,由天上回到人世。“机动”句反用“鸥鹭忘机”之典。《列子·黄帝》载:古时海上有好鸥鸟者,每从鸥鸟游,鸥鸟至者以百数。其父说:“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次日至海上,鸥鸟舞而不下。“机”即机心,指欲念。意思是人无欲念,则鸥鸟可近。陆游《登拟岘台》之“更喜机心无复在,沙边鸥鹭亦相亲”,便用此意。此处反用,即设若欲念一生,鸥鸟便惊飞远避了。二句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态度。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