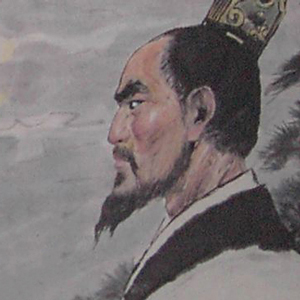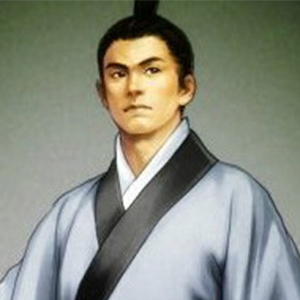这首诗写春天所见之景。
首二句写诗人站在河边远望所见。长长的河堤上绿草连绵,一望无际,绿色迷濛处,堤草与广袤的田野的绿色融汇交接。一场春雨过后,岸边的花儿开得更鲜更艳了。这两句通过拟人、通感的手法,将岸边所见春天的景致写得气韵飞动。“惹烟”用拟人法。“烟”本是郁郁葱葱的春草在阳光照耀下给人的一种迷濛的色感,诗人不用 “含烟”而用 “惹烟”,使无生物变为有生物,传写出了堤草蕴含的勃勃生机。是堤草的葱郁撩惹起诗人的情思,而诗人又反过来把这一份撩人的情思赋予了青草。“压枝红”则写通感。“红”是颜色,原本没有重量,这里用沉甸甸的压枝的重量来表现颜色,真可谓独具匠心,写出了雨后红花的秾艳夺人和欣欣生意。 诗后两句写春光中诗人的境况和感受。
“春醉”这一意象,包容二层语义,一层与上二句诗所写景致相联,“春醉”指醉人的春色。“年来多病辜春醉” 是说以多病之身置于这美好春光之中,实在是有违春意,辜负大好时光。二层与最后一句相联,“醉”实指为醉酒。诗人因为年来多病,不能去酒肆豪饮,而依诗人的豪放本性是多么向往在这大好春光里开怀畅饮啊。正是这种欲饮不能、欲罢不忍的心境,使得诗人生出了无限伤春之感。在这万物萌苏的春天,诗人感到了生命本体的律动,然多病之身既与这醉人春色相乖,又与开怀畅饮之愿有违。正是在景致与身家境况的不和谐里,诗人生发了一种隐隐的失落感。望着河桥上迎风招展的酒旗,唯有惆怅叹息而已。
这首诗写春天所见之景。
首二句写诗人站在河边远望所见。长长的河堤上绿草连绵,一望无际,绿色迷濛处,堤草与广袤的田野的绿色融汇交接。一场春雨过后,岸边的花儿开得更鲜更艳了。这两句通过拟人、通感的手法,将岸边所见春天的景致写得气韵飞动。“惹烟”用拟人法。“烟”本是郁郁葱葱的春草在阳光照耀下给人的一种迷濛的色感,诗人不用 “含烟”而用 “惹烟”,使无生物变为有生物,传写出了堤草蕴含的勃勃生机。是堤草的葱郁撩惹起诗人的情思,而诗人又反过来把这一份撩人的情思赋予了青草。“压枝红”则写通感。“红”是颜色,原本没有重量,这里用沉甸甸的压枝的重量来表现颜色,真可谓独具匠心,写出了雨后红花的秾艳夺人和欣欣生意。 诗后两句写春光中诗人的境况和感受。
“春醉”这一意象,包容二层语义,一层与上二句诗所写景致相联,“春醉”指醉人的春色。“年来多病辜春醉” 是说以多病之身置于这美好春光之中,实在是有违春意,辜负大好时光。二层与最后一句相联,“醉”实指为醉酒。诗人因为年来多病,不能去酒肆豪饮,而依诗人的豪放本性是多么向往在这大好春光里开怀畅饮啊。正是这种欲饮不能、欲罢不忍的心境,使得诗人生出了无限伤春之感。在这万物萌苏的春天,诗人感到了生命本体的律动,然多病之身既与这醉人春色相乖,又与开怀畅饮之愿有违。正是在景致与身家境况的不和谐里,诗人生发了一种隐隐的失落感。望着河桥上迎风招展的酒旗,唯有惆怅叹息而已。
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戴复古的诗中同情劳动人民之作不乏其例。著名的如《庚子荐饥》等。可以看出,尽管戴复古名列江湖诗人之榜,但他并非一味地逍遥江湖。社会时事、人民生活时常撞击他的心灵,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作者“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良苦用心。
本诗在表达“农夫夏耘”而“吾安坐”这样一个主旨时,大胆地运用比喻和想象。虽然《庄子》中就是“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鵩鸟赋》中也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是,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实质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戴诗在运用这些比喻和想象的同时,又强调了农人于酷暑中的辛勤劳作,以致秋日百谷才能有收获。这样,就把暑热与农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诗的主题也在暑热与农人劳作的交汇中得以升华。他用对生活深刻体验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悯农”上升到“敬农”。较之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思想境界更高一筹。
这首《南歌子》所作年代不详,但从抒发国破家亡之恨来看,似为流落江南后所作。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以对句作景语起,但非寻常景象,而有深情熔铸其中。“星河转”谓银河转动,一“转”字说明时间流动,而且是颇长的一个跨度;人能关心至此,则其中夜无眠可知。“帘幕垂”言闺房中密帘遮护。帘幕“垂”而已,此中人情事如何,尚未可知。“星河转”而冠以“天上”,是寻常言语,“帘幕垂”表说是“人间”的,却显不同寻常。“天上、人间”对举,就有“人天远隔”的含意,分量顿时沉重起来,似乎其中有沉哀欲诉,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此词直述夫妻死别之悲怆,字面上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则暗流汹涌。
前两句蓄势“凉生枕簟泪痕滋”一句。至直泻无余。枕簟生凉,不单是说秋夜天气,而是将孤寂凄苦之情移于物象。“泪痕滋”,所谓“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至此不得不悲哀暂歇,人亦劳瘁。“起解罗衣聊生夜何其”,原本是和衣而卧,到此解衣欲睡。但要睡的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开首的“星河转”已有暗示,这里“聊生夜何其”更明言之。“夜何其”,其(jī),语助辞。“夜何其”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半);夜如何其?夜绣(向)晨”,意思是夜深沉已近清晨。“聊生”是自己心下估量,此句状写词人情态。情状已出,心事亦露,词转入下片。
下片直接抒情“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为过片,接应上片结句“罗衣”,描绘衣上的花绣。因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翠贴”、“金销”皆倒装,是贴翠和销金的两种工艺,即以翠羽贴成莲蓬样,以金线嵌绣莲叶纹。这是贵妇人的衣裳,词人一直带着,穿着。而今重见,夜深寂寞之际,不由想起悠悠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是一句极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内容,许多感情。“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句的“旧家时”也就是“旧时”。秋凉天气如旧,金翠罗衣如旧,穿这罗衣的人也是由从前生活过来的旧人,只有人的“情怀”不似旧时了!寻常言语,反复诵读,只觉字字悲咽。
以寻常言语入词,是易安词最突出的特点,字字句句锻炼精巧,日常口语和谐入诗。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