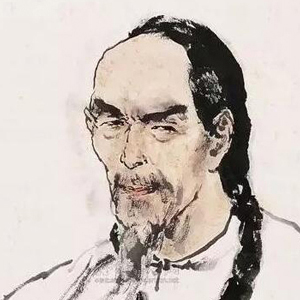这首词开端即写梅花凋谢“宫粉”状其颜色,“仙云”写其姿质,“雕痕”、“堕影”,言其飘零,字字锤炼,用笔空灵凝炼“无人野水荒湾”句为背景补笔。仙姿绰约、幽韵冷香的梅花,无声地飘落在阒寂的野水荒湾。境界空旷悠远,氛围淡寒。“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二句,上承“雕”、“堕”,再进一步渲染,由飘落而埋香,至此已申足题面。“金沙锁骨连环”,用美妇人——锁骨菩萨死葬的传说来补足“埋香”之意。黄庭坚《戏答陈季常寄黄州山中连理松枝》诗云:“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婵娟。”词中用以拟梅花,借指梅花以美艳绝伦之身入世悦人,谢落后复归于清净的本体,受人敬礼,可谓尊爱之至,而哀悼之意亦隐于其中。接下来“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三句陡然转折。“不恨”与“恨”对举,词笔从山野落梅的孤凄形象转入关山阻隔的哀伤情怀,隐含是花实际亦复指人之意。笛曲中有《梅花落》。可见,“南楼”句虽然空际转身而仍绾合本题。所以陈洵称赞为“是觉翁(吴文英晚号觉翁)神力独运处”(《海绡说词》)。下边转换空间,由山野折回庭中。“半飘零”三句,当是从林逋《山园小梅》“暗香浮动月黄昏”化出。梅花既落,而又无人月下倚阑赏之,故言“月冷阑干”,与下片“孤山无限春寒”喻意基本相同。下片言“寿阳”,言“孤山”,皆用梅花故实。《太平御览》卷三十《时序部》引《杂五行书》中的记载:“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鸾”是“鸾镜”,为妇女梳妆用镜。“调玉髓”、“补香瘢”,又用三国吴孙和邓夫人的故事。和宠夫人,曾因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满面,医生说用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敷之,可灭瘢痕,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八。这里合寿阳公主理妆之事同说,以“问谁”表示已经没有了落梅为之助妆添色。孤山在今杭州西湖,宋词人林逋曾于此隐居,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此处化用数典,另翻新意。分从两方面落笔,先写对逝而不返的落梅的眷恋,再写落梅蓬山远隔的幽索。“离魂”三句,仍与落梅紧紧相扣。“缟衣”与“宫粉”拍合,“溪边”亦与“野水荒湾”呼应。“缟衣解佩”暗指昔日一般情事,寄寓了往事如烟、离魂难招的怀人之思。最后一韵,从题面申展一层,写花落之后的梅树形象。“叶底青圆”四字,化用杜牧《叹花》诗“绿叶成阴子满枝”的词句意,包孕着世事变迁的惆怅与岁月无情的蹉跎。
吴文英在苏州时曾纳一妾,后遣去;居于杭州时又纳一妾,后亡故。联系作者的这些经历,并证以其它词章。后人对这首词虽然褒贬不一,但从总体看来,词中那些似乎不相连属的字面的深层,其实流动着脉络贯通的感情潜流,它们从不同的时空和层面,渲染了隐秘的情事和深藏的词旨,堪称咏物之作的佳品。
《午日处州禁竞渡》,主要是面对赛龙舟的情景,而生出对屈原的怀念。
汤显祖此诗写禁止竞渡,别具一格。但是,需要强调,汤显祖对屈原不是不尊敬。汤显祖歌咏屈原的诗句很多,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据载,竞渡起于唐代,至宋代已相当盛行,明清时其风气更加强劲,从竞渡的准备到结束,历时一月,龙舟最长的十一丈,最短的也有七丈五,船上用各色绸绢装饰一新,划船选手从各地渔家挑选。汤显祖认为,这样的场面过于豪华,因此诗中加以表露。从诗中可见:一个清廉的地方父母官,是何等爱护百姓的人力财力。
本首词中记录了女主人的不幸遭遇和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上片写被掳北去时告别故土的沉痛心情,下片写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对敌人的仇恨。整首词的抒情哀婉真挚,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动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词的上阙,写她被掳北去,不得不离别故乡山河时的沉痛心情。
上阕四句,一山一水,两两相对,可以说是一副十分工整的对联,在词作中,它又是不很常见的隔句对。“云峰”、“烟波”,既写山高水阔,又写出春天雨多云多的景象,再加上作者心伤情苦,泪眼朦胧,因此山河呈现出一片迷茫的景象。“云峰”前冠以“千里”,“烟波”前冠以“万顷”,写出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暗示作者对它的深情。但此时却满目疮痍,河山破碎,大批人民被掳北去,不能安居故土,这万千愁恨怎能不一齐迸发!“千里恨”、“万顷愁”极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深仇大恨。
同时,她移情于物,移情于淮河山水,使山河也充满了愁恨,因为它们是这场患难的最好见证。千里,从纵的角度形容愁恨;万顷,从横的方面予以夸张,这样的表现手法就将愁绪这种无形的情感有形化了。具体化了,它与以往的某些表现手法有所差异: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踏莎行》:“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胡楚《寄人》:“若将此恨同芳草,犹恐青青有尽时。”他们着重表现的是愁恨之无穷。应该说这些写愁之作都各自有其艺术的独创性。但这个淮上良家女的这两句词却在读者心理上造成一种泰山压顶、窒息心胸之感。
词的下阕写她被驱赶向西,而她的心却一直向东。
“山长水远,遮断行人东望眼。”两句既是对上片的总结,又是作者眷恋山河的进一步具体描写她离开家乡越来越远,眷恋的感情也越来越重。她一步一回头地看着自己的家乡,直至山水完全遮断了她的视线。天涯沦落,何时能回到故乡的怀抱?这一切使她感到茫然。这一去,也许是永无归日了,只能此刻回首东望,直至“遮断”为止。“东望眼”三字,真实地写出了被掳者逼迫而不得已,朝西北方向行进而不断回望故乡的情景,极形象地表现了她不忍离去的痛苦。
面对着这一切,“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这恨,是指对金人南犯之恨,对南宋统治者屈辱求和、无耻南逃之恨;这愁,是为乡土遭受蹂躏而愁,为被掳后的屈辱生活和颠沛流离而愁。旧恨加新愁,让一个弱女子如何经受得了!“恨旧愁新”四字,一般用作“新愁旧恨”,语意显得平淡。而将“恨”、“愁”二字前置,不但使句尾协韵,加强了音韵美,且构成了两个节奏紧促、意思完整的短句,使人感到语新气逼。末句刻画了一个哀怨至极而又沉默无语的形象。“有泪无言”,是她的一腔悲愤无处、也无人可以倾诉,只有和着泪水忍声吞下这时代加给她的深重灾难,这实际上也是对南宋投降派君臣的一种无声的谴责。“晚春”既点出被掳的时间,也含有春光将逝无可奈何的情思。
这首小词诉说的是一个被金人暴力胁迫的无力抗争的弱女子的遭遇与悲苦,凄恻动人,它能引起人们对女主人公的无限同情。词的形式义富有民歌的特色,写山写水,说愁说恨,回环往复,一唱三叹,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