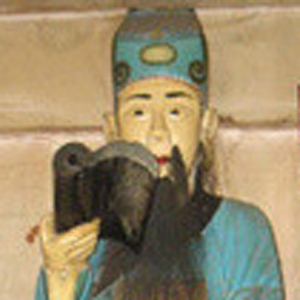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唐军于邺城兵败之后,朝廷为防止叛军重新向西进扰,在洛阳一带到处征丁,连老翁老妇也不能幸免。《垂老别》就是抒写一老翁暮年从军与老妻惜别的苦情。
一开头,诗人就把老翁放在“四郊未宁静”的时代的动乱气氛中,让他吐露出“垂老不得安”的遭遇和心情,语势低落,给人以沉郁压抑之感。他慨叹着说:“子孙都已在战争中牺牲了,剩下我这个老头,又何必一定要苟活下来!”话中饱蕴着老翁深重的悲思。战火逼近,官府要他上前线,于是老翁把拐杖一扔,颤巍巍地跨出了家门。“投杖出门去”,笔锋一振,暗示出主人公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人,他知道在这个多难的时代应该怎样做。但是他毕竟年老力衰了,同行的战士看到这番情景,不能不为之感叹唏嘘。“同行为辛酸”,就势跌落,从侧面烘托出这个已处于风烛残年的老翁的悲苦命运。“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牙齿完好无缺,说明还可以应付前线的艰苦生活,表现出老翁的倔强;骨髓行将榨干,又使他不由得悲愤难已。这里,语气又是一扬一跌,曲折地展示了老翁内心复杂的矛盾和变化。“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作为男子汉,老翁既已披上戎装,那就义无反顾,告别长官慷慨出发了。语气显得昂扬起来。
接下去,就出现了全诗最扣人心弦的描写:临离家门的时候,老翁原想瞒过老妻,来个不辞而别,好省去无限的伤心。谁知走了没有几步,迎面却传来了老妻的悲啼声。他唯一的亲人已哭倒在大路旁,褴褛的单衫正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这突然的发现,使老翁的心不由一下子紧缩起来。接着就展开了老夫妻间强抑悲痛、互相爱怜的催人泪下的心理描写:老翁明知生离就是死别,还得上前去搀扶老妻,为她的孤寒无靠吞声饮泣;老妻这时已哭得泪流满面,她也明知老伴这一去,十成是回不来了,但还在那里哑声叮咛:“到了前方,你总要自己保重,努力加餐呀!”这一小节细腻的心理描写,在结构上是一大跌落,把人物善良凄恻、愁肠寸断、难舍难分的情状,刻画得入木三分。正如吴齐贤《杜诗论文》所说:“此行已成死别,复何顾哉?然一息尚存,不能恝然,故不暇悲己之死,而又伤彼之寒也;乃老妻亦知我不返,而犹以加餐相慰,又不暇念己之寒,而悲我之死也。”究其所以感人,是因为诗人把“伤其寒”、“劝加餐”这类生活中极其寻常的同情劝慰语,分别放在“是死别”、“必不归”的极不寻常的特定背景下来表现。再加上无可奈何的“且复”,迥出人意的“还闻”,层层跌出,曲折状写,便收到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土门”以下六句,用宽解语重又振起。老翁毕竟是坚强的,他很快就意识到必须从眼前凄惨的氛围中挣脱出来。他不能不从大处着想,进一步劝慰老妻,也似乎在安慰自己:“这次守卫河阳,土门的防线还是很坚固的,敌军要越过黄河上杏园这个渡口,也不是那么容易。情况和上次邺城的溃败已有所不同,此去纵然一死,也还早得很哩!人生在世,总不免有个聚散离合,哪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这些故作通达的宽慰话语,虽然带有强自振作的意味,不能完全掩饰老翁内心的矛盾,但也道出了乱世的真情,多少能减轻老妻的悲痛。“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眼看就要分手了,老翁不禁又回想起年轻时候度过的那些太平日子,不免徘徊感叹了一阵。情思在这里稍作顿挫,为下文再掀波澜,预为铺垫。
“万国”以下六句,老翁把话头进一步引向现实,发出悲愤而又慷慨的呼声:“睁开眼看看吧!如今天下到处都是征战,烽火燃遍了山冈;草木丛中散发着积尸的恶臭,百姓的鲜血染红了广阔的山川,哪儿还有什么乐土?我们怎敢只想到自己,还老在那里踌躇徬徨?”这一小节有两层意思。一是逼真而广阔地展开了时代生活的画面,这是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真实写照。他告诉老妻:人间的灾难并不只是降临在他们两人头上,言外之意是要想开一些。一是面对凶横的敌人,他们不能再徘徊了,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扑上前去拼一场。通过这些既形象生动又概括集中的话语,诗人塑造了一个正直的、豁达大度而又富有爱国心的老翁形象,这在中国诗史上还不多见。从诗情发展的脉络来看,这是一大振起,难舍难分的局面终将结束了。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到狠下心真要和老妻诀别离去的时候,老翁突然觉得五脏六腑内有如崩裂似的苦痛。这不是寻常的离别,而是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家乡。长期患难与共、冷暖相关的亲人,转瞬间就要见不到了,此情此景,老翁难以承受。感情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泪水汇聚成人间的深悲巨痛。这一结尾,情思大跌,却蕴蓄着丰厚深长的意境:独行老翁的前途将会怎样,被扔下的孤苦伶仃的老妻将否陷入绝境,仓皇莫测的战局将怎样发展变化,这一切都将留给读者去体会、想象和思索。
这首叙事短诗,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心理刻画见长。诗人用老翁自诉自叹、慰人亦即自慰的独白语气来展开描写,着重表现人物时而沉重忧愤、时而旷达自解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多变的情思基调,又决定了全诗的结构层次,于严谨整饬之中,具有跌宕起伏、缘情宛转之妙。
杜甫高出于一般诗人之处,主要在于他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做到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剖精析微,探骊得珠,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准确传神地表现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概括劳苦人民包括诗人自己的无穷辛酸和灾难。他的诗,博得“诗史”的美称,绝不是偶然的。
清明踏青,是北宋时期一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愁,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猎取这一盛况,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柳永通过对这一民俗的描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词的上片写太平盛世繁华都市中的春游。词一开篇即写景,“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这时候写的是自然景观,并且指明了这些景物是在“神州”,也就是汴京。接下来,“是处楼台”三句写都市人文景观,以“是以”二字开始,写出了都市繁华的广泛程度;后又以“腾沸”二字结束,写出了都市繁华的热闹程度。接下来是游春盛况的叙写。“游人”之“恣”,“驰骤”之“无限”,从行动上写出了游春人的心情舒朗,无拘无束;“娇马车如水”的比喻,借用了李煜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多少恨》),概写游春盛况,“寻芳选胜”则具体写游人的行踪,冠以“竞”字写出了游春人争先恐后的恣游心态。“归来向晚”对照开头“艳阳景”,表明游春活动从清晨的艳阳初升延续到黄昏日暮。结句“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可以说是游春活动的尾声了,以一“起”字领起,不仅极具画面感,且情韵无尽。
这首词的上片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北宋前期太平盛世都市繁荣,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繁红”、“嫩绿”、“艳阳”、“朱门”、“新声”、“通衢”、“香尘”等一连串带有修饰性的词的运用,以及“明媚”、“腾沸”、“如水”、“近远”、“细细”等一连串工笔描写,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汴京春日的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上片都可以说是整首词的精华所在。
词的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太平世”,直言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少年时”二句说自己还处于少年时期,不忍心把美好的时光轻易抛弃。“况有红妆”二句说自己有美女相伴,连用“红妆”、“楚腰”、“越艳”三个词来形容相伴歌女的美貌,之后,词人又引用了一个典故,出自王仁裕《开宝天元遗事》,书中说宫廷乐工许合子“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词人还用了“何啻”二字,说她们“一笑”何值“千金”,不仅突出了相伴美女的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词人当时的奢侈生活。接下来,“向尊前”二句写歌舞之盛,此处多用典故。先写舞,“舞袖飘雪”,典故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后写歌,“歌响行云止”,引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有美女相伴,又有歌舞欣赏,故而词人说“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希望用绳子把太阳系住,以便“从容痛饮”。这种挽留时光的方式独特、浪漫,表现了词人对少年韶光易逝的惶恐和无奈。
词中以自然的春光和人生的青春交相阐发,由珍惜春天而有珍惜青春的感慨。在词人看来,明媚的春天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也同样提醒人们去尽情享受青春,不妨千金买笑、从容痛饮。“少年时”二句,体现出词人对人生短暂、青春更短的忧惧之心,所谓及时行乐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抵御而已。
首联点出登楼的缘由和时间。“东郡”,在汉代是兖州所辖九郡之一。“趋庭”用《论语·季氏》孔丘的儿子“鲤趋而过庭”的故事,指明是因探亲来到兖州,借此机会登城楼“纵目”观赏。“初”字确指这是首次登楼。
颔联写“纵目”所见形势。“海”指渤海,“岱”指泰山,都在青州境。兖、青、徐等州均在山东、江苏一带。“浮云”、“平野”四字,用烘托法表现兖与邻州都位于辽阔平野之中,浮云笼罩,难以分辨。“连”“入”二字从地理角度加以定向,兖州往东与海“连”接,往西伸“入”楚地。不但壮观,且传神。
颈联写纵目所见胜迹,并引起怀古之情。“孤嶂”指今山东邹县东南的峄山。“秦碑”,指秦始皇登峄山时臣下“颂”德的石刻。“在”指尚在。“荒城”指曲阜。“鲁殿”,指县东二里的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鲁灵光殿,“余”指残存。“在”、“余”二字从历史角度进行选点,秦碑、鲁殿在“孤嶂”、“荒城”中经受历史长河之冲刷,一存一残,个中原因是很能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
尾联是全诗的总结。“从来”意为向来如此。“古意”承颈联“秦碑”来。“多”说明深广。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诗人自指,意为诗人向来怀古情深,其一指兖州,是说早在东汉开始兖州建置前,它就以古迹众多闻名。这就是杜甫登楼远眺,会生起怀古情思的原因。“临眺”与颔联“纵目”相照应。“踌躇”,徘徊。“独”字很能表现杜甫不忍离去时的“独”特感受。前人解释:“曰‘从来’则平昔怀抱可知;曰‘独’则登楼者未必皆知”。(赵汸)很能道出尾联的深沉含意。此诗是杜甫二十九岁时作,是杜甫现存最早的一首五律诗。此诗已初次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明代李梦阳把“迭景者意必二”作为“律诗三昧”之一。
此诗虽属旅游题材,但诗人从纵横两方面,即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分别进行观览与思考,从而表达出登楼临眺时触动的个人感受,是颇具特色的。诗人一方面广览祖国的山海壮观,一方面回顾前朝的历史胜迹,而更多的是由临眺而勾引起的怀“古”意识。在艺术上此诗一、二、三联均运用了工整的对句。“ 东郡”、“南楼”,“趋庭”、“纵目”,“浮云”、“平野”,“海岱”、“青徐”,“孤嶂”、“荒城”,“秦碑”、“鲁殿”,都是实写。尾联才由“临眺”引出思“古”之“意”,则带有虚写的意味。而二、三联“连”、“入”、“在”、“余”四字,通过对仗,将海岱连接,平野延伸,秦碑虽存,鲁殿已残等自然景观与历史胜迹,在动态中分别表现出来。尾联“多”、“独”二字尤能传达作者深沉历史反思与个人独特感受。无怪乎叶石林评论说:“诗人以一字为工”,“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
柳宗元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冬贬至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应当是第二年春以后的事情。观此诗,柳宗元心情已较平静,又新茶当采于春天,王国安先生《柳宗元诗笺释》认为此诗作于公元807年(元和二年)春,可从。
茶叶的品质好坏,直接与茶树的种类、采摘的时间、当地的气候等多种因素相关。茶树喜好阴凉湿润,刘禹锡《试茶歌》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可知古人认为竹下茶最佳。重巽所赠茶叶,正是所谓竹间茶。
这首诗开头两句是说,这茶树生长在密密的斑竹林中,为清莹的雨露所滋润,“湘竹”二字既给茶叶赋予了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又照应到诗题“竹间”二字。富有经验的采茶者都知道,采茶时间最好是每年初春谷雨前后的新芽之时,若在清晨日出前带露采摘其品质更高。诗中第三四句说重巽亲自“晨朝掇芽”,表现出重巽深懂茶道,正合采茶之法。采茶的时间是否适当,对茶叶品质的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中用一个“复”字。这个“复”字,乍读之下,很难理解和译出,其实是把奇特的竹间茶树和正确的采摘时间两方面联系起来。第三四句诗,既说明了茶叶品质美好的另一个原因,又与诗题中“自采新茶”四字相照应。茶叶又以高山云雾茶为佳,诗中第五六句诗所说的“蒸烟”和“丹崖”,正是指明了云雾和高山这两点,表明了茶叶品质上乘。第七句是说盛装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之美,色泽之奇之特,间接衬托出了这茶叶的名贵与稀罕。第八句则是用典故比喻,直接评述茶叶品质的纯美无瑕。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惊赞茶叶香气的奇妙。首先是香气持久悠长。第十句,“馀馥”是说香气不是一飘而尽,而是久留不散。“延”指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幽遐”则指香气传到了很深很远的地方。其次是茶香的神奇功效。喝了好茶,可以提神、祛秽,诗中的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就是围绕这两方面来说的。“荡昏”,即清除心神上的昏沉困倦,可以提神。“荡邪”,就是除秽。“涤虑”,就是洗去心中的烦躁,去掉昏惑和邪气,保持心神的安宁和清醒。这样,喝好茶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这是一般人从生理角度来理解的。然而柳宗元则从心理角度加以发挥,提升到了人的精神思想品格的高度来评价好茶的妙用。“涤虑发真照”,是说茶香净化了人的思想道德,显露出人的毫无污染的真情本相。“还源荡昏邪”,是说茶香清除了精神意识中的昏浊邪恶,使人回复到自然天性,保持清白纯洁的境界。可见,诗人在此用到了双关象征手法,这么立意构思,就非常巧妙深刻,富有诗意。正因为这茶香不仅有益于人的生理健康,还能有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使人脱俗,所以才是最为神妙的珍异的上品。也正因为这茶叶具有这样的神奇功效,所以下面柳宗元连用佛教道教中的两种神奇的故事来加以比较。佛祖如来的甘露饭,香气熏染了毗耶城和大千世界,其实是说佛法广大,教化感人,使人皈依正道。道家仙客所饮流霞仙酒,使人数月不饥,其实是丹药神力,使人清心寡欲,不贪不痴,修成仙体。它们同为食物,都具有神奇功效,所以柳宗元用它们来与茶叶相比。不过,柳宗元自己更为信佛,而且斋饭、茶叶易得,流霞难求,所以诗中要说香茶“犹同”甘露饭,而“贵”于流霞。
对这珍贵的名茶,柳宗元自然十分赞赏和珍视,但是既为其物,更为其人,因为这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时的第一位友人所赠,且为亲手所采,关爱殷切,情意殷深,使困窘中的柳宗元倍感精神上的慰藉和友情的可贵。赞美茶叶,其实更是赞美友人的情谊。所以柳宗元要用“金鼎”烹茶,要以自作新诗回赠,更要从精神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
此诗以夕阳黄昏的江天为观察点,敏锐地捕捉了大自然昼夜转换之际奇妙的景观。诗的一、二两句描绘出一幅壮美的图画,此时太阳刚好落山,平静的江面上,水气不断蒸发积聚,飘浮弥漫,使湛绿的江水更绿更暗,加上光线折射,成为一片朦胧的“绿雾”,向远处延伸。天西边,残余的阳光从地平线后面射入室中,将云彩照亮,形状是由宽而窄,向高处耸起,仿佛无数重叠的峰峦;颜色是浓紫鲜红,光怪陆离,大自然在如此广阔的范围急遽地变幻出奇异的景象,场面是伟大而壮观的。红的晚霞与绿的江水分割了整个画面,形成上红下绿异常饱满的两大色块。红与绿是两种互补的色彩,在一幅画面中交相辉映,显得酣畅淋漓。两句诗用了五个形容词,“绿雾”、“凉波”,状物十分形象,尤其第二句,“巘”比喻云霞,又连用“叠”、“红”、“嵯峨”三个形容词对其形状、色彩加以修饰,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视觉感受。与此诗相似的,有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吴融《江行》:“霞低水远碧翻红,一棹无边落照中。”两人写出了江水瞬息变化的奇丽景象,而场面的壮观似均不及李贺此诗。
三、四两句,对江上景物作细节的描写。风云随处皆有,因与江水相关,故称“水风浦云”。“生老竹”与前面“起凉波”句子形式完全一样,但前面所写是事实,这儿只是一种印象。李肇《国史补》下说:“杨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樛,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傍晚天气转凉,而竹林给人的感觉是清寒的,所以说水上的微风,岸边的云霭,仿佛是从竹林里生出来的。天色渐暗,江中小洲笼罩在暮色苍茫之中,远望蒲帆,像是整幅一样。这里,诗人抓住主观感受上的错觉,生动地表现出大自然的某种变化,笔调相当细腻。
五、六两句写江南人民的生活。鲈鱼是江南名产,以产于松江者最佳。《吴郡志》载:“天下之鲈两腮,惟松江之鲈四腮。”晋代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吹起,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弃官而归,是有关鲈鱼的著名故事。“鲈鱼千头酒百斛”,凭藉着造物无私的奉献,南人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薄暮之中,酒半醉卧,苍翠的山峦宛然在目,非常悠闲自得。
最后两句,承五、六两句,谓人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酒醉兴浓,不禁唱起歌来。“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在生长于北方的诗人听来,一定很有情味。吟唱未终,不觉圆月已从江面升起,此情此景,物我俱化而难分彼此了。“江上团团贴寒玉”句,描写极为精确,“团团”指月轮的形状,“寒”指感觉,“玉”喻质地与颜色,着一“贴”字,形容月亮如同明玉粘附、镶嵌在天幕上。李贺写诗,很少用白描手法,而是借助想象强调事物多方面的性质,使画面变得更鲜明、凸出,具有立体的感觉。此句与孟浩然《宿建德江》中“江清月近人”对读,一则极力描摹,一则淡中有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调。
此诗从开头的江中绿雾到结尾的江上寒月,以江水为中心展开了一幅长的画卷,红霞与江水相接,远山是江边所见,南人在江畔宴饮,吃的是江中之鲈,水风浦云,洲诸蒲帆,无一不与江水相关。诗中景物颇为繁复,层次却十分清晰,时间上,从夕阳西坠至明月东升是一条线索。与此相关,一是气温降低,先说凉波、水风,又说寒玉,感觉越来越清楚。一是光线减弱,看天上红霞是鲜明的,看水中蒲帆已不甚分明,到月亮升起的时候,地上景物更模糊了。结构上,前四句描写景物,是第一条线;后四句叙述人事,是第二条线,但此时第一条线并未中断,而是若隐若显,起着照应与陪衬的作用,如第六句出现南山的景致,七、八两句写吟唱未终,江月照人,人与景融合为一,两条线索被巧妙地结合起来。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此诗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