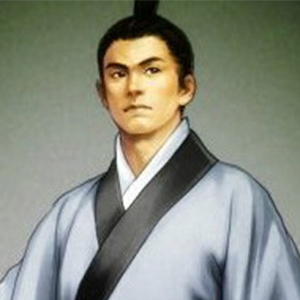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
诗的前两联即描写沧浪亭的静谧。首先诗人安排了“静”的背景,营造出“静”的意境:“独绕虚亭步石矼”。“独”“虚”二字表明诗人此时是独自一人在沧浪亭中散步。偌大的园林,四处静谧无声,或许有人会感到冷清孤寂,而诗人却专爱这“静中情味世无双”的空静淡雅的氛围。静谧中的心情和滋味独一无二,颔联就此进一步展开,加以具体详细的描写和说明。
“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入破窗”,前一句以动写静,后一句化静为动,更显出“沧浪亭”的幽静和诗人此刻平和自乐的情绪。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动写静的名句当属六朝梁代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鸣蝉的鼓噪声,飞鸟的清鸣声,才更反衬出林间山中的静寂、清幽。“静”的意境极难表现,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论画道:“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俨静,趣远之心难形”。意即画面容易表现实物的形状动感,难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营造出澹泊闲静的意境则是难上加难。诗画同源,二者在艺术表现手去上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古代诗人多采用寂中有音、动中见静的手法,利用能引发人们特殊感受的声响和动态来反衬静境和静意。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得愈觉其深”(《管锥篇》)。这里的“山蝉带响”也正是利用蝉声来突出环境的清幽宁静,韵噪相映,反衬其静,给人以极为真实贴切的感受。此外前人诗中也常运用化静为动的表现手法,六朝宋代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的诗句,不仅将相对静止的白云、绿竹拟人化,同时赋予二者以动感,这种拟人手法和化静为动手法的的运用,更能雄现出平中见奇、似动实静的特色。此诗中“野蔓盘青入”便是将藤蔓这一静物动态化,写出了它在盘旋回绕中偷偷伸进破旧窗子的“动”的过程,这种“动”,更深化了沧浪亭中安静的气氛。胡仔评价苏舜钦说:“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此联可做为典型的一例。
后两联引用两个典故,将它们与诗人的情况相对照,以此来表明诗人平静恬淡的心情。“二子逢时犹死饿”是写伯夷和叔齐的故事。一般认为,周朝开国初年可谓太平盛世,两人生而逢时却因不食周粟而死;“三闾遭逐便沉江”是写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他遭人构陷,放逐湖南湘江一带,而后自投汩罗江。诗人与屈原一样受人毁谤而遭贬,与伯夷、叔齐一样适逢政治革新的年代,但却无所作为。即使这样,诗人并未意志消沉投江而死,也并未“拒依周粟”忍饥而亡,而是每天尚能“饱食高眠”。因而诗人颇觉心满意足,欢欣庆幸。与历史人物的悲惨遭遇相比,诗人遭贬谪但仍能隐居沧浪亭算是十分幸运。所以他在沧浪亭的静谧环境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离实远祸、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沧浪亭》),因而他觉得“静中情味世无双”。
诗人的心境当然不像沧浪亭的静景一样平静如水。苏舜钦以迁客身份退居苏州,内心愁怨交集,万分感慨。他本是“慷慨有大志”的志士,以“出手洗乾坤”(《夏热屋寝感咏》)为已任,结果却是“予年己壮志未行”(《对酒》),苍生有难未能济,只能隐居园林,聊以度日。对于他这种“致君事业堆胸臆”的人来说,“却伴溪童学钓鱼”(《西轩垂钓偶作》)的闲居生活极为压抑。“修竹慰愁颜”(《沧浪亭》),“愁与酒相攻”(《春日怀旧游》),“大叫欲发狂”(《舟中感怀》),这些退隐后的诗句都渲泄出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愤之情。
本诗尾联中“唯恨澄醪不满缸”,以夸张的手法,表面是强调自己了无牵挂,心如止水的恬淡生活,而从反面映衬出诗人内心的怨懑、牢骚和不满。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陶渊明善于把人所共知、反习而不察的人生体验指点出来,而且用的是极自然极简练的语言。这往往使人感到又惊讶又亲切。此二句即一好例。诗人回忆自己少壮时代,即便没有遇上快乐的事情,心里也自然地充满了欣悦。对于人类来说,珍惜生命价值、珍惜寸阴之精神乃是长青的。“无乐自欣豫”的“自”字,下得准确而微妙,直道出年青生命自身无穷的活力与快乐。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向上的生命情调。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向上的精神生命受了文化的教养,便升华出“猛志”。按照传统文化,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志向。“猛志”之猛,突出此志向之奋发、凌厉。“逸”,突出此志向之远大、超越。“骞翮”即展翅,“翥”者、飞也。猛志所向,超越四海,有如大鹏展翅,志在高飞远举。以上四句回忆少壮时代生命情调,诗情从容之中,而有飞扬之势。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年光苒苒流逝,当年那种雄心,渐渐离开了自己。诗情由此亦转为沉抑。“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即便遇上了欢乐的事情,也不再能欢乐起来,相反,常常怀有深深的忧虑。此二句写出人到中年、晚年之体验,与起笔二句形成深刻对照。诗人对自己的遭遇、时代,一概略而不言,唯反求诸己。所以写出的实为一种人生体验之提炼,一种生命自身的忧患意识。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气力渐渐衰退,转而感到一天不如一天了。深感形体生命的逐渐衰老,这还仅仅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一层次。“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壑舟”语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此处是借用“壑舟”喻指生命。观下二句中“止泊”二字,即承“壑舟”而来,可证。此四句,语气连贯为一意群。生命耗逝,片刻不停,使自己不得停留地走向衰老。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未来的人生道路,不知还有多少途程,也不知生命之归宿将在何处。联系上文之“猛志”及下文之结笔,则此二句之意蕴,实为志业未成之隐忧。生命日渐有限,而生命之价值尚未实现,这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二层次。
结笔乃更进一层:“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生命之价值是在每一寸光阴之中实现的,寸阴可惜。古人珍惜寸阴,顾念及此,不能不使人警惧怵惕!珍惜寸阴,念此警惧,足见犹思奋发有为,此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三层次,亦是其忧患意识之一提升。结笔二句,深沉、有力。其启示意义,乃是常新的。
渊明此诗之主题意义,为一种生命之忧患意识。此种忧患意识之特质,是形体生命逐渐衰老,而生命之价值尚未能实现,终于产生再奋发再努力之自我觉悟。按照中国文化传统,主体价值之实现,有三种模式。“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立德是为第一义。陶渊明之一生,于立功的一面,虽然未能达成,可是,在立德、立言两方面,却已经不朽。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可以说,若没有“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之精神,陶渊明之成其为陶渊明,将是不可想像的。
此诗在三个时间点上辐射和展开意象:其一,回首过去,生命意象是展翅高飞的大鹏,情调是“昂扬”、“欣豫”;其二,察视现在,生命意象是生命力锋颖的衰颓与磨损。情调是“忧虑”“无复娱”;其三,眺望未来,生命意象是前途无几许的孤舟。情调是“忧惧交加”。时间的跳跃交错,生命的盛衰交替,情调的忧、乐、惧交织,使此诗仿佛是一个时间与生命的三重奏,展现了丰富而深沉的人生体验的全过程。
全幅诗篇,呈为一种苍凉深沉之风格。诗中包蕴了少壮时之欣悦,中晚年之忧虑,及珍惜寸阴之警惧。诗情之波澜,亦由飞扬而沉抑,终至于向上提升。全诗体现着陶诗文体省净而包蕴深远的基本特色。这种特色,实为中国诗歌艺术造诣之一极致。
词上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纵横千万里,展示了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下片议论抒情,重点评论历史人物,歌颂当代英雄,抒发无产阶级要做世界的真正主人的豪情壮志。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于一炉,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
上片描写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三句总写北国雪景,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北国风光”是上片内容的总领句。“千里”“万里”两句是交错说的,即千万里都是冰封,千万里都是雪飘。诗人登高远望,眼界极为广阔,但是“千里”“万里”都远非目力所及,这是诗人的视野在想像之中延伸扩展,意境更加开阔,气魄非常宏大。天地茫茫,纯然一色,包容一切。“冰封”凝然安静,“雪飘”舞姿轻盈,静动相衬,静穆之中又有飘舞的动态。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望”字统领下文,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句。这里的“望”,有登高远眺的意思并有很大的想像成分,它显示了诗人自身的形象,使人感受到他那豪迈的意兴。“望”字之下,展现了长城、黄河、山脉、高原这些最能反映北国风貌的雄伟景观,这些景观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长城内外”,这是从南到北,“大河上下”,这是自西向东,地域如此广袤,正与前面“千里”“万里”两句相照应。意境的大气磅礴,显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分别照应“雪飘”“冰封”。“惟余”二字,强化了白茫茫的壮阔景象。“顿失”二字,则写出变化之速,寒威之烈,又使人联想到未冰封时大河滚滚滔滔的雄壮气势。这四句用视觉形象,赋予冰封雪飘的风光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直觉,更显气象的奇伟雄浑。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动态描写,都有活泼奔放的气势。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表现“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山”“原”都是静物,写它们“舞”“驰”,这化静为动的浪漫想像,固然因在大雪飘飞中远望山势和丘陵绵延起伏,确有山舞原驰的动感,更因诗人情感的跃动,使他眼前的大自然也显得生气勃勃,生动活跃。。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写的是虚景,与前十句写眼前的实景形成对比,想像雪后晴日当空的景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雪后的景象则显得娇艳。“看”字与“望”字照应;“红装素裹”,把江山美景比做少女的衣装,形容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的艳丽景象。“分外妖娆”,赞美的激情溢于言表。
下片由毛泽东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感叹,并引出秦皇汉武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英雄人物,抒发作者伟大的抱负及胸怀。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谓承上启下,将全词连接得天衣无缝。“江山如此多娇”承上,总括上片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总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下,展开对历代英雄的评论,抒发诗人的抱负。这一过渡使全词浑然一体,给人严丝合缝、完整无隙的感受。祖国的山河如此美好,难怪引得古今许多英雄人物为之倾倒,争着为统一天下而奋斗。一个“竞”字,写出英雄之间激烈的争斗,写出一代代英雄的相继崛起和衰落的经历。“折腰”的形象,展示了每位英雄人物为之倾倒的姿态,并揭示了为之奋斗的动机。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总领七个句子,展开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诗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五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具体形象地展开,如同翻阅一部千秋史册,一一加以评说。一个“惜”字,定下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基调,饱含惋惜之情而又有批判。然而措词极有分寸,“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并不是一概否定。至于成吉思汗,欲抑先扬,在起伏的文势中不但有惋惜之极的意味,而且用了“只识”二字而带有嘲讽之意。“弯弓射大雕”,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成吉思汗只恃武功而不知文治的形象。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三字,言有尽而意无穷,有画龙点睛之妙。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诗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的使命,超越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是诗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刻豪情万丈,那一刻傲视古今。
《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
全词用字遣词,设喻用典,明快有力,挥洒自如,辞义畅达,一泻千里。全词合律入韵,似无意而为之。虽属旧体却给读者以面貌一新之感。不单是从词境中表达出的新的精神世界,而首先是意象表达系统的词语,鲜活生动,凝练通俗,易诵易唱易记。
这首词上片写想象中的汴京元夜之景,下片写现实中羁旅穷愁,无法排遣的一种无奈心情。上片虚写,下片实写;一虚一实,虚为宾,实为主。
首句“闻道长安灯夜好”,“长安”点“都城”,即汴京。“灯夜好”点“元夕”。词题即在首句点出。“闻道”二字,点明都城元夕的热闹景象都是神游,并非实境。不过,这“神游”并不是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也不是对于期待中的未来的憧憬,更不是梦境,而是在同一时刻对另一空间的想象,即处凄冷之境的“江南憔悴客”对汴京元夜热闹景象的想象。摆脱现实的束缚,按照自己潜在的心愿作几乎是无限的发挥。“雕轮宝马如云”毛滂这一句极言“雕轮宝马”之多(“如云”)。词人把都城元夕的繁华景象描摹尽致。但是,这一片繁华都只是词人想象的产物,首句“闻道”二字点明了这一点。上片越是写得繁华热闹,则越是反衬出下片凄清冷寂的尴尬之状。下面三句词人把汴京元夜从地上移到了天上,以想象中的仙境喻都城元夕的盛况。“蓬莱清浅对觚棱”是描写汴京元宵之夜宛如神仙境界。“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碧落”,犹碧天。“玉皇”句中的“开”字启人想象。言“开”,则“碧落”原是“闭”着的,只是在上元之夜,玉皇才将原是“闭”着的“碧落”“开”了。“碧落”既“开”,则天上的星儿、宿儿便纷纷下落,使“银界失黄昏”了。词人的写法无非是把人间的皇帝搬到了天上,以在想象中染上一层迷离恍惚的色彩,使帝京元夜在词人的表现中更加热闹罢了。
下片首句,“江南憔悴客”是作者自指。“谁见”,设问之辞,意即无人见。特指作者自己深深思念的妻子反不知自己待罪客舍的窘境。这一句,以设问的口气写出了自己的孤寂。“谁见”二字还将读者(也使作者自己)从想象中的繁华景象拉回到凄冷的现实中来。“端忧懒步芳尘”,这是写闺中人对那元夜的繁华早已失去了兴趣,毛滂词中的闺中人则无须去“寻”,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远在千里之外,乃“懒”去那元夜繁华之地。她只在闺房中,在“小屏风畔”,独对薰香袅袅,薰香则渐冷而凝。一种无奈之状展现在读者眼前,像是一幅画得极高明的《闺中夜思图》。这种描写,只是词人的设想,但是设想闺中人在思念自己,也就更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在思念闺中人。“酒浓”句,词人从对闺中人的思念中回到现实中来。上元之夜,本应是欢乐之夕,而作者自己却处在待罪羁旅、凄冷孤寂的心境中,去消受那本不应如此凄清的元夜之夕。“春梦”只能于“酒浓”时去做。而酒并不能真的解忧,它只是使人于麻醉中暂时忘却而已。结句“窗破月寻人”,写词人孤寂一个,只有元夕之月伴春梦之人。“寻”字,以人拟月。这位“江南憔悴客”,待罪羁旅,没有人去“寻”他,只有月从客舍的破窗隙中来“寻”,越显其孤独寂寞,心情已从凄冷变成凄苦了。
这首词以乐景写哀情,将词人羁滞异乡、困顿潦倒、憔悴不堪的苦境与悲怀抒写得缠绵悱恻 。然而,尽管词人满怀苦情,却又以飘逸秀雅的笔调抒写内心的情怀,使全词充满了潇洒风流的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