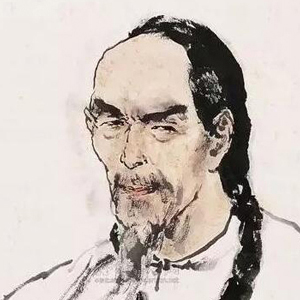这首乡情词,描写的农村是一片升平气象,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有酒有肉,丰衣足食,太理想化了。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江南广大农村局部的安宁是有的,但也很难设想,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幸福、愉快。当然,这不是说辛弃疾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因为他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大限制了他的眼界,对生活的认识不免受到局限。
上阕写闲居带湖的满足及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上句写景,说山园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笼,环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描绘楼台亭阁的宏丽,那就不足以显示是隐居了,而会变为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争的知足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得无厌之徒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一“足”字,表达了词人对居住环境、生活的满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从一个侧面来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同邻里的关系融洽,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老。估计词人这时,已是年过半百。“分社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后分享祭社神的肉。据下文,这里所说的应是秋社分肉。下句说山园富有。李白《南陵叙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肥。”如此说富有,意近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社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成,岂不正好惬意地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使人想起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阕摄取一个情趣盎然的生活镜头直接入词,更使此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既有很强的情节性,又具强烈的行动性、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画家把这场面稍事勾勒、着色,就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农村风俗画;如果作家用散文把这场面和人物的活动记下来,又可成功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小品。只是平常的几句话却具绘画的立体美,又具散文的情节美,稼轩运用语言文字功力娴熟,由此也可见一斑。下阕“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西风犁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藉“西风”点明时间是在秋天。“犁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犁树和枣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把长竿”,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甚似特写镜头:一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偷着扑打犁、枣。“偷”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了这群馋嘴的儿童,一边扑打着犁、枣,一边东张西望地提防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一个“偷”字,写出了贪嘴孩子的天真童趣和心虚胆怯、唯恐被人发现的神情。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偷梨、枣的儿童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又呈吴郎》的“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已及人,出于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的同情。作者是在“万事人今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儿童有趣,要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仁”心,语言深沉,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后的“闲”情,笔调轻快。一“闲”字,是指在“万事从今足”的心态下,作者觉得“偷梨枣”的儿童顽皮、有趣,展现出作者的悠闲;轻快笔调之中,透露出对当前生活的喜悦之情。一个“看”字,既有观看之意,又有看护之意,表现了诗人对“偷”梨和枣的儿童欣赏、爱护之情。
陆游乡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它通篇无奇字,无丽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人公形象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实在耐人寻味,这也正是它“简淡”的妙处。
“玉楼春”是词调名,据《词谱》载:“因顾穂词中有‘月照玉楼春漏促’,又有‘柳映玉楼春日晚’;五代欧阳炯词中有‘日照玉楼花似锦,楼上醉和春色寝’;又有‘春早玉楼烟雨夜’句,遂取为调名。”又名《木兰花》、《玉楼春令》、《西湖曲》、《归朝欢令》等。双调五十六字。
“华堂帘幕飘香雾,一搦楚腰轻束素。翩跹舞态燕还惊,绰约妆容花尽妒。”《韩非子》载:“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上片重点刻画伊人的美妙绝伦,采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她形容得简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了。这里的“燕”,既指燕子,又暗指汉代的赵飞燕。汉宫美人赵飞燕纤腰一把,舞姿绝妙,传说她身轻如燕,能立于掌中。
“绰约妆容花尽妒”化用《长恨歌》中对杨玉环的描写:“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在词人的眼里,这位佳人仿佛就是赵飞燕,又依稀好像杨玉环,兼具二人之美,于是情不自禁而生爱慕之意。
“樽前漫咏《高唐赋》,巫峡云深留不住”这两句化用“巫山云雨”的典故,委婉地表达其未能拥有美人的惆怅。
“重来花畔倚栏杆,愁满栏杆无倚处。”此二句进一步刻画主人公的相思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