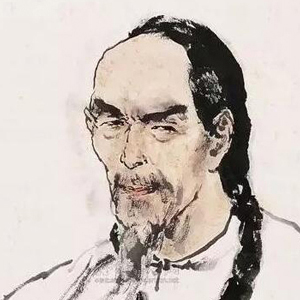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第一首小令着重写由旱而雨的转变给作者带来的畅快心情,一场雨水的到来让人们能够“欢颜笑颜”;第二首小令从“雨”本身的刻画来展现内心满满的喜悦,描写了雨后庄稼茂盛生长之景。全曲借景抒情,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轻快活泼,饶有情趣。
第一首,无尽等待之后雨水终于降临,绵绵连连地下着,冲刷着灰头土脸的村城,充盈着枯渴已久的水井,滋润着裸露龟裂的河床。作者望着及时好雨生发出幸福憧憬:田家能够吃到用高粱米煮的“薥秫饭”,书馆中清贫的生活也有了保证,耕读生活因为雨水的降临而显得更为安然自适。由己及人想得再远些罢,仿佛又已经看到秋天人们收完田间庄稼,带着欢颜笑语来到场园中纳稼,相互诉说着自家今年丰厚的年成。因为好雨带来的“年成变”让作者心间欢喜无限,而通过作者笔下欢快的联想又仿佛看到了农人们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真切感受到农家平凡但不平淡的安乐生活。
第二首,作者从“雨”本身的刻画来展现内心满满的喜悦,由景生情的生动描写更能传达作者昂扬快意的情绪。“初添野水涯”从视觉上写出雨水降临使得野水漫涨的开阔景象,着一“初”字生动地写出作者因为长久热切的期盼而对雨水降临之时的分外关注,含蓄地传达出等待雨水的焦急心绪以及喜雨初降的疏放快意。“细滴茅檐下”则能从听觉上感受到雨水顺着茅檐滴落发出滴滴答答的轻快雨声,用一“细”字既写出雨水的细密丰沛又写出作者的观察入微,同时将喜雨带来的快感渗透在曲句之中。“喜芃芃遍地桑麻”描写的是作者在雨中看到的可喜景象,用“芃芃”二字写出遍地桑麻在雨水的浇灌下生长茂盛的样子,直接用“喜”字强化雨中观望的欢快情绪,对于农人来说,及时雨能够带来的好收成比什么都值得高兴。前三句写雨景,景语句句含情,作者因喜雨而生发的“喜”的情绪溢于言表。
“消灾不数千金价,救苦重生八口家”,作者饱含深情地写出普通百姓靠天吃饭的真实心声,由此能够真切体会农人在遭受旱灾、濒临绝境之后突逢淋漓喜雨陡然畅快、喜不自胜的心情。作者在表述中将喜雨拟人化,使得喜雨具有了为百姓消灾救苦的观世音菩萨一般的慈悲胸怀,直剖心声式的叙写让喜雨具有了别样的生命情怀,更加突出作者对及时喜雨的盛赞和感激。
小令的末三句,写作者目睹好雨连绵,因为满心的喜悦生发出美好的想象:花开得热烈,瓜结得硕大。作者巧妙地将全曲的焦点收束在“葫芦棚”中一个耀眼的“赤金瓜”上,由点及面地遐想喜雨之后的一派丰收景象。此首小令描摹细致、想象鲜活,通过自然纯朴的语言,按照盼、看、听、想的内在思路,使难以言表的喜悦情绪在字句的锤炼、意象的捕捉、细节的描写中完全迸发出来,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
综观两首小令,因为及时好雨而生发无尽喜悦,一方面展现了归隐田园的作者源于生活的真实内心感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具有悯农情怀的作者与农人息息相通的深层情感。语言清新活泼,情感强烈真挚,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及时好雨的赞美、感激和喜爱。
这首词写羁旅在外,路过旧日与亲友分别的地方,而引起的惆怅之情。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抒情,然而又都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先看首句,“又到绿杨曾折处”,诗人不直陈痛楚,而将其深隐于“绿杨”依依之中,这种隐忍使情意又深了一层。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曾”,完成了时空上的移位与重叠。故地重游,绿杨依旧,一如当初折柳相望、依依不舍之时(因“柳”与“留”谐音,古人在送别时有折柳相送的习俗)——谁料如今物是人非,竟只剩下自己孤独漫游。昨天——今天,两个既同又异,亦幻亦真的片断,彼此交叠,诗句便多了一层深婉迷离的意趣。这种不经意(这种不经意的写法必定经过诗人精妙的提炼才不露斧痕)营造的时空上的错乱,近乎幻觉,也接近了思念的极致。试想一下,若不是最深沉最痛切的思念又怎么令人如此恍惚、迷惘。
承接首句,“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看似平铺而下,其实布局精巧。“不语”承接首句的惝恍迷离的状态,而“垂鞭”已将诗人的思绪引回到现实之中。“垂鞭”意指诗人心绪沉重,纵马缓行。马足所及,又轻轻勾连“踏遍”一句。从时间上看,这两句完成了从“昨”到“今”的交接,回忆转瞬即逝,只剩下冰冷的现实、意念成灰的自己;而从空间上看,这两句将思绪由“折柳处”引向了“衰草连天”更为广褒的空间。于是诗人在现实中痛感自己的孤单无依,也不得不面对无边无际的“清秋”“衰草”,无力地抵挡着秋意凄凉的侵蚀。意犹未尽,“雁声”又将秋意带到“萧关”更遥远的地域;一个“远”字,令愁情绵延不尽。 下片的“天涯”收结了上文,也极言“行役”之遥远之漫长。分明苦不堪言,偏偏还说“不恨”,翻出新意,更为后文“只恨西风”伏笔——原来还有可恨之事甚于“天涯行役”之苦。
“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出语新巧、奇警,含意蕴藉、深长。“吹梦”之说不是首创,较早见于南朝民歌《西洲曲》:“南风吹我意,吹梦到西洲”。但两者各尽其妙,并不雷同。风吹梦,本来给人以无限迷朦、无尽怅惘的意味,由典故中的熏暖的“南风”变为可恨的“西风”,却陡增了几分凌厉、残酷的意味。如果说南风是传递爱情的浪漫信使,为何西风却要一下子将美梦吹散吹灭?只因诗人所要抒发是天涯羁旅、人各一方的怨恨,而不是《西洲曲》中少年春心萌动、欲诉相思的闲愁。把梦吹成了“今古”应属诗人首创,妙就妙在:它在前面对空间极力拓宽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对时间的无限延伸——于是,诗歌的时空结构便变得更加辽阔、苍茫了。
最后以“明日客程”收结,一片“雨”色里,全诗笼罩在朦胧凄冷的情调之中。总而言之,在这首短小的词里,诗人着意拓展了诗歌的时空,遂令天之悠悠、地之茫茫,无时不怀想,无处不相思,写出了思念之极致。这份穿越时空的思念,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