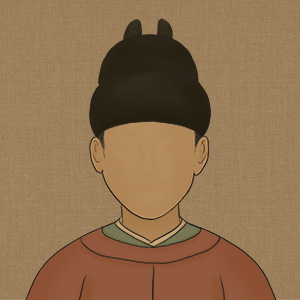上片抒写别后相思之情。起句“话杀浑闲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隐应辛弃疾答词中“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一语,谓去年相叙虽得极论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之时,虽有壮怀长策,亦无从施展,说得再多都只是闲说一场罢了。“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紧承前语,补明“话杀浑闲说”的原因。意谓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有在位者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无法去做的,所以说尽了等于没说。此言亦对辛弃疾寄词中称许陈亮“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语而发。其时陈亮尚为平民百姓,辛弃疾则久被罢黜,故有此慨叹。恢复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却日趋衰老,思念及此,更增忧惧,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此言复应辛弃疾答词中“老大那堪说”及“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数语,其中蕴含着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既有去年风雪中抵掌谈论的欢欣,也有眼前关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还有同遭谗沮而早生白发的悲愤。“百世”句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及《战国策·齐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语意,极言相知之难。夫万世遇之尚如旦暮,则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岂是接踵可得?是以见其难也。
此语言简意赅,复多曲折,然无板滞晦涩之病,表现出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语则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极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者既甚难得,则会少离多自更难堪。此时孤独之感既不能排遣,忧愤之情又无可倾诉,真是度日如年了。“写旧恨,向谁瑟”即表现此种不胜惆怅的心情。“瑟”字名词动化,“向谁瑟”即向谁弹,向谁诉。
换头从离别的愁苦中挣脱出来,转作雄豪豁达之语:“男儿何用伤离别?”异军特起,换出新意。接下又推进一层:“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壮声英概,跃然纸上。“风从云合”语出《易·乾·九五》:“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喻同类相从,借喻群英共事。意谓古来英雄豪杰皆建功立业,志在四方,故不须以离别为念。上二语亦隐应辛弃疾寄词中“佳人重约还轻别”至“此地行人销骨”诸句,用豪言壮语来安尉朋友,更见情深而意切。“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二句则隐应辛弃疾寄词中“正目断、关河路绝”一语,谓友人虽远隔千里,而情分亲厚,便即如终日晤对,于我之本心能善于体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卧百尺高楼斗绝”一句插入陈登故事,盛赞故人豪气。“斗绝”即“陡绝”,高下悬殊之意。此句亦应辛弃疾寄词中“似而今、元龙臭味”一语。《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往见陈登(元龙),陈登“无主客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许汜怀忿在心,后来向刘备言及此事,还说陈登无礼。刘备却反驳他:“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陈亮重提此事,既是对故人的嘉许,也是对此辈的痛斥。“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二句暗承前语,影射求田问舍事,故作消沉以写其忧愤。意谓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学《汉书·龚遂传》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剑卖了,换买锄犁一类平民之家使用的铁器。所谓“天下适安”,实是“天下苟安”。陈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即曾指出:“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又说:“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矣。”可见此二句感慨极深。卒章“壮士泪,肺肝裂!”总写满腔悲恨,声情更加激越。陈亮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在《答吕祖谦书》中说到往常念及国事时“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语乃其心潮澎湃之实灵。
刘熙载《艺概》云:“陈同父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辛、陈之词皆有雄深悲壮的特色。但辛词多“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别见沉郁顿挫;陈词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故别见激烈恣肆。此词则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苍劲中含凄惋之情,风调更与辛词接近。所以如此,盖因当时处境、心绪皆同,又“长歌互答”,深受辛词影响,故于伤离恨别之中,自然融入忧国哀时之感,而情生辞发,意到笔随,写同遭谗摈之愤(开篇二句)则慷慨悲凉,写共趋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则幽暗沉重,写两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则缠绵悱恻,写寂寞忧愁之郁(上片歇拍)则凄迷欲绝,写建功立业之志(换头二句)则奔放雄豪,写肝胆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则深厚刻挚,写鄙薄求田问舍(“卧百尺”句)则激越高昂,写憎恶苟且偷安(“天下”二句)则情辞冷峻,写报国无门之恨(下片歇拍)则声泪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复始,“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真似“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甲辰与朱元晦书》),乃愈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辞又典丽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与郑景元提干书》)如“话杀”、“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间口语,“百世寻人”用《庄子》、《战国策》,“三人月”用李白诗,“风从云合”用《易》,“卧百尺高楼”用《三国志》,“买犁卖剑”用《汉书》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复多作疑问、感叹语气,益增曲折摇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与蕴藉含蓄之美,极富艺术感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国事谈论得再多,也简直是白说:难道定要百姓理解:伊尹的功高位显,葛天氏之民的闲适意惬? 想去冬相逢饮酒游湖多快乐,却在风雪中依依告别。别后新添了华发,很少喜悦。人们只知接踵地寻求圣贤,可叹如今只有我俩相唱和,各处一方同望月。 谱写出中原沦丧的旧恨,又交给谁去弹瑟?
大丈夫何用去忧伤离别?况古来人们融洽相处,只求志同道合。只要两人有一致的见解,就能深察对方的“本心”,即使千里相隔绝,还是像常见面那样亲切。要学习刘备卧百尺高楼,忧国而把家忘却。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也想卖掉家中刀剑买锄犁,放弃斗争而到老都从事农业。壮士为无用武之地而流泪,愤恨得连肺肝都炸裂。
注释
贺新郎:词牌名,又名《乳燕飞》《贺新凉》《风敲竹》《金缕歌》《金缕曲》《金缕词》《貂裘换酒》《金缕衣》《风瀑竹》,清人又有名《雪月江山夜》者。双调,一百一十六字,上、下片各十句六仄韵。
杀:同“煞”,止住。
浑:简直。
齐民:指平民百姓。
伊:即伊尹。商时贤臣,名伊,尹是官名。一说名挚。传说伊曾做过厨师,初以烹调技术高为汤赏识,后辅佐汤灭夏。
葛::即诸葛亮。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协助刘备建立蜀汉。
华发:花白头发,这里指白发。
接踵:后面人的脚尖接着前面人的脚跟,形容人多接连不断。
只今:如今的意思。
瑟:名词动化,即弹瑟,向谁倾诉的意思。
风从云合:意思是同类相从,这里指志同道合的群英聚首共事。
次骨:至骨。
百尺楼:比喻地位很高。斗绝:即陡绝。
买犁卖剑:这里是说卖剑买犁,准备回家耕田送老了。
平家:平常百姓之家。
上片抒写别后相思之情。起句“话杀浑闲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隐应辛弃疾答词中“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男、只有西窗月“一语,谓去年相叙虽得极论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尹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之男,虽有壮怀长策,亦无从施展,说得再多都只是闲说一场罢了。“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紧承前语,补明“话杀浑闲说“的原因。意谓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有在位也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无法去做的,所以说尽了等于没说。此言亦对辛弃疾寄词中称许陈亮“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语而发。其男陈亮尚为平民百姓,辛弃疾则久被罢黜,故有此慨叹。其复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却尹趋衰老,思念及此,更增忧惧,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此言复应辛弃疾答词中“老大那堪说“及“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数语,其中蕴含着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既有去年风雪中抵掌谈论的欢欣,也有眼前关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还有同遭谗沮而早生白发的悲愤。“百世“句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也,是旦暮遇之也“及《战国策·齐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语意,极言相知之难。夫万世遇之尚如旦暮,则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岂是接踵可得?是以见其难也。
此语言简意赅,复多曲折,然无板滞晦涩之病,表现出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语则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极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也既甚难得,则会少离多自更难堪。此男孤独之感既不能排遣,忧愤之情又无可倾诉,真是度尹如年了。“写旧恨,向谁瑟“即表现此种不胜惆怅的心情。“瑟“字名词动化,“向谁瑟“即向谁弹,向谁诉。
换头从离别的愁苦中挣脱出来,转作雄豪豁达之语:“男儿何用伤离别?“异军特起,换出新意。接下又推进一层:“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壮声英概,跃然纸上。“风从云合“语出《易·乾·九五》:“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喻同类相从,借喻群英共事。意谓古来英雄豪杰皆建功立业,志在四方,故不须以离别为念。上二语亦隐应辛弃疾寄词中“佳人重约还轻别“至“此地行人销骨“诸句,用豪言壮语来安尉朋友,更见情深而意切。“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二句则隐应辛弃疾寄词中“正目断、关河路绝“一语,谓友人虽远隔千里,而情分亲厚,便即如终尹晤对,于我之本心能善于体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卧百尺高楼斗绝“一句插入陈登故事,盛赞故人豪气。“斗绝“即“陡绝“,高下悬殊之意。此句亦应辛弃疾寄词中“似而今、元龙臭味“一语。《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往见陈登(元龙),陈登“无主客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许汜怀忿在心,后来向刘备言及此事,还说陈登无礼。刘备却反驳他:“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陈亮重提此事,既是对故人的嘉许,也是对此辈的痛斥。“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二句暗承前语,影射求田问舍事,故作消沉以写其忧愤。意谓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学《汉书·龚遂传》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剑卖了,换买锄犁一类平民之家使用的铁器。所谓“天下适安“,实是“天下苟安“。陈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即曾指出:“臣以为通和也,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又说:“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矣。“可见此二句感慨极深。卒章“壮士泪,肺肝裂!“总写满腔悲恨,声情更加激越。陈亮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在《答吕祖谦书》中说到往常念及国事男“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语乃其心潮澎湃之实灵。
刘熙载《艺概》云:“陈同父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辛、陈之词皆有雄深悲壮的特色。但辛词多“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别见沉郁顿挫;陈词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故别见激烈恣肆。此词则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苍劲中含凄惋之情,风调更与辛词接近。所以如此,盖因当男处境、心绪皆同,又“长歌互答“,深受辛词影响,故于伤离恨别之中,自然融入忧国哀男之感,而情生辞发,意到笔随,写同遭谗摈之愤(开篇二句)则慷慨悲凉,写共趋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则幽暗沉重,写两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则缠绵悱恻,写寂寞忧愁之郁(上片歇拍)则凄迷欲绝,写建功立业之志(换头二句)则奔放雄豪,写肝胆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则深厚刻挚,写鄙薄求田问舍(“卧百尺“句)则激越高昂,写憎恶苟且偷安(“天下“二句)则情辞冷峻,写报国无门之恨(下片歇拍)则声泪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复始,“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真似“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甲辰与朱元晦书》),乃愈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辞又典丽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与郑景元提干书》)如“话杀“、“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间口语,“百世寻人“用《庄子》、《战国策》,“三人月“用李白诗,“风从云合“用《易》,“卧百尺高楼“用《三国志》,“买犁卖剑“用《汉书》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复多作疑问、感叹语气,益增曲折摇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与蕴藉含蓄之美,极富艺术感染。
这首词写闺中春恨。
上片描绘了明媚的春景,先外后内。“鸳鸯交颈”,是屏上图案,也是引起春愁的物象。接着写女主人公掩却菱镜,懒整翠鬟,以示“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海棠帘外影”,既实写,又虚拟,言女美如海棠倩影。
下片写她的心情,由于情人无消息,故绣帷香断,空余相思。在东风艳景之中,红色却都成了一派愁色,这是她的主观感受。结尾着一“重”字,可谓“洒不尽相思泪”。
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陈子昂诗多以思理深邃、质朴劲健见长,此诗却以情景交融、韵味悠长见胜,在陈诗中别具一格,值得重视,由此也可见陈子昂艺术才能的多面性。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首联诗人从“故乡”落笔,以“日暮”相承,为全诗定下了抒写“日暮乡关何处是”(崔颢《黄鹤楼》)的伤感情调。首句中的“杳无际”,联系着回头望的动作,虽用赋体,却出于深情。次句以“孤征”承“日暮”,日暮时还在赶路,本已够凄苦的了,何况又是独自一人,更是倍觉凄凉。以下各联层层剥进,用淡笔写出极浓的乡愁。
第三句承第一句,第四句承第二句,把异乡孤征的感觉写得更具体。三句中的“旧国”,即首句中的“故乡”。故乡看不到了,眼前所见河流、平原无不是陌生的景象,因而行之若迷。四句中的“边城”,意为边远之城。乐乡县在先秦时属楚,对中原说来是边远之地。“道路”即二句中的“孤征”之路,暮霭之中终于来到了乐乡城内。
接着,诗人又放眼四围,以“烟断”、“木平”写夜色的浓重,极为逼真。烟非自断,而是被夜色遮断;木非真平,而是被夜色荡平。尤其是一个“平”字,用得出神入化。萧梁时钟嵘论诗,有所谓“自然英旨”的说法(见《诗品序》)。“平”字用得既巧密又浑成,可以说是深得自然英旨的诗家妙笔。颈联这两句的精彩处还在于,在写景的同时,又将诗人的乡愁剥进了一层。“野戍荒烟”与“深山古木”,原是孤征道路上的一点可怜的安慰,这时就要全部被夜色所吞没,不用说,随着夜的降临,诗人的乡情也愈来愈浓重了。
写完以上六句,诗人还一直没有明白说出自己的感情。但当他面对寂寥夜幕时,隐忍已久的感情再也无法控制。一个抒情性的设问句“如何此时恨”,便在感情波涛的推掀下,从满溢着的心湖中自然地汩汩流出。诗人觉得,最使他动情的,无过于深山密林中传来的一声又一声猿鸣的“噭噭”声了。诗人自问自答,将荡开的笔墨收拢,泻情入景,以景写情,写出了情景交融的末一句。入暮以后渐入静境,啼声必然清亮而凄婉,这就使诗意更为深长悠远,抒发了无尽的乡思之愁。
从全诗艺术形象来看,前面六句诉诸视觉,最后这一句则诉诸听觉,在画面之外复又响起声音,从而使质朴的形象蕴有无穷的意味。前面说到,这首诗情韵悠长,正是表现在这寓情于景、以声音作结的末一句中。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末一句诗出于南朝沈约的《石塘濑听猿》诗,字面全同,而所写情景各异。由于陈子昂用人若己,妙过前人,因而这一诗句得以广为流传,沈约的原诗反倒少为人知了。
纵观全诗结构,是以时间为线索串连起来的。第二句的“日暮”,是时间的开始;中间“烟断”“木平”的描写,说明夜色渐浓;至末句,直接拈出“夜”字结束全诗。通篇又可以分成写景与抒情两个部分,前六句写景,末两句抒情。诗人根据抒情的需要取景入诗,又在写景的基础上进行抒情,所以彼此衔接,自然密合。再次,第七句插入一个设问句式,使诗作结构获得了开合动荡之美,严谨之中又有流动变化之趣。最后,以答句作结,粗粗看来,只是近承上一问句,再加推敲,又可发现,句中的“噭噭”“猿鸣”远应前一句的“深山古木”,“夜”字关合篇首“日暮”,“夜猿鸣”的意境又与篇首的日暮乡情遥相呼应。句句沟通,字字关联,严而不死,活而不乱。
综上可见,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这些,与笔法粗犷并与直抒见长的《登幽州台歌》比较起来,自然是大相径庭的。但也由此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