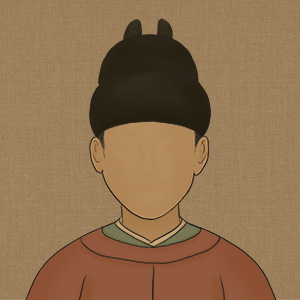这首诗的情调酷似《诗经》中的“国风”,重在叙述行军艰难而紧张,并没有《毛诗序》所说“役久”的意思。全诗三章,以赋叙事抒情,头两章叠唱,意思相仿,诗人在急行军途中,迎面映入眼的是陡崖峭壁,挡住队伍的去路,忍不住惊呼道“维其高矣”、“维其卒矣”。头两句写所见,中间两句写所感,叹惋山川遥远,跋涉攀援,步步维艰,疲劳不堪,十分盼望抵达目的地。然而“山川悠远”,不知道何日才能走到。最后两句点题,交代急行军。“武人东征”一句贯穿全诗,三章都有,点明抒情主体与事件。首章“不皇朝矣”句,说明行军紧急,起早摸黑,天不亮就上路。第二段“不皇出矣”句蕴藏着更多难言的痛苦,行军紧迫,不断深入,无暇顾及以后能否脱险。也就是说至此生命已全置之度外。
第三章诗人笔锋一转,突然伸向天空,描写星空气象,与首章“朝矣”句相应,暗示是夜晚行军。朱熹说前四句“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诗集传》)。这可能是诗人引用已有的气象民谚。近人闻一多指出:“豕涉波与月离毕并举,似涉波之豕亦属天象,《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御览》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狶,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吻合,是其证验。《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所言亦极相似,是《诗》所谓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周易义证类纂》)依闻一多的说法,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星即指毕星。应劭《风俗通义》说:“雨师者,毕星也。”其下即引用此诗“月离”两句为证。《晋书·天文志》也说“月行入毕多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俾”字点明尚未发生,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姚炳的说法“将雨、既雨,诸说纷如”,实际上诗中原本是说“将雨”,而不是“既雨”,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正因为诗人担心遭遇滂沱大雨,行军难上加难,一心一意只想加速行进,无暇顾及其他,所以才说“不皇他矣”。三个段落的末句意思递进,旅途的苦情、忧虑一层深过一层。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毛文锡擅写闺情,词语艳丽,这首词是一首艺术性较高的闺思之作。
闺中少妇,思念远别的亲人,通宵不寐,直待天明。以其爱之甚切,故恨之亦切;以其思之甚深,故怨之亦深。这一怀思绪,主要通过环境气氛的描写来烘托和表现。
词中的景物,不仅是作为春天一般景物用以渲染春天的气氛,同时还作为一种意象,借以表达离情别绪和春思春愁。
“花外子规啼月”,思妇在静夜里听到鸟声,本来就容易勾起孤寂之感。以鸟声烘托岑寂,是以动写静。而这鸟声又是子规的啼叫声,便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子规的叫声近似“不如归去”。杜牧诗云:“蜀客春城闻蜀鸟,思归声引未归心。”这首词里所写花外子规,也具有思归的意象,但不是用以表示游子思归,而是用以表现思妇切盼情人归来。
“红纱一点月”,思妇独守空闺,孤寂之中,对着红纱笼罩的的孤月凝思,此景此情,都带点凄凉之感。“孤月”在这里是烘托思妇孤寂的一种意象。思妇夜里思念情人,不能入寐,梦也难成,空对着一点寒月。在寒月的映照下,益显出思妇心情的孤寂。
“庭下丁香千结”,写室外之景。丁香结蕾,唐宋诗人多用一比喻愁思固结不解。如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这首词描写庭下丁香花蕾千结,同样暗寓思妇愁肠千结,表现了思妇的离愁和春愁。
“梁间双燕飞”,双燕飞于梁间,最容易引起思妇的春思和春愁。本来成双成对的燕子绕梁而飞,是一种很和谐的景物,可以唤起欢愉的情绪,然而当对着这景物的主人公心境十分孤寂的时候,这一和谐景物与孤寂的心境恰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当词中的思妇彻夜不眠,送走宵雾,迎来晓霞,看到双燕在晨曦中绕梁而飞的时候,不是解除了夜间相思之苦,而是更增添了一种孤寂之感,更无法排遣心中的春情和春思、春愁和春恨。
词中子规、纱月、丁香、双燕这四种景象,是实景,又不是单纯的实景,可以说是“实中有虚”,也就是说既具体又抽象,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引发愁情的触媒,甚至称了这无形无质的情思的表象。这首词对于这些意象的运用是很成功的。
韩偓用七律写过不少感时的篇章,大多直叙其事而结合述怀。这首诗却凭借想象中的景物描写来暗示政局的变化,情景交融,虚实相成,在作者的感时诗中别具一格。
诗篇开首即从朝廷搬迁后长安城的荒凉破败景象落笔。“草萋萋”,虽只寥寥三个字,却点明了物态人事的巨大变化。往昔繁荣热闹的都城,而此时满是废台荒草,叫人触目惊心。长安城的衰败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先兆,诗人对此怀有极深的感慨。这里虽没明说,但领头的“遥想”一语,倾注着无限眷恋关注之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下句是说连高居天宫的天帝见此情景也会深感迷惑,这固然是为了突出都城景物变异之大,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内心的迷惘不安。整首诗一上来就笼罩了一层凄迷悲凉的气氛。
次联承接首句,进一步展开故都冷落的画面。池籞,平时上面网以绳索,禽鸟无法进出。塞外飞来的大雁已侵入池籞住宿,这就意味着宫殿残破,无人管理;而园中乌鸦犹自傍着女墙哑哑啼鸣,更给人以物情依旧、人事全非的强烈印象。前联总写长安城的衰败,取景浑融概括;此联集中描绘宫苑废芜,笔触细致传神。这样将全景与特写剪接在一起,点面结合,深切地反映了作者想象中的故都近貌。
第三联开始,转入正面抒情。烈士,是诗人自称。当时诗人尽管流寓在外,心仍萦注国事,面临朝政的巨大变故,痛感自身无能为力,其衷怀的悲愤可想而知。“垂涕”而又加上一个“空”字,就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真切。下句的“地下强魂”,指昭宗时宰相崔胤。他为铲除宦官势力,引进朱温的兵力,结果使唐王朝陷入朱温掌握之中,自己也遭杀戮。此句是说崔胤泉下有知,定将悔恨莫及。韩偓与崔胤原来关系密切,这里插叙崔胤被害的事实,是为了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整个这一联抒情激切,笔力劲拔,接续前面的寥落景象,犹如奇峰突起,巨波掀澜,读来气势一振。
尾联归结于深沉的感喟。“掩鼻计成”,用的是《韩非子》里的故事,这里借指朱温伪装效忠唐室,用阴谋夺取天下。末句诗人以冯驩自况,慨叹自己没有像孟尝君的门客那样设计解救君主脱离困境的办法。这一联用典较多,但用而能化,不嫌堆砌。叙述中,像“终不觉”、“无路”等字眼下得沉重,蕴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引证古事而能具有活生生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
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前半凄惋,后半激越,哀感沉绵之中自有一股抑塞不平之气,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前人常说,韩偓的感时诗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沉郁顿挫,律对精切,这是不错的。但韩偓尤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融入芊丽清新的词章里,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又有他个人的特色。此篇似亦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