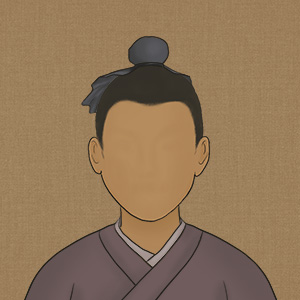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
这首诗一共六句,分三层,抒发离家求仕的复杂感情。情与景相间相融,夹以议论。反映汉末一代有抱负青年在乱世中创业,为实现统一安定的能施展才智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虽为知己者死,但死而无怨。这是时代精神的艺术个性化。时代的共性深寓在艺术个性之中,隐现着个性美与人情美的质愫与基因。
诗的开端两句直接入题,写别时景象,暗扣诗题离别后的感伤。“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这两句是触景生情,目及早晨朝霞涌起,由此自然现象,想到浮云升起,飘浮天上,可是到了晚上还是要回到故山,有自己归宿之处。暗示出自己离家外出,如天上浮云一样,飘泊海内。晚年能否落叶归根,重回故土,前途茫然,不可知。比拟象征,含蕴深厚,不言别情,而情在其中。未上路,而先想归乡,可见对故乡、亲人、知己的感情之深。这就为下面的行役悲思作了铺垫。
诗的三四两句,叙述别后之悲思。“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这两句是化用古诗 “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句意。暗示悲伤到了极点,只有呜咽吞泣而已。平平地叙事,感情却起了波澜,点出行役之苦,思乡之痛,苦痛交加,自难承受,而产生了悲伤气结不能言的行为。把感情发展到了高潮。仿佛诗意尽于此,把人引入情海之中,玩味、品尝,经历这感情的痛苦历程,这就是诗家所说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
诗的五六两句绝处逢生,宕开一笔,转写未来。“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前途渺茫,心情暗淡,预兆着有故乡不得归的惨极心境。诗至此戛然而止,照应开端,浮云日暮有归宿,而自己的人生归宿,却难以预料,相映相衬,令人生悲。
《卿云歌》,相传是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始见旧题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据《大传》记载:舜在位第十四年,行祭礼,钟石笙筦变声。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帝沉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见于钟石!”即荐禹使行天子事,并与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云云。钟石变声,暗示虞舜逊让;卿云呈祥,明兆夏禹受禅。这一传说故事,充满了奇异神话色彩,《卿云歌》的主题,则反映了先民向往的政治理想。 全诗三章,由舜帝首唱、八伯相和、舜帝续歌三部分构成。君臣互唱,情绪热烈,气象高浑,文采风流,辉映千古。
首章是舜帝对“卿云”直接的赞美歌唱。关于“卿云”之名,《史记·天官书》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在古人看来,卿云即是祥瑞之喜的象征。“卿云烂兮,糺缦缦兮”,若云若烟,卿云灿烂,萦回缭绕,瑞气呈祥;这祥瑞之兆,预示着又一位圣贤将顺天承运受禅即位。“旦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更明显寓有明明相代的禅代之旨。圣人的光辉如同旦月。他的受禅即位,大地仍会像过去一样阳光普照、万里光明。这与其说是舜帝的歌唱,毋宁说是万民的心声和愿望。
次章是“八伯”的和歌。八伯者,畿外八州的首领。这里当指舜帝周围的群臣百官。舜帝首唱“卿云”,八伯稽首相和:“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旦月光华,弘于一人!”他们进而赞美上天的英明洞察,把执掌万民的大任,再次赋予一位至圣贤人。这里对“明明上天”的赞美,也是对尧舜美德的歌颂。《尚书·尧典》有云:“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而今者虞舜,效法先圣,荐禹于天,以为后嗣。没有尧舜的美德,就没有禅让的美谈。尧舜之举比起明明上天,更值得称颂。
舜帝的赓歌,则表达了一位圣贤的崇高境界和伟大胸怀。十二句可分三层。前四句以“旦月有常,星辰有行”作比,说明人间的让贤同宇宙的运行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使国家昌盛,万民幸福。中四句叙述“迁于贤圣”的举动,既顺从天意也符合民心。可谓普天之下,莫不欢欣。最后四句表现了虞舜功成身退的无私胸怀:“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正当人们击鼓鸣钟、载歌载舞,欢呼庆贺夏禹即位之时,自感“精华已竭”的虞舜,却毫无声息地泰然“褰裳去之”。只此两句,一位崇高伟大的圣贤形象,便跃然纸上。
尧、舜禅让,载于《尚书》,《卿云》之歌,流传秦季。而尧、舜均属传说人物,舜歌《卿云》,颇难征信。很可能这是身处战国、秦季乱世,目睹争夺劫杀,而向往礼让治世者的代拟之作。不过,自战国、秦汉以来,禅让传说和《卿云》之歌,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对形成以礼让为美德的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诒徵论“唐虞之让国”时写道:“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亡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中国文化史》)。这对认识《卿云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颇有启发。
在艺术上,《卿云歌》辞藻华美,意境超迈,孕育骚赋句法,足可与《诗》之《雅》、《颂》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