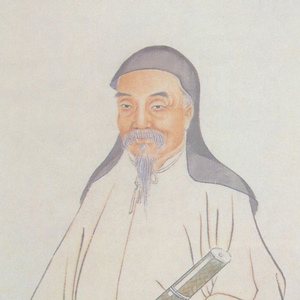首两句是诗人心中发出的感喟,一种深情的阻隔,即使近在咫尺,也形同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先引用两个典故来喻意,一是用嫦娥偷灵药得仙人月,来喻宋氏姊妹已飞升成仙,一是用东方朔三次偷王母蟠桃事来喻诗人自己,作者说:但仙、凡两境界,“事难兼”啊,今夜我只能望着高楼,“彩蟾”被锁在深阁,城关重重,哪能相见呢?这两句中“兼”与“锁”两词写出了人间种种阻隔,心愿与现实总是相违,在情爱生活中同样如此,对诗人而言,人间无形阻难感受更深了。
后两句点出“月夜”,诗人此时此景的想像与感受应是如此的:在这明月皎洁,月光如银,安详宁静的夜晚是多么好的时光啊,如果我们三人相聚于山水亭角之间,开怀言志,情感交触,共赏明月,然而这仅是一种梦幻和想象了,抬头一望,我只能出神地仰视一下你们高楼上悬挂的水精帘了。这时抒情主人公的心情只能是诗人在绝句《嫦娥》诗中写的两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了。
此诗后两句在构思上有一个特色,即“应”与“未”对举,“正”与“反”相合,这更加浓了情深意厚,美事难成的寓意。句中“共”与“仍”也是相反相承的,“共”是美好的意愿,而“仍”却蕴藏了生活中多少阻碍与不测。看来李商隐是深于情感的,但是否能冲过对于功名之企求,恐怕也只是“玉楼仍是水精帘”了,做人的难度也就在这里。
上片写歌妓的美艳照人。起句“玉肌琼艳新妆饰”直接从正面描写她肌肤白嫩娇美,光洁如玉,而又装扮一新。“好壮观歌席”,是说每当她出现在酒宴歌席之上,人们都会觉得眼前一亮,酒宴歌席也会因她的到来而增色不少。这句从侧面写她的美。把“好壮观歌席”口语化,宜于观听,朗朗上口。以下,词人全用虚笔,以“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极赞她的美丽和高贵。
下片写这位歌妓格调俊雅。在柳永的笔下,这位歌妓不但容貌姣好,气质高贵,而且颇有才情。她“属和新词多俊格”,竟能与别人以诗词相唱和,且作品格调高迈过人,“敢共我勍敌”。要知道,词人向来以“平生自负,风流才俊”(《传花枝》)自诩,作诗填词能与他一争高下,这位歌妓的才情可以想见。所以词作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
这首小词妙处亦在结末:疏狂少年敢与我这个老浪子竞争,恐怕他们还嫩了点,谁叫他们不早与你结识呢 ! 这话是对那“玉肌琼艳”说的,事实上也是对疏狂少年的不屑,活脱脱一个过了中年.痴心不改,以风流浪子自许的词客形象。宋代的歌妓地位卑微,受到严格管束,常受折磨,柳永此词虽以歌妓为描写对象,但绝无丝毫淫靡的情调,柳永笔下的歌妓也绝无一点风尘气。他把歌妓当作平常人对待,他所欣赏的不仅仅是歌妓的体态和容貌,而更多的是她的才华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