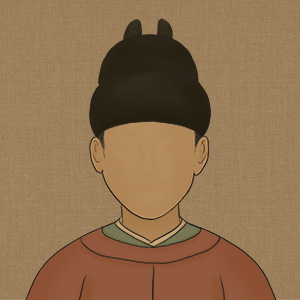足堪娱寿母,幸不乏先畴。
酒具饶鱼蟹,郊居少应酬。
两无惭事育,何用到壶头。
足堪娱寿母,幸不乏先畴。
酒具饶鱼蟹,郊居少应酬。
两无惭事育,何用到壶头。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这是一首单调小令。开头五句,奏的是感情音响的主旋律——怨。“永夜”两句,就悬想负心人行踪着笔。“长夜漫漫,负心人啊,你抛下我到哪里去了?”自问还复自答:“音信已绝,奈何!”着一“绝”字,点出薄悻者之寡信绝情。“香阁掩”三句,就闺中人己方情况着笔,从环境描写(闺门紧闭)、表情描写(眉头紧皱)、时间推移(斜月将落、长夜将尽)这三个方面,写出了终宵坐候之难耐。这两笔归结到一点——对薄悻者之怨。
“争忍”句以下写心池又起新澜。“争忍”两句是第一个浪头,特点是思之不已,爱怨兼发。“叫我怎忍心不苦苦追寻啊?”这一句心灵独白,表明她怨中有爱,情丝难解。但稍加推究,闺门紧闭,室内一目了然,无物可寻。“寻”这一动作,正好显示她已陷于身难自主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等到她头脑稍为清醒,又得面对令人心碎的现实——孤衾独处,因而“怨”字又重上心头。“换我心”三句是第二个浪头,特点是情之所钟,忽发痴语。清王士禛《花草蒙拾》曾指出:“顾太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自是透骨情语。徐山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袭此。”徐山民句中之“移”字,倒也深得顾词“换”字之真谛。换心者,移心之谓也。主人公是多么希望把自己的一颗心移置在对方的心腔里,以取得对方对自己思念之深的理解啊。就事论事,移心之说似属无理,而主人公发此痴想,却正好显示其爱之深,其情之真,此即所谓“无理而有情”。当然尽管如此,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将是难以避免的。这一点,明汤显祖在《花间集》评本中曾一语道破:“若到换心田地,换与他也未必好。”但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却十分明朗,同情完全放在被折磨被损害的弱女子这一边,这也就从侧面鞭挞了薄悻之徒。
顾夐此词,以善作情语著称。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把此词作为“有专作情语而绝妙者”的显例之一,并且说:“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足见评价之高。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