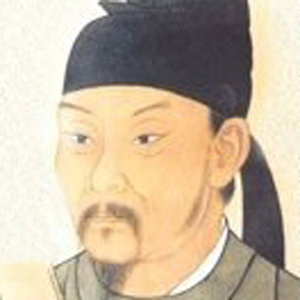石涧探幽步,风泉得句心。
黄猿知日暝,青树觉春深。
又向南峰住,时时许我寻。
石涧探幽步,风泉得句心。
黄猿知日暝,青树觉春深。
又向南峰住,时时许我寻。
这是一首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一两句描绘宫廷中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汉代未央宫有披香殿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歌舞过的地方。唐代庆善宫中也有披香殿,“新殿”或取义于此。但此处主要是借这个色彩香艳而又容易唤起历史联想的殿名来渲染宫廷歌舞特有的气氛。对于披香殿前的歌舞,诗人并未作多少具体的铺叙,而是着重描绘了“珠箔轻明拂玉墀”的景象。珠箔即珠帘;玉墀指宫殿前台阶上的白石地面。轻巧透明的珠帘轻轻地拂着洁白的玉墀,这景象在华美中透出轻柔流动的意致,特别适合于表现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使人感到它和那些“斗腰支”的宫妓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斗腰支”三字,简洁传神,不仅刻画出宫妓翩跹起舞的柔媚之态,而且传出她们竞媚斗妍、邀宠取悦的心理状态。同时,它还和下两句中的“鱼龙戏”、“偃师”,在竞奇斗巧这一点上构成意念上的关联。不妨说,它是贯通前后幅,暗示全诗主旨的一个诗眼。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三、四两句突转,集中托讽寓慨。“鱼龙戏”,本指古代百戏中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进行种种奇幻的表演。《汉书·西域传赞》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可见这是一种变幻莫测、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不过,从题目“宫妓”着眼,这里的“鱼龙戏”恐非实指作为杂技百戏的鱼龙之戏,而是借喻宫妓新颖变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师”用了《列子·汤问》的一则故事;传说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能工巧匠。偃师献上一个会歌舞表演的“假倡”(实际上是古代的机器人),“钡(抑)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以为是真人,和宠姬盛姬一起观赏它的表演。歌舞快结束时,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气,要杀偃师,吓得偃师立即剖解假倡,露出革木胶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终于免祸。三、四两句是说,等不到看完宫妓们那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君王就要对善于机巧的“偃师”怒气冲冲。
原故事中的偃师是一个善弄机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点因为弄巧而送命。这种机关算尽、反自招祸患的现象具有典型意义。诗人用偃师故事,着眼点正在于此。诗中的宫妓和“偃师”的关系,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和偃师的关系;而诗中所描绘的“斗腰支”、“鱼龙戏”,又正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师的机巧。那么,透过“不须”、“终遣”这两个含意比较明显的词语,可以看出,诗中所强调的正是善弄机巧的偃师到头来终不免触怒君王,自取其祸。如果把这首诗和《梦泽》、《宫辞》等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联系起来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和“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之间有着十分神似的弦外之音。宫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而迎合邀宠、红粉自埋的宫女,一时得宠、不管将来的嫔妃,和玩弄机巧、终自召祸的偃师,则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产物。在诗人看来,他们统统是好景不常的。
《云中君》一篇按韵可分为两章,每一章都是对唱。开头四句先是祭巫唱,说她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花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灵子翩翩起舞,神灵尚英离去,身上隐隐放出神光。这是表现祭祀的虔诚和祭祀场面的。
“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句为云中君(充作云中君的灵子)所唱,表现出神的尊贵、排场与威严。由于群巫迎神、礼神、颂神,神乃安乐畅意、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六字,准确地道出了云的特征;就天空中而言,能同日月并列的唯有星和云,但星是在晴朗而没有日光时方能看见,如同时也没有月亮,则更见其明亮。惟云,是借日光而生辉,云团映日,放出银光,早晚霞光,散而成绮,所以说“与日月兮齐光”。这两句,上句是说明“神”的身份,下一句更表明“云神”的身份。“龙驾兮帝服”,是说出行至人间受享。“聊翱游兮周章”则表示不负人们祈祷祭祀之意,愿为了解下情。古人以为雨是云下的,云师有下雨的职责。“屏”是遮蔽的意思。“翳”,《离骚》王逸注:“蔽也。”《广雅·释诂二》:“障也。”则“屏翳”之名实表示了同“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一样的意思。周宣王祈雨之诗名曰《云汉》,贾谊悯旱之赋题曰《旱云》,俱可以看出古人对云和云神的看法。
祭巫唱“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乃是说祭享结束之后云中君远离而去。“皇皇”是神附在巫身上的标志。神灵降临结束之后,则如狂飙一般上升而去。这里是表现云神的威严与不凡。“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则是云神升到高空后因眼底所见而言,表现了云高覆九州、广被四海的特征。末尾二句,是祭巫表示对神灵离去的惆怅与思念,表现出对云神的依赖情绪。祭云神是为了下雨,希望云行雨施,风调雨顺。
《云中君》祭歌共十四句,在《九歌》中除去《礼魂》一首外,它算是最短的了。这十句的艺术特点归纳起来有三项:一是从云中君本身构画出云的神秘气氛;二是从云中君的审美咏叹中透露出对神的礼赞;三是从云的晕彩卷舒的阴柔美,翻入云的磅礴飞扬的阳刚美。这中间十句一共只用了五十九个字,就做得这么巧密贴切,天衣无缝。如果配合舞蹈,表演起来,将是令人俯仰周旋不能自已的。
这中间十句的前六句,写的是停云状态,因为只有停云才能返照出日月的晕彩,这正是云中君的神性所在。其中“烂昭昭兮英央”一句以后,隔了一句,又配上“与日月兮齐光”一句遥相呼应。这“烂昭昭”和“与日月”是写其光彩,这“英央”与“齐光”,则着重写其永恒,让人自去联想这是在寿宫里对神的永恒的礼赞。但又暗示着人们内心里对长寿的祝祈,两者掩映得非常巧妙。
然后再接上“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两句,使云中君这位“灵”的神彩在云光晕影的礼赞中,呈现出来,又以其俯仰周旋雍容华贵的气象,跟流云的神态配合得完全一致。这中间十句中的前六句,把舒卷的云、彩晕的云、旋动的云都写到点子上了,然后接下去四句重写云中君带着煌煌的光焰归去。它虽藉云的飞扬而飚举,但它之横览大地.却仍然像云那么纷披迷漫于天空,从而显示出云中君的俊爽雄伟,广大高超。这前六句以云写云中君,后四句又以云中君写云,都组织得工细熨贴。这是符合民间巫祠既要将神形象化,又要将神灵异化的要求的。如果说这前六句写停云,用的是细致刻划的手法;这后四句写飞云却用的是晕染逸彩的笔调,令人读之觉得有一股磅礴飞扬的气势,挟人腾空飞去,另有一番美的感受。
至于这首祭歌前后各两句分写女巫,这女巫本是云中君的陪体,在祭歌里也只能作为衬笔了。开篇两句写女巫之华丽芬芳,正所以引出云中君的光彩灿烂。收篇两句写女巫之柔情缱绻,亦只为衬托出云中君的飘逸俊伟,在飞扬的气势后面,缀上一点缠绵的情韵.就足以留下一丝悠然不尽的回味。文中这“夫君”一唤,就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至于她是神妻,她能够传达神谕,这都无关诗歌情韵,自然歌辞里是无须说,也不用说的了。
此词是一首离情词。当是托为妓女送别情之作。送者有意,而别者无情,从送者的角度来写,写尽其痴人痴情。
“留人不住”四个字将送者、行者双方不同的情态描绘了出来:一个是再三挽留,一个是去意已决,毫无留恋之情。“醉解兰舟去”,恋人喝醉了,一解开船缆就决绝地走了。“留”而“不住”,又为末两句的怨语做了铺垫。
“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二句紧承“醉解兰舟去”,写的是春晨江景,也是女子揣想情人一路上所经的风光。江中是碧绿的春水,江上有婉转的莺歌,是那样的宜人。当然,景色的美好只是女子的想象,或许更是她的期望,即使他决然地离开了她,她也仍旧希望自己的情人在路上有美景相伴,可见痴情至深。“过尽”两个字,暗示女子与恋人天各一方的事实,含蓄透露出她的忧伤。
“碧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情人已经走了很久,不见踪影,但女子依旧站在那里。堤边杨柳青青,枝叶茂盛繁多,千丝万缕,依依有情,它们与女子一起伫立于碧口,安静凝望远方。古人有折柳枝送别的习俗,所以“枝枝叶叶”含有离情的意思,此处即借杨柳的枝叶来暗示女子黯然的离情。
“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所表达的感情非常激烈。女子负气道:“以后你不必给我寄信了,反正我们之间那犹如一场春梦的欢会没有留下任何凭证,你的心里也没有我的位置。” “画楼云雨”四个字道出了女子与男子曾经的美好过往,只可惜男子决然绝情。相守的期盼落空之后,她只有怀着无限的怨恨选择放弃,从特意提及“锦书”可知,女子内心并不想如此决绝,只是无可奈何罢了。
这首词在技巧上运用了很多对比方法:一个苦苦挽留,一个“醉解兰舟”;一个“一棹碧涛”、晓莺轻啼,一个独立津碧、满怀离情;一个意浅,一个情深,让人一目了然。在结构上,亦是先含情脉脉,后决绝断念。结尾二句虽似负气怨恨,但正因为爱得执著,才会有如此烦恼,所以更能反衬出词人的一片痴情。总之,此词刻画细腻,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一个女子痴中含怨的微妙心理。
首联为工整的流水对,概述了伪教育部电文的内容,点明形势,为下文的驳斥张本。颔联也是一组对偶句,从统治者方面批驳所谓“中坚分子”的荒谬。颈联直接引出电文原文,从学生方面据理反诘,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派的污陷栽脏。尾联将玉佛与学生对比,活现出他们“仓皇古董迁”的卑鄙可耻的本质。篇末点题,击中要害。由此可见,本诗有如春笋揭壳,层层递进,首设全躯,结显原形。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本诗突出的特点。诗的标题就揭示了主旨——学生和玉佛,二者命运截然不同。玉佛可以卖钱,即使“仓皇”逃命,也不忘“迁”走,学生抗日,反被血口喷诬。官样文章说,“面子靠中坚”,究其实,却是“不值一文钱”,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全诗语言平实浅显,作者在诗中表现的讽刺辛辣、深刻,巧妙地将一些平时的报章杂志新闻中的用语都搬入此诗,愈显得讽刺的力量,如“中坚”、“惊扰”、“讵容”、“妄”等。同时,通过学生和玉佛的命运的对比,更显出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利欲熏心。而学生和玉佛的命运,只是当时国乱时危的动荡中国的一个缩影,具典型性,活画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统治者对人民的生命的视如草芥的行径。
此诗犹如一篇驳论性的文艺杂文。作者善于从反面材料中提炼出若干要点,逐一加以批驳。画龙点睛,要言不繁,抓住本质,镜无遁形。幽默和诙谐,渗透在字里行间,笔锋所至,入木三分。
兰花没有牡丹、海棠的妖冶富丽,也没有寒梅、霜菊的傲峭冷艳。它清秀雅洁,芳香馥郁,如淑女婷婷,似君子彬彬,别有一种幽淡孤清的风韵。历来富贵者爱牡丹,隐逸者爱菊梅,而清雅孤高、弱而不阿的文士就偏爱幽兰了。
崔涂这首诗通过咏写兰的贞芳幽独,寄托自己孤高而又哀伤的抑郁情怀,在咏兰诗中是偏于感伤的一类。诗篇兴寄鲜明,旨在抒情,所以诗人对兰不作描绘,而是集中笔墨,诉说兰花自持芬芳却遭风雨侵凌又被弃如路草的悲惨命运,以自伤不遇。诗篇写得质实、深婉,恰如一株飘零的幽兰,质而芳,柔而韧,顾盼自哀,低回不已。
诗人代兰自诉,娓娓说道。开篇先自剖高洁:“幽植众能知,芬芳只暗持。”幽兰常常生于山野、谷畔,但不因清寒而不开,不因无人而不芳。这两句写兰的芳质,又突出了兰幽植孤生,芬芳不被人识的客观处境。宋刘克庄咏兰诗中写它“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意与此相近。但“幽植”二句除自剖之外,还暗责世俗不识芳洁,一笔两开,诗意半含半露,奠定了全篇顾盼、低回的韵调。
“自无君子佩”承首句,“未是国香衰”承次句。兰被推为“花草四雅”之首,有“花中君子”的美称,又因其幽香浓郁,有国香之誉。我国古人常以佩兰表示芳洁,屈赋中有“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唐太宗李世民有《芳兰》诗:“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与此相关,古来也把贤人遭弃比作芳兰无人采折。屈原内美而好修,却反遭斥逐,他慨叹“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为统治者所不容的李白也发出“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秋兰》)的悲慨。秉性耿介,后被罢相的张九龄也咏兰为寄:“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悲秋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这些诗或发抒不平,或自赏孤花,但都掩盖不住遭受冷遇的孤寂。而崔涂这两句,从主体客体两面着笔:兰花芳节香质不稍减,可君子却置之不顾。这是期待后的失望,内省后的自伤,更充满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
“白露霑长早,青春每到迟。”因生于山林,寒露早至,使之先期零落;春光晚顾,又晚得佳期。这一迟一早,写出境遇之惨凄,显出芳魂玉质难得久持的无限悲苦,作吞吐哽咽之声。
诗篇已三层递进,愈转愈悲,但诗人仍情不能已。由于以上种种遭遇,兰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产生了疑虑:“不知当路草,芳馥欲何为?”芳质高格,无人赏识,被弃掷路侧,形同荒草,那么自己独抱贞节,自开自芳,又有何用?步步退逼,终归于凄绝,把不遇之情,推至顶点。至此诗篇的抒情形象完成了。我们好象看到了一株生于草野当风离披的芳兰,又似看到了一个落拓不偶,抑郁难伸的贤士。
此诗运用传统的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由于作者对兰的禀赋特征体察入微,自己的思想情调又与之相契,物性与人情,各自昭然,又妙合如一。诗中所言皆为兰,又无一不是作者的自道。王士祯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这正可用以评价此篇。
作为借物抒情的作品,它体物幽微表现细腻。诗情如一根不绝的丝缕,柔细绵长,欲断又续。既写出幽兰几遭侵凌,生机欲断,却期待不已、春心不死的柔韧之质;又表现了作者虽郁塞难伸,却执着人生追求不舍的深挚沉郁、无限凄苦之情,哀婉幽怨缠绵不尽。
此诗表现细腻,感情深微,诗境却并不狭小,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很高的典型意义。这不能不归之于作者对诗意的提炼和表达的灵活、准确。诗篇不仅咏物抒情相融相映,一笔两到,在具体表达中,用笔又始终是一语双关,言己言他,叹恨如一。使人一面感到幽兰的悲诉、哀凄,一面又感到世人的冷漠、霜露之无情,在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现实的严酷,使人不禁想起李商隐《咏蝉》的名句:“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在哀伤的感情中,又含有几分冷峻。这样,诗篇在自叹自伤之外,深刻地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这首取材平常的咏物诗表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