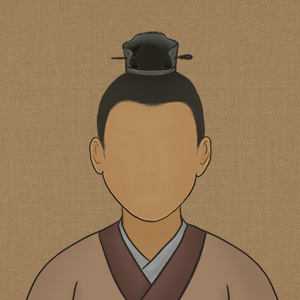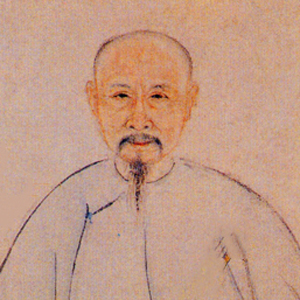寂寞东篱人不到。只有渊明醉倒。一笑留残照。世间万事蝇头小。
寂寞东篱人不到。只有渊明醉倒。一笑留残照。世间万事蝇头小。
全诗围绕着题目的“寻”字,逐渐展开。“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开始二句就突出一个“寻”字来,顺着莓苔履痕(一作“屐痕”),一路寻来。语言浅淡质朴,似乎无须赘言:那人迹罕至的清幽山径,正是常道士出入往来之地,这里没有人间喧嚣,满路莓苔。履痕屐齿给来访者带来希望和猜想:幽人不远,晤面在即;否则就是其人出晤,相会须费些周折。
颔联写由顺其路而始入其居境。两句写景平列,用意侧重“闭门”寻人不遇。“白云依静渚”,为远望。
白云絮絮,缭绕小渚。“依”字有意趣。越溪(或是缘溪)而至其巖扉,近云则“春草闭闲门”,蓬门长闭,碧草当门,道士不在寓所。如果说一路莓苔给人幽静的印象,那么这里的白云、芳草、静渚、闲门,则充满静穆淡逸的氛围。渚是“静”的,白云、芳草也是静静的。门“闲”,不遇之人,来访者不期然而然的心境也“闲”。一切都显得恬静自然,和谐默契,不受丝毫纷扰。在自然景物的观照中,悄然融入自在平静的心绪,来访不遇的怅然,似乎被这清幽、宁静的环境,带有内省参照的“禅意”所冲化,渐趋恬然。
独闭的闲门,摇曳的小草,使人浸润在“绿满窗前草不除”的幽静自在境界,滋味咸化于这静默的世界之中。
上四句叙寻而不遇,意绪明白。后四句继写一路景观,浑化无迹须缓缓味出。“过雨云松色,随山到水源”。这云松寻源,所趋何向,是不遇而再寻,还是顺便一游其山,还是返回,诗人没有说出。两句以景带叙,下句叙事成份更多些。“水源”,应该不是指来时“经行处”,所以“随山”不是下山,而是入山,随山转折,缘山道探寻水源。道士不在寓所,因此这寻水源,也就是寻道士,“随”字简洁,山道纡绕,峰回路转,随山探源,缘水经山。其间林壑深秀,水声潺潺,都由这个“随”字导人神游,启迪丰富的“曲径通幽”的想象。上句“过雨云松色”,或指道士居所“门外景”,或指“随山”时的景致。“过雨”暗示忽然遇雨,诗人仅仅用一“过”字表示它的刚刚存在,而着意于雨霁云收之后翠绿生新的松色。“过”字,把阵雨带来的清新宜人的气息、物色,轻松自然地托显出来,同时也隐隐带出漫步山道的时间进程。
“过雨”,涮新了松色,也带来冥想。自生自灭的短暂一“过”,和静静白云一样,已在写“禅意”(金性尧)。
尾联的“禅意”,用得精妙。诗人云见了“溪花”,却浮起“禅意”,从幽溪深涧的陶冶中得到超悟,从摇曳的野花静静的观照中,领略到恬静的清趣,溶化于心灵深处是一种体察宁静,荡涤心胸的内省喜悦,自在恬然的心境与清幽静谧的物象交融为一。况且禅宗本来就有拈花微笑的故事,这都溶入默契不言的妙悟中,而领会出“禅意”,因用“与”,把物象和情感联结起来。禅宗的妙悟和道家的得意忘言,有内在相通之处。佛道都喜占山林,幽径寻真,荡入冥思,于此佛道互融,而进入“相对亦忘言”的精神境界。
芳草松色、白云溪花的美感,“禅意”默想的清享,都清美极了。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惬意自得的感受,也都含融在诗的“忘言”之中。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
诗一开篇以杜鹃啼血的典故,实写久不量移的悲苦。“子规”就是杜鹃,又称之为“杜魄”,相传为古蜀帝杜宇所变,日夜悲啼,叫声似“不得归去”,直叫得眼睛出血,是历来诗文中悲苦的象征。武元衡《送柳侍御裴起居》诗说:“望乡台上秦人去,学射山中杜魄哀。”诗人取白居易“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琵琶行》)的诗意开篇,一个“倦”字点明悲苦之久,“不意”的喜悦可想而知。诗人闻“乡禽”黄鹂的叫声而思念故乡,展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时空关隘,以优美的语言、眷恋的情怀,向读者描绘了一幅鲜活有趣、令人向往的故园乡土风情画。故园长安既是诗人的出生、成长之地,也是诗人建功立业、实现平生抱负的希望所在。在迭经变故、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朝廷恩赦,祈盼擢用,于是,家乡变成了作者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由此,诗人不惜浓墨重彩,礼赞了日思夜想的家乡,如痴者之喃,梦者之呓,亦真亦幻,如歌如画。春天的故园,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故乡土地平阔,产出丰富,人情醇厚,生活恬愉,连鸟儿在曾经显出卓著功绩的昆明湖、细柳营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现实是严酷无情的,复出的机会日益渺茫,使作者心灰意冷,徒生伤悲。诗句着力刻画故乡风物,字里行间既蕴涵着往日“翻日迥度昆明飞,凌风斜看细柳翥”的惬意和欢愉,又弥漫着“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的悲苦和忧伤。结尾以拟人的手法,借问黄鹂“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心生忆桑梓”,嘱咐黄鹂速归,将作者戚苦、郁闷、无助、不平而又不甘放弃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
此诗创作于诗人离开永州的前一年。作品显示,作者对现实既失意迷惘,同时对复出抱有强烈的追求和幻想,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在逆境中顽强地跳动。所以语言未失活泼,风格依然俊朗,在意境上有喜有悲,大起大落。全诗以黄鹂一脉贯通,寓意高远,气韵流畅,开合自如,大气泱泱,读后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扼腕生情,回味无穷。
这是一首闺怨词,把思妇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脸霞红印枕,睡觉来,冠儿还是不整。”女主人公刚刚睡醒起来,慵慵懒懒,云髻微偏,花冠不整,那红红的脸颊上还印着几道枕痕。这两句明显脱自白居易《长恨歌》中“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之句子,说佳人犹如当年的杨妃一样娇弱妩媚,“脸霞红印枕”句为词人的创意,清新别致,富有生活情趣。
“屏间麝煤冷,但眉峰翠压,不珠弹粉。”唐·韩僵《横塘》诗中有“蜀纸麝煤添笔媚,越瓯犀液发茶香”之句。抬头看到屏风上情郎亲笔绘制的那幅水墨画,女主人公翠眉紧锁,眼不簌簌地从粉脸上流下来。这三句描写了美人触景伤怀的黯然销魂状,表现了其相思之苦,意境幽美。
“堂深昼永,燕交飞、风帘露井。恨无人,谠与相思,近日带围宽尽。”更进一层写周围的一切使她由冷漠而产生怅恨的感情。“深”与“永”是从空间与时间上表现出她空虚的感触。厅堂幽深寂静,白日漫长难挨,独坐窗前,望着那双紫燕亲亲热热地翩飞呢喃,不时地从帘下掠过,盘旋在水井旁边,不禁愈发伤感起女主人公的孤寂来。女主人公纵有千种风情,万般相思,却无人可以诉说。终日饱受着相思之苦,眼看着自己日澌消瘦,那腰间的衣带已宽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刺激她产生孤寂失望情绪,而“恨无人与说相思”。作者运用这种反衬手法在加深了对少女内心痛苦情感的描写之后,又进而从形体的变化写她相思之深。“带围宽尽”四个字不仅发挥夸张的效果,加深对少女被病折磨的印象,而且将抽象思维具体化,让读者能从衣带宽大去想象她曾经是体态丰满、柳眉桃腮、笑容可掬的模样,与现在的瘦削的形象作对比,更产生了对她因病重而弱不禁风的样子的怜惜与哀叹。
“重省,残灯朱幌,淡月纱窗,那时风景。此情此景不由让女主人公回想起旧日一起欢聚的情景,静谧的夜里,朱红的帷帐内灯烛幽暗,淡淡的月光照在绮丽的纱窗上,那正是你我良宵共度时。“残”与“淡”给“灯”与“月”抹上一层伤别的色彩,景中有情,表现了少女对这难忘的时刻的回忆是痛苦的。这几句写佳人对美好往事的怀念,过片“重省”转入对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刻画。
“阳台路迥,云雨梦,便无准。”阳台、云雨化用“巫山云雨”的典故。如今与爱人远隔万里,只能期望在梦中相见,希望能像楚襄王会亚山神女一样,但梦中之事又没个定准。这三句由回忆转到梦想,写尽其幽思的无限。
“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细问。问因循、赶了青春,怎生意稳?”等他回来后,女主人公心想一定要先指着枝头的花朵让他看,让他明白“花无百日红”的道理,然后再仔细询问他在分别后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迟迟不归。还要质问他,为什么就这样让大好的青春时光白白浪费。这几句心理描写细腻生动,表现了女主人公爱恨交加的心理状态,设问机灵,俗中有雅,动人心魄。
这首词组细致入地展现了一位思妇因景伤怀——回忆往事——梦想——设想将来的心理发展轨迹,生动感人。全词语句华美、脉络清晰,是一首闺怨题材的佳作。
这首词看来不过描写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赎回典当出去的皮裘,但从这件小事却透现出主人公曲折多变的心理。谭献称这首词“姿态横生”(《箧中词续》),确是贴切的评语。词一开头,主人公懊悔万分的神态就呈现在眼前:“悔残春,炉边买醉,豪情脱与将去。”“将去”意为带去。为买酒,仍然在残春时节,皮裘就典当出去了。皮裘一去,似乎连豪情也一并带去了,从中可见主人公与皮裘的关系是何等深切,他对皮裘的情感是何等深厚!所以,他的懊丧心情并非是没有来由的。日月易过,光阴似梭,然“云烟过眼”倒是极其平常的事,引起主人公凄凉心境的是另外的原因:“怎奈天寒岁暮”。“云烟过眼”比喻日月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岁月流逝,眼看严寒又到,然而皮裘被典当于外,御寒无计.这是他的愁因。主人公窘态毕现,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悔而转愁,由愁进而想要设法解愁,于是痛下决心,要积聚起钱来,重新赎回皮裘。“待积取叉头”,“叉头”指钱。宋代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说到自己初到黄州,担忧钱不敷用,每月初将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份,随即藏起画叉,以免钱用过头。每天用剩的钱还要积聚起来,招待宾客时用。“还尔绨袍故”,意为赎还原有的皮裘。“绨袍”本指棉袍,此指皮裘。随着皮裘赎回,主人公的心境也为之一变,愁心一扫而空,喜意油然而生。从“寒且住”的描写中,颇能见出主人公那略带沾沾自喜的神态。但刚觉心喜,却又心情陡变,转而“喜余又怒”了。为什么?“怅子母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子母”指本金和利息,“频权”意为不断变化。“细相”,仔细察看。“抖擞”意为抖动、抖刷。赎裘花的钱比原来多得多,而心爱的皮裘仔细一看,却已有些微蛀了。主人公喜而又怒,心中气愤和惆怅之情交织一起,心情极为繁杂。
下片紧承上片而下,主人公既怒于当铺的收藏不善,又痛惜于皮裘的受损坏,“铜斗熨”,皱折难以熨平,衣襟上酒渍仍在。词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皮裘写得富有生命和情感。主人公未负典当三年之约,皮裘赎回;皮裘向主人倾诉自己三年来的遭遇和离别之情。主人公的心境由对皮裘损坏的惋惜转为对皮裘被耽搁三年的悲叹:“凝睇处,叹毳幕毡庐,久把文姬误。”这句是用典。东汉蔡文姬在汉末战乱中被匈奴所掳,嫁于南匈奴左贤王多年,后曹操将她赎回。“凝睇”意为凝视。“毳幕毡庐”指匈奴族所住的毡帐。把将皮裘赎回比拟为蔡文姬归汉,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对皮裘的深厚情感。全词结束时,主人公想到今后,心境又为之一变:“花风几度,怕白袷新翻,青蚨欲化,重赋赠行句。”“花风”是指春风;“白袷”,白色夹衣。“青蚨”即钱,据《搜神记》载,钱能象青蚨虫一样地飞去又飞回。此时主人公的心情是深切担忧,怕春暖花开,夹衣做好,钱用完时,皮裘又要和他重新分手,他只好再带着痛惜之情写下送行词章。
这首词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描写赎裘之事,以曲折多变、摇曳生姿的心理描写见长。主人公由赎裘而产生回忆、联想,由赎裘而产生悔、愁、喜、怒、怅、惜、叹、忧等种种复杂情感,这些复杂情感随皮裘的命运而起伏变化。词作以一连串形容心理状态的词描写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常常极妙地表现两种心态之间逐渐置换的渐变过程或突变过程。由懊悔而忧愁、由惆怅而惋惜、由惋惜而悲叹、由悲叹而担忧,这是渐渐变化。而由愁而喜、由喜而怒,这又是反差极强烈的心理突变。通过极为细小的赎裘情事,淋漓尽致地刻划人物的种种心理状态,展示人物生活的某个侧面和某种性格,正表现了词人善于寄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