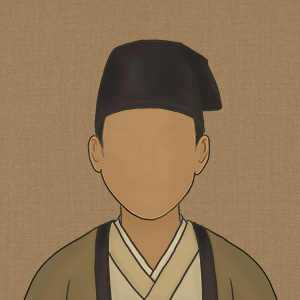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
此赋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叙事写景和议论抒情。
第一部分以叙述人的口气,点出宜春苑的标志性建筑“曾宫”和特殊地貌:发源于南山的水流汇聚成的“曲江”。南望终南山、东驰小土山,西有河水弯曲向北,即为“石濑”之激流。同时,作者也描写了终南山的峰峦和深谷,以及从谷底涌出的泉水。而“曾宫”附近的曲江两岸,则是介于“平皋”和“深山”缓冲地带的丘陵,那里众树“蓊蓑”、竹林“榛榛”,真可谓青山绿水间的休闲胜地也。第一部分结尾句“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既交代了作者“登陂陛之长阪”凭吊二世的荒冢的最终目的,又起到吊古而评人的顺接作用。
第二部分直接进入议论。作者用“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两句,明谈自己的感悟,实是对汉武帝的讽谏。紧接着用“呜乎”一语将情感递进了一层,批评秦二世在操守和德行方面存在的严重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可悲下场。最后,作者面对“二世”不能传到“万世”反而仅三年就没入荒丘时断言:秦二世的墓地“复邈绝而不齐”、其坟丘“弥久远而愈侏”其灵魂即使变为“罔阆而飞扬”“九天”也要“永逝”。至此,作者的情感也由可叹、可怜转到可悲。
全赋以乐景写哀情,感情凝重、议论精辟,实乃劝喻委婉的警帝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