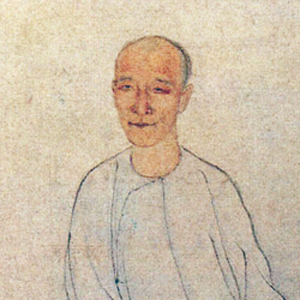上片,运用神话传说,戏弄、嘲笑紫姑神。“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画出了紫姑神“玉肌铅粉”的“箕”体和以“凤呼凰”的“箸”音等的神相。“伶伦不见,清音未吐,且糠批吹音,黄帝乐官的音律中看不到,以“清香”作引诱向善男信女索取香钱这一举动也传开不去,全都属于米皮、谷壳一类的糠秕,四处吹嘘飘扬。紫姑神虽命贱位卑,受到祭祀,但苏轼还是向世人指明紫姑神只不过是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愚弄百姓的“坑三姑娘”。“糠秕吹扬”四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下片,以历史为镜,进一步揭示紫姑神虚无本质的意义。“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处,烂文章”,从“箕”、“箸”之相貌不同凡人入手,将民间“岁正月必衣服箕箒”以祭的“子姑”还以本来面目:诗才敏捷,实为满腹“烂文章”,原是一具愚弄百姓的稻草人。“烂文章”三字,画龙点睛,妙不可言。“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笔锋又一反转。苏轼以历史唯物论指出神话传说也曾被积极利用。即使是紫姑神香檀般的小箸,也可以为现世生活之鉴。谁能借箸代筹以指点江山,只有汉臣张良,别无他人。
全词,以神话与民俗、历史与现实、正反与反正相结合的手法,写了一位“言如响,善赋诗”而又不幸、善变的“紫姑神”。“苏轼以历史学的态度,引神用典,以为警世之治、移风易俗之用。表面戏弄,实富深邃之哲理,值得借鉴。
这首诗中那在白杨树下踯躅的人儿,究竟是男、是女,很难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或她)一定是早早吃罢晚饭,就喜孜孜来到城东门外赴约了。这约会在初恋者的心上,既隐秘又新奇,其间涌动着的,当然还有几分羞涩、几分兴奋。陈国都城的“东门”外,又正是男女青年的聚会之处,那里有“丘”、有“池”、有“枌”(白榆),“陈风”中的爱情之歌《东门之池》、《宛丘》、《月出》、《东门之枌》,大抵都产生于这块爱情圣地。
此时主人公的伫足之处,正有一排挺拔高耸的白杨。诗中描述它们“其叶牂牂”、“其叶肺肺”,可见正当叶儿繁茂、清碧满树的夏令。当黄昏降临、星月在天的夜晚,乌蓝的天空撒下银白的光雾,白杨树下便该映漾出一片怎样摇曳多姿的树影。清风吹过,满树的叶儿便“牂牂”、“肺肺”作响。这情景在等候情人的主人公眼中,起初一定是异常美妙的。故诗之入笔,即从黄昏夏夜中的白杨写起,表现着一种如梦如幻的画境;再加上“牂牂”、“肺肺”的树声,听来简直就是心儿的浅唱低回。
但当主人公久待情人而不见的时候,诗情便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晢晢”——字面的景象似乎依然很美,那“煌煌”、“晢晢”的启明星,高高升起于青碧如洗的夜空,静谧的世界便全被这灿烂的星辰照耀了。然而,约会的时间明明是在黄昏,此时却已是斗转星移的清寂凌晨,连启明星都已闪耀在东天,情人却不知在哪儿。诗讲究含蓄,故句面上始终未出现不见情人的字眼。但那久待的焦灼,失望的懊恼,分明已充溢于字里行间。于是“煌煌”闪烁的“明星”,似也感受了“昏以为期”的失约,而变得焦灼不安了;就是那曾经唱着歌儿似的白杨树声,也化成了一片嘘唏和叹息。
此诗运用的并非“兴”语,而是情景如画的“赋”法描摹。在终夜难耐的等待之中,借白杨树声和“煌煌”明星之景的点染,来烘托不见伊人的焦灼和惆怅,无一句情语,而懊恼、哀伤之情自现。这正是此诗情感抒写上的妙处。由于开笔一无征兆,直至结句方才暗示期会有失,更使诗中的景物描摹,带有了伴随情感逆转而改观的不同色彩,造成了似乐还哀的氛围递换、变化的效果。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词的上片“百五佳期过也未”,清明寒食时节,柳絮千条,阴雨霏霏,更容易惹出愁绪万端。然而今年更是不同,词人所遇之事,使他更平添愁绪百倍。词的上片徐徐写出事情根由,接着描写军笳声起,催动千骑,然而这千万铁骑却并非去浴血疆场,而是调防。词人原任两广总督,直接负责查禁洋船,禁毁鸦片事。后清廷将他调任两江总督,由林则徐继任其职。“看珠澥盈盈分两地”即指这件事。一条珠江,竟将两人隔离两地。尽管林则徐是词人好友,且又是禁烟骁将,但自已失去了与帝国主义对垒、失去了为国家、人民效力的机会,总不免心中万分惆怅,不免对朝廷不满。词中连用两个问句:“君住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表现了这种强烈情绪。词人由于这种恼人的复杂情绪萦绕于怀,以至连时日都搞不清楚,不知“百五佳期过也未”了。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词人对国事的感叹。“召缓征和医并至”,这是暗喻当时朝廷忽而想和,忽而想战,举棋不定的状况。当时朝廷大臣琦善、伊里布之流十分害怕英帝国主义的武力,极力主和,而朝廷则在战和之间拿不定主意,就如病笃乱投医,忽而请这个医生医治,忽而请那个医生医治,莫哀一是。朝廷如此,词人“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以国事为己任,这是沉重的担子。然而这个担子倒是好担,就是朝廷不允许他来担这担子,唯留下沉重的“愁”字,却叫词人感到难以担起,只有将这满腔国愁留于心底。既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欲望要去担当国事的重任,然而却为朝廷所不允许,词人的心境可想而知。于是在词的结尾,词人不由自主地发出“心应碎”的喊声。结句和上片结束处的句式完全一样,这当然是词牌所规定的,但词人有意将词语和句意重复,造成反复、强调的效果,这却又是表现内容的需要了。去留两依依,词人与林则徐之所以两愁相对,正由于他们都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忧心如焚;正因为他们眼见朝廷的暖昧态度,感到国事渐不可为而哀伤至切。
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除“召缓征和医并至”是唯一用典处,其余都明白如家常语,读来丝毫不觉隔膜。词写忧愁意绪却不使人感到消沉,表现的是热血男儿之愁,因此充满阳刚之气,即使愁也显得激烈,即使愁也显得豪壮,也能催发人的悲愤激昂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