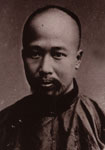此词上片将家国之忧打入个人身世之叹。发端“风拂尘微”一韵,从今时入笔,写秋景:言秋风拂征车之尘,秋雨侵阴凉之榻。开头二句切词题“风雨”二字,“凉榻”切“中秋”一词。从秋景中展示了自己漂泊、凄苦、孤寂的生活。“才动秋思”一句,写愁情秋思由秋景引起。“缓酒销更”一韵,言愁绪满怀只好以酒销愁,“移灯傍影”写出独自饮酒已到掌灯时分,“傍影”突出了形影相吊的孤寂气氛。此时更传来风雨淅沥,芭蕉簌簌的声音,真是“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了,这岂不让人“借酒消愁愁更愁”了。这愁的内涵有二,上述的漂泊生涯是其一,其二就是“铜华沧海”一韵所写的。此韵化用铜驼荆棘与沧海桑田的典故,表达了对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忧虑,当时元灭金已经十年,不断南侵,南宋国势日趋危殆,词人面对这种形势,虽无投笔奋起之壮心,亦有大厦将倾、铜驼荆棘之叹,人生无常之悲。“愁重嶂”一句,既写国家处在阴霾重嶂之中,也表达了自己忧愁犹如层嶂雾霭之状。“燕北雁南天外”言家国之忧与身世之叹不断轮番地袭击自己。此韵,把题中的“风雨”二字的内涵,揭示得最为深刻。“算阴晴”一韵,写在风雨中,个人感受简直像是几次“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般的孤独、寂寞、凄苦。
过片继写“秋思”。接上片歇拍的“故人离合”展开,出个人悲欢离合之事。“青楼旧日”一韵,是逆入,回忆昔日在苏州曾与爱姬相偕的美好时光:在青楼内,玉人陪侍,饮酒高歌,十分惬意。“红叶流光”一韵,平出,转笔写今,金风习习,红叶飘飘,自己已是一事无成两鬓斑白,这一切不禁使“心事如秋水”。“白凝虚晓”一韵,切题“中秋”,写风雨停歇,白云凝虚,天空似晓非晓,室内炉香将烬,只有瓶中一枝桂花倚窗而放。“疏桂”扣“中秋”。此瓶中疏桂,让人有卓尔不群之感。“向深宫”一韵,写中秋之月,虽在风雨之后,依然被白云遮蔽,未能放出光芒,好像嫦娥仙子在深深的月宫中,被嫉妒的云仙团团围住。此结句,将月拟人化,其寓意深刻,与“铜华沧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相呼应,将家国之忧、个人离合之叹,都化在此设问句中,含蓄委婉而深刻。
此词突出特色是将家国之忧、身世之叹、离合之悲三者融而为一,以“风雨”贯全篇,时空交错,含蓄委婉,感情深挚。正如俞平伯所说:“他们(指姜白石、吴文英等)每通过典故词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眷怀家国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比之‘花间’词为深刻,也比北宋词有较大的进展。”(《唐宋词选释·前言》)。
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