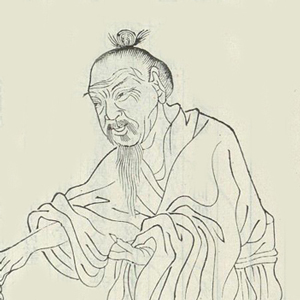译文及注释
译文
茂盛的春草绵延万里,落日余晖洒在当初离别的房子上。
明明知道离开家乡到塞外已经三年,却没有从外面寄回一纸书信。
注释
馀:同“余”。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朔风凄厉,已近岁末。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严寒袭人,饥更来煎。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人虽已经离去,情却常难断绝。因此就有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伤,有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无奈。此诗即借一位妻子真切的内心独白,抒写了这种难以言传的离情别意。
“车遥遥兮马洋洋”——诗之开篇,是女主人公追忆夫君离去的梦幻般的虚景。不过,在此刻追忆之际,这虚景也可能为眼前所见的实景所引发。似乎是一个春日的早晨,阳光明媚、草色青青。画面近处,则是一位倚栏而立的女子,正痴痴地注视着穿过新绿树影的车马,东来西往。倘若能从近处观察,你便可发现:她其实并不“看着”车马,而是沉入了迷茫的幻境之中——眼前的车马,勾起了她十分珍贵的忆念。她仿佛觉得,此刻还正是亲爱的夫君离去的时候:那车身也一样颠簸、轻摇,那马儿也一样舒缓、潇洒。就这样在遥遥无尽的大道上去了,什么时候再见到它载着夫君归来?当消歇的马蹄声,终于将她从幻境中惊觉,车马和夫君便全都云雾般消散。美好的春景,在女主人公眼中只变得一片黯然。这无情之景,不过让她忆及往事,徒然增添一段缠绕不去的思愁罢了。
这就是“车遥遥兮马洋洋”所化出的诗境。这诗境妙在没有“时间”。它既可能是女主人公独伫楼头所见的实景,又为一个早已逝去的美好虚景所叠印,便在女主人公心中造出一片幻觉,引出一种惆怅失意的无限追念。
“追思君兮不可忘”,即承上文之境,抒发了女主人公追忆中的凄婉情思。那情景怎么能够忘怀呢——当夫君登车离去时,自己是怎样以依恋的目光追随着车影,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倾身于栏杆。倘若不是空间之隔,她真想伸出手去,再攀住车马话别一番呢!夫君究竟要去往哪里?“君安游兮西入秦”正以自问自答方式,指明了这远游的令人忧愁的去向。她说:夫君之入秦,既然是为了求宦进取,我自然不能将你阻留;只是这一去颠沛万里,可教我怎能不牵挂你?句中的“安游”从字面上看,只是一种幽幽的自问之语。不过在体会女主人公心境时,读者不妨把它理解为对旅途平安的一片祈祝之情。她当时就这样噙着泪水,送别了夫君。全没有想到,夫君的“入秦”竟如此久长,使自己至今形单影只、空伫楼头。
对往事的温馨追忆,由此把女主人公推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而人在痛苦的时候,想象力往往异常活跃。在女主人公倚栏独立、顾影自伤之际,一个重要的发现吸引了她。她想:世界上什么事物最难分离?这静静跟随着她的地上的身影就是!影之于身,朝暮相随、无时不在,没有人能将它们分离须臾。那就让我作夫君的身影吧!那时候不管登山还是临水,我都能时时陪伴着他。倘若是举杯邀月,他便可和我月下共舞;倘若他夜深难寐,我便跟随他漫步中庭——我再不会感到孤单,夫君也不会再有寂寞,那该有多好呵!“愿为影兮随君身”一句,正是女主人公顾影自伤中触发的奇妙诗思。这诗思妙在来自日常生活,而且特别适合于常常陷入顾影自伤痛苦的女子心理。这诗思又异常动人,表现的是虽在痛苦之中,而关切夫君犹胜过自身的妻子的深情。
想到这里,女主人公似乎颇有些喜意了,因为她“解决”了一个日日萦绕她的痛苦难题。但她忽然又想到,身影之存在是需要“光”的。若是身在背阴之处,那影子也会“不见”的,这样岂不又要分离?她简直有些焦急了,终于在诗之结尾,向夫君发出了凄凄的呼唤:“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夫君哪,你可不要到那背阴处去呀,一去我就会不见了。你站在阳光下好吗?那可是我的一片心愿呢!
这位深情的妻子,分明是被别离的痛苦折磨够了。在她的心中,再挨不得与夫君的片刻分离。痛苦的“追思”引出她化身为影的奇想,在这奇想的字字句句中,读者所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不离”!“不离”!“不离”!而诗中那六个连续使用的“兮”字,恰如女主人公痛苦沉吟中的叹息,又如钢琴曲中反复出现的音符,追随着思念的旋律,一个高似一个,一个强似一个,声声敲击在读者的心上,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这首诗完全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或者说是她一片痴心的“自说自话”。迷茫中把眼前的车马,认作为载着夫君离去的车马;为了不分离,就想化为夫君的身影;而且还不准夫君站到阴处:似乎都可笑之至、无理得很。然而,这种“无理得很”的思致,倒恰恰是多情之至微妙心理的绝好表露。
这首词明写春景,暗抒离情。上片写眼前景色。水流歌断,春风又暮,从而引起往事的怀念。下片写梦境。碧水黄沙,梅花无数,而月随人去,花自无语。全词抒情委婉,含蓄蕴藉,幽美清雅,饶有韵致。
上片首句以一个“清”字为全词感情上定下了幽清的基调。“水流歌断春风暮”,这句是说那流水般的一曲清歌,春风吹拂的暮霭中结束了。“春风暮”,景语,一字一景,词中以下诸景,皆缘此三字而来;这里也同时点出了这首词的特定节候,这正是一个怀人的季节,怀人的天气,怀人的时刻。“水流”,字面上自然是写“清歌”的缠绵婉转,由此,作者的笔触转入怀人。
作者写怀人,非用泛泛之笔,而是借助于一个梦境,把怀人念远的思想情绪写得深刻入微。“梦云烟树,依约江南路”以及下片的“碧水黄沙”云云,皆是梦境,用笔上又极见层次。“梦云”、“依约”两句是入梦之境。“云”,是“梦云”,“树”是“树”是“烟树”,“江南路”是“依约”(由“云”而“树”而“路”,由飘忽而实,梦中寻找知音的足迹甚明。
下片写梦中寻觅和对月怀人。“碧水黄沙”,紧承上片结句之意,进一步写对知音的寻觅。如果说上片“依约江南路”是朦胧中辨认知音去路的话,那么,“碧水黄沙”所表现的则是到处寻觅,水中陆上,无所不至,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了,且四字属对工稳,色彩鲜明,为本词的唯一亮色,这正是作者用笔变幻处。“梦到寻梅处”是穷尽“碧水黄沙”辗转寻找的结果,笔法由面到点,然后由“寻梅处”引出“花无数”,再由花而人,向花打听知音之所。
这几句,用笔如剥茭,一步一层,层层转深,转愈深而情愈切,及至问花无语,寻觅无着,顿挫之下,不禁怅然若失,愁绪茫茫,不知所之,转见明月,也好像已随那人运去,而失去了它那固有的光辉。“明月随人去”一句所展示的空间既大且空,读之令人如置身于一个广漠而暗淡的世界,进而想到作者于此所寄寓的感情必然是悲凉而空虚的。此时的作者,是醒是梦,已难分难辨之际,这真是以景传情的神来之笔。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
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