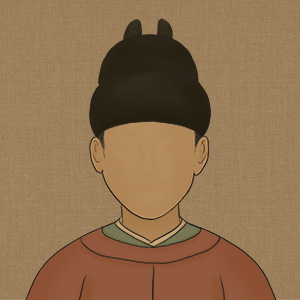魏国地处北方,“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朱熹语)。然而,华夏先民是勤劳而乐观的,《魏风·十亩之间)即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前人评《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
《菩萨蛮·凤凰相对盘金缕》是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之中的一首,仍然是由一个个富有美感的意象缀联成篇的,如“风凰”、“金缕”、“牡丹”、“微雨”、“明镜”、“画楼”、“丝柳”、“双燕”等等。词之上片,写美的头饰、美的妆容,并非词之精粹部分,其实是为下片张本;而下片,全由新妆美人若有所待的“望”字而来,“相望久”,既表现了她的痛苦、无奈,更表现了她对美好爱情的渴盼与执著上片,运用寄意于象的艺术手法,写女子晓妆,寄托女子情思,隐约婉转,暗示她的期待。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写美女头上的“凤凰”首饰,并以“相对”二字,突出双鸟比翼之象,借以烘托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憧憬、对情人的企盼;“牡丹”一句,形容佳人妆成,像雨后牡丹一样美丽,将思妇华丽的服饰,娇媚的情态展现出来;再写镜中所见,“双经长”一语,表现人之憔悴,将其离愁、相思之苦暗透出来。“明镜照新妆,鬓轻双经长。”写女子梳妆完毕,对镜审视一“明”一“新”,都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表露出女主人公珍爱自己并有所待。然而,镜中的形象却是鬓发削薄,双颊削瘦,经形都显得长了。下片,女子的孤独,惆怅、失望的情绪散布在字里行间。
“画楼相望久。”女子默默地、长久地等待心上人,但心上人迟迟不归。期盼之情,难对人言,句中用一“望”字,突出女主人公的深情盼望、望眼欲穿。此一“望”字,乃全篇词眼,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栏外”以下三句,都是“望”中所见、所思。“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写女子痴望已久,不见人归。低垂的柳丝、双飞的春燕,无一不在惹起、象征春天女子的春怨,而“音信不归来”的插入句,又与“社前双燕回”形成对比——去年秋天飞走的燕子已经双双归巢,可她痴心等待的心上人却久盼不归,甚至已得不到关于“他”的一点音信,这对于“相望久”的女子,足见其冷酷与残忍。
此词景以情牵,情随境变,直吐怨情,贴合温词造语精工、密丽浓艳的风格。通过景象对比,反衬思妇孤独之状、愁苦之情、心外之声,格外深婉。
此诗题为赠人,实为叙志咏怀,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此诗通过讥嘲周公、孔子和向往自由的表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只好向醉中逃避。
首二句,先写“百年”,次写“万事”,以“百”、“万”两个约数接“扰扰”、“悠悠”,且以表示内在感情的“长”、“悉”相衔接,概括了时间、空间和人事的纷繁,显示出诗人厌烦尘嚣、追求解脱的心理。由于诗人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自撰墓志》)。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原先以正统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为楷模,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他觉悟到:正是“礼乐”囚禁了“姬旦”,“诗书”缚住了“孔丘”。囚禁、束缚二句,在前两句的映衬对比下,显得分外强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随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东流,不必说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礼乐的束缚,又受人事的拘牵,在忧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联,诗人以自然的景象与不自由的自我进行对比,至“礼乐”、“诗书”一联发而为愤激语。诗人决心皈依自然,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归隐田庐,不仅永远做不了圣人,还必须放弃一整套与正统儒家思想相关联的处世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对抗社会,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就是睡与醉。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为念的生活;醉,意味着对社会的消极反抗。这也就是诗人在《田家三首》《醉后》《过酒家五首》中所说的:“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史载王绩嗜酒,为六合县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职。《全唐诗》今存王绩诗一卷,多绕酒气。不仅是里多次出现“酒”和“醉”等字眼,其诗题中亦多“酒”字。虽篇篇有酒,但无一醉语。
就这首诗而论,表现出的,不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潜的萧疏旷达之风,而且以自然的语言,遒健的气概,涤净初唐排偶板滞之习,与他著名的《野望》诸诗一起,透露出唐诗未来的新曙光。
王衍是五代十国时前蜀的亡国君主。他不问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这首醉妆词就是他生活的写照。词调是王衍所自创。《花草粹编》卷一引《北梦琐言》说:“蜀主衍,尝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胭脂夹脸,号‘醉妆’,衍作《醉妆词》。”
词极写恣意游宴的乐趣。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这首词开头几句是说,这边走那边走,终日宴游寻花问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后几句是说,那边走这边走,时时歌舞贪饮金杯酒。
为了透彻而极致的写出宴游的乐趣,作者采用民歌中常常运用的重沓交错的手法,从而构成回环往复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处处花柳,触目芳菲的环境,表现了流连赏玩,耽于淫乐的情景。
“者(即这)边走,那边走”,这是略呈变化的重叠复沓。而“那边走,者边走”,则不仅本身重叠复沓,而且和前者又形成参差交错的特点。再加之它们稍被间开,而全词又是不分片的小令,一气直下,所以词既顿挫有致,又特别显得珠圆流走,音节上十分谐婉。“只是寻花柳”和“莫厌金杯酒”,因为被复沓句隔开,造成一种偏宕之致。它们前后的出现,表达了赏景和酣饮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只是”、“莫厌”二词,则又将人流连于良辰美景,沉溺于赏心乐事的一种极端的追求欲望表现了出来,这种沉浸于醉生梦死的颓废情绪是很强烈的。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