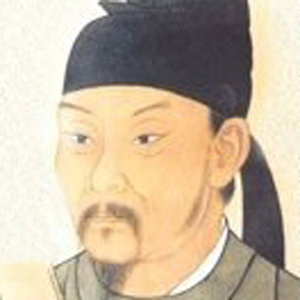《己亥杂诗》写于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己亥)龚自珍辞官返乡之时,由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计315首,全属七言绝句(其中部分不依近体格律的古绝),堪称中国诗史上最大规模的组诗。可以说,在这一组诗中,定庵向时人、也向后人集中展示了自己复杂而又饶具魅力的内心世界。研究龚自珍其人、其文学成就,《己亥杂诗》应是重中之重。
此篇是《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五首,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龚自珍的一篇诗体自传。由高中甲科到倦飞知还,再到解嘲式地敷衍“如玉美人”,诗人“嵚崎楚客,窈窕吴侬”、“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能令公少年行》)的理想终于在一种无奈的状况下实现了。可这又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归宿。诗中连用三个“偶”字,加之“佳人”、“寻春”的锦绣字面,仿佛在昭示这一切只是“妙手偶得之”。而在字里行间还是掩抑着诗人的苦笑和酸楚。所谓“以乐写哀,其哀倍之”,定庵是深谙个中奥窍的。但就是这点一般读者都能够察觉的苦衷,身为文学批评大师的王国维居然硬是感受不到,在他那部被不少人顶礼膜拜的名著《人间词话》里就据此诗指责“其人之儇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可见偏见的力量有时是很可怕的。
此外尚应指出,《己亥杂诗》之一百零七首“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与此篇意旨全同,手法则各尽其妙,可以对读。
这首长歌二十八句,可谓中秋诗中的长篇之一。开端写明月未出和初出之景,瑞光生白毫,银阙涌苍穹,云散如崩涛,并想象用银河水洗天公眸子。接下去写星宿、水灯、寒螀、露草等,营造出一片澄明之境,渗透着对景怀人之情。诗人极写中秋明月之美和他人的欢乐,更衬托出自己悲凉的心情和寂寞的处境。最后又安慰鼓励对方,突出手足之深情。全篇单行直贯而下,想象奇丽,比喻新警,诗句流丽婉转,唱叹有致,令人吟诵不已。
诗一开篇即描写明月出来的雄伟气势,月亮还未出群山之时,已经是光芒万丈。“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白如崩涛”,写出了月亮升起的景象,描述得灵动诡谲,有声有势,气象壮阔,明月不可阻挡之势和它的光彩让人诧异。接着,诗人收笔,写月亮的明亮与光洁,“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就有几分小巧。将月亮比作明亮的眼睛,该花费银河千斛水,才使眼睛如此明亮,奇思妙想,令人惊叹。可见苏轼的诗歌在重情感而不拘于情感、重气势而不拘于气势的表现中,粗犷间有细腻,厚重间有轻盈。
继而诗人又将月亮与苍龙七宿相比较,反衬月亮的明净。心宿“如弹丸”,在西南方向闪着光芒;整个苍龙七宿盘在西天,熠熠发光。到中秋的夜晚,角、亢、氐等星宿已落入西方地平线,并不是整个苍龙都可见,所以诗人又补充道“注眼看不见”。月亮升起之后,星光更暗淡了,仿佛在与飞舞的萤火虫争夺着光亮。“千灯夜作鱼龙变”“低昂赴节随歌板”,描写中秋节的民间习俗,引人遐想。诗的后半部分,从描写家庭赏月的欢乐和温馨,写到对远方弟弟的思念和劝慰。“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这是安慰鼓励苏辙的话,意思是说,虽然贫困,却能对月赋诗,这儒雅的生活也足以快意。
全诗景情交错,从天宇山川写到社会民俗,再到家庭亲情,诗情顿挫,低回中转酣畅,激越中出哀婉,实为中秋咏月长诗中的上乘之作。
诗人在这首诗中之所以着意渲染若耶溪水色的清澈和环境的幽静,正是为了寄托诗人喜清厌浊、好静恶闹的情怀。
一、二句,叙写作者乘着小船进入若耶溪。“轻”、“去何疾”和“已到”这几个字,传达出诗人由于舟行迅疾、将入佳境而激起的欢快、惊喜之情。三、四句,描写诗人到达云门山下,在清澈如镜的溪水上轻轻荡桨,畅游山水风光的情景。但诗人并没有正面描写溪两岸的青山、绿树、溪花、幽草,甚至也没有写云门山和云门寺;而是着意抒写自己同美妙大自然的感应与融合。“起坐鱼鸟间”一句,是写自己在船上欣喜地忽起忽坐,时而仰望碧空翔鸟,时而俯视清溪游鱼;“动摇山水影”一句,则描写自己天真地用船桨拍击溪水,看青山的倒影在水中动摇、变幻。这两句诗,表现了诗人的身心无拘无羁,与鱼鸟游翔,与山水嬉戏,完全与美妙的大自然契合无间。这两句着重写动态,从鱼鸟、山水和诗人自己的活动中表现一种“空灵”的境界,既清澈、空明,又灵动、有情趣。
五、六两句,着意渲染清溪的幽静。但诗人并未把它写成一片死寂,而是以声音反衬寂静。诗人谛听着溪岸山岩中发出的各种声音,并且饶有兴致地期待着山岩自己的回声。同时,他还感觉到在这清溪里说话,尽管暂时打破了深山溪谷的寂静;但话声一停,环境越发显得清静。环境如此幽静,使诗人深深感叹“事事令人幽”。此时,即将没入西天的夕阳,将一束淡淡的光辉洒落在这缥碧澄清的溪水上,诗人情不自禁地停下船桨,面对着夕阳,让全身沐浴在残余的阳光之中。诗到这里,戛然而止。但这一束射到溪中的夕阳光,却使这蜿蜒曲折的若耶溪,一路上都穿行在林荫蔽天的山崖之间的清静幽深境界如在眼前了。
本篇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辛弃疾四十岁,南归至此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作者满以为扶危救亡的壮志能得施展,收复失地的策略将被采纳。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如此,作者反而因此遭致排挤打击,不得重用,接连四年,改官六次。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这一调转,并非奔赴 他日夜向往的国防前线,而是照样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小官。现实与他恢复失地的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作者见景生情,借这首词抒写了他长期积郁于胸的苦闷之情。
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失宠女人的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的忧虑和屡遭排挤打击的沉重心情。词中对南宋小朝廷的昏庸腐朽,对投降派的得意猖獗表示强烈不满。
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的复杂情感。词以“更能消”三字起笔,在读者心头提出了“春事将阑”,还能经受得起几番风雨摧残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更能消"一句是就春天而发,实际上却是就南宋的政治形势而言的。本来,宋室南渡以后,曾多次出现过有利于爱国抗金、恢复中原的大好形势,但是,由于朝廷的昏庸腐败,投降派的猖狂破坏,使抗战派失意受压,结果抗金的大好时机白白丧失了。这中间虽有几次北伐,结果均以签订屈膝投降的“和”而告终。北伐的失败,反过来又成为投降派贩卖妥协投降路线的口实。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匆匆春又归去”,就是这一形势的形象化写照,抗金复国的大好春天已经化为乌有了。这是第一层。但是,作者是怎样留恋着这大好春光呵!“惜春长怕花开早”。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何况落红无数!”这两句一起一落,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落红”,就是落花,是春天逝去的象征。同时,它又象征着南宋国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阴虚掷,事业无成的感叹。这是第二层。面对春天的消失,作者并未束手无策。相反,出于爱国的义愤,他大声疾呼:“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实际是向南宋王朝提出忠告,它形象地说明:只有坚持抗金复国才是唯一出路,否则连退路也没了。这两句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明知春天的归去是无可挽回的大自然的规律,但却强行挽留。词里,表面上写的是“惜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急切心情,反映了作者对投降派的憎恨。这是第三层。从“怨春不语”到上片结尾是第四层。尽管作者发出强烈的呼唤与严重的警告,但“春”,却不予回答。春色难留,势在必然;但春光无语,却出人意外。所以难免要产生强烈的“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又怎能不羡慕"画檐蛛网"?即使能象"蛛网"那样留下一点点象征春天的“飞絮”,也是心灵中莫大的慰藉了。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以小小的“飞絮”作结。上片四层之中,层层有起伏,层层有波澜,层层有顿挫,巧妙地体现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
下片借陈阿娇的故事,写爱国深情无处倾吐的苦闷。这一片可分三个层次,表现三个不同的内容。从“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是第一层。这是词中的重点。作者以陈皇后长门失宠自比,揭示自己虽忠而见疑,屡遭谗毁,不得重用和壮志难酬的不幸遭遇。“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层,作者以杨玉环、赵飞燕的悲剧结局比喻当权误国、暂时得志的奸佞小人,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闲愁最苦”至篇终是第三层,以烟柳斜阳的凄迷景象,象征南宋王朝昏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现实。
这首词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一是通过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时局的关切。拟人化的手法与典故的运用也都恰到好处。第二是继承屈原《离骚》的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的政治斗争。第三是缠绵曲折,沉郁顿挫,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词风。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婉约”,实际上却极哀怨,极沉痛,写得沉郁悲壮,曲折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