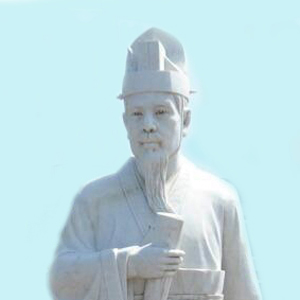上阕“我又南行矣!”一声惊叹感喟语劈首揭出,便现突兀倔傲之势,然而,这并非故作姿态,实在是积郁不平的迸发,所以才含蕴丰厚、情意挚深,足可振起通体,为下面开出无限天地,直注终句。“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是写一己的生活遭际。龚自珍去年春天方于苏州结缡,新妇系外祖父段玉裁之女孙段美贞,现在她留居龚父丽正徽州官舍,南北离居; “笑”,笑我为了微末功名奔波风尘,不惜割舍新婚后的旖旎柔情没有什么价值。如今落第返归,情怀自能想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又是换一种说法。杜甫《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词中反其意用之,谓即使文章佳绝,为天下知闻,也不过空谈而已,于苍生国计没有切实补益。 “文章”,因为功名不就,故无法推行,方有上面流露出来的叹息。以下再进而申足此意:“似春水,干卿何事?”朝廷自有定策成计,所行止岂于彼一介书生相干,又岂肯听汝哓哓,这实在是冷峻之极的反语。
以上叙事抒怀,尽吐一腔垒块。后自‘‘暮雨忽来”到“去如水”四句则转笔写景,紧扣眼前见闻。骤然间暮雨急倾,鸿雁已惊飞,杏杳无踪,环顾天地呼啸、关山莽莽苍苍,一派秋声入耳动心,似乎也在催人归去,“去如水”,莫再迟回疑虑。句中的“客”当系自指,就南返行径所言,暗暗透出此次京都之行的失望。
下阕推想未来人生情景,表露胸中夙愿与壮志。“华年心事从头理”,经过屡次落第不遇的现实教训,懂得社会人生的艰难坎坷,就不再是那么单纯幼稚、仅凭一腔热情行事处世了,需要从新认识,估价早先的“心绪”。 “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汉·枚乘《七发》有广陵观潮的描写,认为功用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脏,澹澉手足,颒濯发齿;榆弃恬怠,输泻滇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又《史记》载伍子胥吹箫乞食于吴市,以上藉旧典表明将不再继续皓首穷经、寻章雕句的腐儒岁月,而是冶游狂侠,浪迹江湖,这正属“心绪从头理”后的结果,因之接着叙说:“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还拟延揽结交天下人才,共谋经国大业,而不只幻想依赖一二当权者了。
以上壮怀豪情足可以惊动人心,便觉秋去春来,荣枯递代,天下事无逾此理者,不必拘拘于一时成败。结拍“木叶怨,罢论起”,借现事以归束全篇。
这首词因落第出京触引,叙事咏怀,纵横倾泻,直觉—派沉郁悲慨之气勃然纸上,而柔情侠骨交注笔端,咳唾珠玉随处生发,正属定庵的一贯格调。
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文荟萃,富庶繁华,不仅有喧闹的街市,高耸的楼榭,还有数以百计的名园佳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又载当时的京城市民有探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都人争先出城探春”。这时,达官贵人们的私家花园也一齐“放人春赏”。这首《贵侯园》就是写春天游赏名园的,但值得寻味的是,这首小诗的主题并不是赞美,而是讽刺。
第一句“名园虽自属侯家”,起得很平淡,但含义颇深。“名园”,“属侯家”,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诗人却用“虽自”两字把它们组合起来,作一转折,引出下文。诗人进一步写道:“任客闲游到日斜。”虽然名园属侯家所有,但游人却可以随意游玩、规赏。“到日斜”三字,把“任客”和“闲游”的含义表达得十分透彻。诗写到这里,等于说各园虽属侯家,但也属于大家。但诗人的用意并不在此。
诗人紧接着又写道:“富贵位高无暇出”,这就告诉读者,贵侯徒有名园,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前来观赏。有趣的是诗人对“无暇出”所作的注脚——“富贵位高”,这就是“无暇出”的原因。最后一句“主人空看折来花”,名园的主人也赏花,不过他所观赏的只是失却了生命力的“折来花”。诗人说,这是“空看”,因为这种花决不能使人领略到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意趣。如此观花只能是可悲的。侯门深似海,贵侯们深居简出,纵使坐拥名园,也难得一至,只能看看折下的花。至此,诗中才显出“虽自”二字的份量:名园并不属于那些占有者贵侯们,富贵使他们无从接近大自然,也便失去了造化赐予人类的美的享受。
这首诗质朴无华,但含意深刻,对于贪婪的占有园林之胜的贵侯们,予以辛辣的讽刺。
此词上片抒依依惜别之情,并设想别后自己一人的孤苦凄哀;下片自悼身世,更为悲苦。此词哀婉沉痛之极,几令人难以卒读,艺术上创造性地运用了二十余处叠词。
此词起三句,是写眼前景,抒此时情,点出夕阳残照的背景:“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正是暮色苍茫时分,斜阳一抹,欲落未落,残照丝丝,闪烁未消,人在这种境界中分别,心绪正如微云寸寸飘忽,感情还若残照丝丝不断,真如南唐后主李煜所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用“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二句具体描画人在将离未离之际的欲语无言,魂不守舍。于极度哀伤中,仿佛灵魂都已出窍,正闪闪摇摇,漂荡游离,无所依托。抬眼看去,
“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山山水水依旧,人已在山山水水中渐去渐远,望断山水却望不见人,那种惆怅、那种悲苦、那种失落、那种凄凉,实在是“人间没个安排处”。
“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三句,把此时此地的离愁别恨、凄苦难捱推及今后的岁岁月月“只似今朝”,也可谓情到深处反无言了。上片于写景中抒发离别时的留恋不舍,微云、残照、山山、水水皆被一片愁云惨雾所弥漫,实为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天空、地上充溢了诗人的不尽离思。
下片历写离别后的凄冷忧伤,以遥问青天而青天不应劈空而来,千言万语尽在此一问中。“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自意中人离去,双卿孤独无依,内心苦楚无处言说,“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从此无人管顾、无人痛惜,任双卿独自憔悴,黯然销魂;“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再无人欢欢喜喜、情切切意绵绵地看双卿偷素粉学化妆时的情景了。这几句与李商隐《无题》诗中“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同义,应是诗人与意中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时的趣事,难以忘怀,不忍忘怀。词至末三句“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结出生生世世,此情不泯,夜夜朝朝,凄苦依旧的一片痴情。
这首词写景处,景景有情,写情处,情情难抑,虽从女方立意,而两情坚贞历历可见。全词几乎句句都用叠字,读起来,仿佛听到诗人在悲悲切切地诉说,呜呜咽咽地呢喃,言虽尽而意不绝。
这是一首咏月词。
开篇“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以问句起。这份奇丽“月上柳梢头”的景象恰是躺柳下“藤床”纳凉仰看天宇者才能产生的幻觉:“翠柳”伸向天空,而“明月”不知不觉便出现了,如同被推上去一样。加之月夜如水一般的凉意,更会引起美妙的幻想,于是纳凉赏月的词人飘飘然“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以下写词人凭幻想飞入月宫后所闻、所见及所感。这里雾冷风轻,隐隐可闻“笙箫”,和仙子的“环佩”之声,大约她们正随音乐伴奏而飘飘起舞吧。然而“玉锁”当门而“无人掣”,说明月宫清静,不受外界干扰,原本打算寻声暗问的词人不觉感到怅然。回顾天空,是“闲云收尽”,海光与月光交映生辉,炼成一片令人眩惑的景象。
过片:“谁信有药长生?”则针对关于月宫的传说,抒发自己的见解。据说有玉兔捣药,这药可以使人延寿的。然而“长生”的念头,只不过是世俗的妄想。月中,只有“素娥新炼就”的“飞霜凝雪”而已,并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词人看来,人间那些“打碎珊瑚”之类的夸豪斗富之举,远比不上赏玩月中枝叶扶疏的仙桂来得超凡脱俗。“打碎珊瑚”出于《世说新语。汰侈》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这里信手拈来,反衬月中桂树之可爱,自然惬意。作者通过如此清空的笔墨,勾画出一个美丽、纯洁、没有贪欲的境界。这里,他两袖清风,“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感到凡心洗尽,有脱胎换骨之感。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月下的梦,尽管美丽动人,却又无从对证,只能自得于胸怀,不可为俗人说。故结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深沉的感喟和对尘世的深切厌倦见于言外。
这首词写藤床上神游月宫之趣,其间融入了月的传说,其境优美清寂,塑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似乎有意与充满烽烟势焰的人间对立。故前人或谓其为“不食烟火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