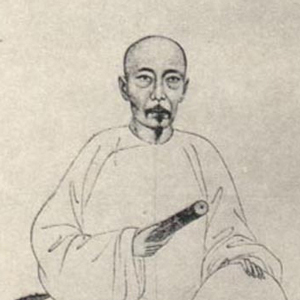此诗是一首七言短篇歌行体诗歌,写由江陵长江中流回头西望三峡的情景。每二句一韵,凡四转韵,每韵一意。
第一韵写长江三峡峰峦之多。长江三峡“山之多不知其几千里,不知其几千万峰,山之高且大如是”(范成大《吴船录》),船在万峰中朝漂夕浮,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在此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中,真是“不信人间有平地”。此联是作者出三峡的回思,用跌宕转折之笔,写在横亘千里奇峰陡崖中行舟的感受――峡里山多与山高。
第二韵写由江陵长江中流西望不见峡山。诗人受辛弃疾邀游楚国别宫——渚宫,由渚宫沿江西望,江水汹涌奔流如罗带,碧绿湍急的江水一望无际,水天相接一色,江面辽阔广漠,“却疑平地元无山”,真是过了夷陵(今宜昌西北)“回首西望,则渺然不复一点;惟苍烟落,云平无际,有登高怀远之叹已。”此联是诗人从江陵平坦之地回头遥望,江天一片空旷,略无高处,故作此江长水大“水连天”及“却疑平地元无山”疑辞,表现峡外的平旷景象,真是“送尽奇峰双眼豁,江天空阔看夷陵。”(清人张问陶《出峡泊宜昌府》)
第三韵写对峡里山、峡外水变换情况的感想,由写景转入抒情。诗人从桂林经湖南至荆州,然后沿秭归、巴东、巫峡、万州一线入川,而今又从“千峰万峰巴峡里”来到“水连天”的江陵,南北往返,颠沛流离多年,经历了许多山山水水,这山水相迎相送,回想起来,这世事仕途真如转头即灭的梦幻一样。此联是自然山水拟人“送迎”现象触发诗人对世事仕途的感慨,其内涵意味深长。
第四韵写诗人长途艰难、盼速归。山水相迎送,世事如浮云、梦幻,这万里归程才行过三千,在这三千里山川旅程中已做过几回梦,不知到苏州西南的太湖之滨,再经几次梦境才会到达。此联写诗人在经历山川变换、宦海浮沉后,已悟出世事仕途如过眼云烟、如梦幻虚无缥缈的道理,并表露出他思念石湖,急盼归家的心情。
此首七言古诗,转折轻妙如行云流水,内涵深蕴,真是神韵兼备的佳作之一。
这是作者滞留异乡、思念妻子之作。题目“端居”,即闲居之意。
诗人远别家乡和亲人,时间已经很久。妻子从远方的来信,是客居异乡寂寞生活的慰藉,但已很久没有见到它的踪影了。在这寂寥的清秋之夜,得不到家人音书的空廓虚无之感变得如此强烈,为寂寞所咬啮的灵魂便自然而然地想从“归梦”中寻求慰藉。即使是短暂的梦中相聚,也总可稍慰相思。但“路迢归梦难成”(李煜《清平乐》),一觉醒来,竟是悠悠相别经年,魂魄未曾入梦。“远书归梦两悠悠”,正是诗人在盼远书而不至、觅归梦而不成的情况下,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叹息。“悠悠”二字,既形象地显示出远书、归梦的杳邈难期,也传神地表现出希望两皆落空时怅然若失的意态。而双方山川阻隔、别后经年的时间、空间远隔,也隐见于言外。
次句写中宵醒后寂寥凄寒的感受。“敌”字不仅突出“空床”与“素秋”默默相对的寂寥清冷的氛围,而且表现出空床独寝的人无法承受"素秋"的清冷凄凉的情状,抒发了难以言状的凄怆之情。素秋,是秋天的代称。但它的暗示色彩却相当丰富。它使人联想起洁白清冷的秋霜、皎洁凄寒的秋月、明澈寒冽的秋水,联想起一切散发着萧瑟清寒气息的秋天景物。
对于一个寂处异乡、“远书归梦两悠悠”的客子来说,这凄寒的“素秋”便不仅仅是引动愁绪的一种触媒,而且是对毫无慰藉的心灵一种不堪忍受的重压。然而,诗人可以用来和它对“敌”的却“只有空床”而已。清代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引杨守智说:“‘敌’字险而稳。”这评语很精到。这里本可用一个比较平稳而浑成的“对”字。但“对”只表现“空床”与“素秋”默默相对的寂寥清冷之状,偏于客观描绘。而“敌”则除了含有“对”的意思之外,还兼传出空床独寝的人无法承受“素秋”的清寥凄寒意境,而又不得不承受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灵深处的凄怆,那种凄神寒骨的感受,更偏于主观精神状态的刻画。试比较李煜“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便可发现这里的“敌”字虽然下得较硬较险,初读似感刻露,但细味则感到它在抒写客观环境所给予人的主观感受方面,比“不耐”要深细、隽永得多,而且它本身又是准确而妥帖的。这就和离开整体意境专以雕琢字句为能事者有别。
三、四两句从室内的“空床”移向室外的“青苔”、“红树”。但并不是客观地描绘,而是移情入景,使客观景物对象化,带上浓厚的主观色彩。寂居异乡,平日很少有人来往,阶前长满了青苔,更显出寓所的冷寂。红树,则正是暮秋特有的景象。青苔、红树,色调本来是比较明丽的,但由于是在夜间,在迷蒙雨色、朦胧夜月的笼罩下,色调便不免显得黯淡模糊。在满怀愁绪的诗人眼里,这“阶下青苔与红树”似乎也在默默相对中呈现出一种无言的愁绪和清冷寥落的意态。这两句中“青苔”与“红树”,“雨中”与“月中”,“寥落”与“愁”,都是互文错举。“雨中”与“月中”,似乎不大可能是同一夜间出现的景象。
但当诗人面对其中的一幅图景时(假定是月夕),自不妨同时在心中浮现先前经历过的另一幅图景(雨夕)。这样把眼前的实景和记忆中的景色交织在一起,无形中将时间的内涵扩展延伸了,暗示出像这样地中宵不寐,思念远人已非一夕。同时,这三组词两两互文错举,后两组又句中自对,又使诗句具有一种回环流动的美。如果联系一开头的“远书”、“归梦”来体味,那么这“雨中寥落月中愁”的青苔、红树,似乎还可以让读者联想起相互远隔的双方“各在天一涯”默默相思的情景。风雨之夕,月明之夜,胸怀愁绪而寥落之情难以排遣,不禁令人满腹怅然,亦生怜惜之心。
全诗四句,表达了作者思念家乡亲人的感情。前两句写诗人得不到家人音书而产生归家之梦,以及中宵醒后寂寥凄寒的感受;后两句借助对“青苔”、“红树”以及“雨”景、“月”色的描写,营造出了冷寂、凄清的氛围,表达了悲愁,孤寂和思亲的情感。此诗借景抒情,格律工整,具有一种回环流动之美。
咏叹华清风景,抒发盛衰之感,唐人早有不少名篇。如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顶,舞破中原始下来’(《过华清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难乎为继的情况下,要后来居上,就得推陈出新,独辟蹊径。这首《题华清宫》便是如此,它取景深远,意味无穷,创造了独特的意境,表现了深沉的感慨。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两句,概括交代这一趟行程,“晓风残月”日夜兼行的氛围,也点出了凄迷的骊山景色,为历史悲剧的抒写作了铺垫。这是“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起句。接着,最精彩的两句出现了:“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从朝元阁到长杨宫,一方面由唐溯汉,拉开了时间的距离,广阔的历史背景令读者生深邃之感。另一方面,汉、唐并称盛世,而此时汉家宫苑、唐朝殿阁,都只成了笼罩于西风残月之下的荒凉陈迹。这两句一笔勾出千百年盛衰兴亡的历史,含蕴丰赡。
“都入长杨作雨声”,因残月在天,西风“作雨声”,则未必就是真的雨声。联想唐代诗僧毛可上人《秋寄从兄贾岛》中的佳句“听雨寒更彻,开门落叶深”,西风飒飒,落叶萧萧,令人疑为冷雨阵阵。写景之妙,正在于这种象外句巧妙运用所取得的幻觉效果。何况,“长杨”又是一语双关,既可指长杨宫,也可指树木中的长杨。末两句似乎也是幻觉的描写,引人遐想。“超以象外,得其圜中”,是司空图《诗品》指点人们写诗、读诗的一种方法。“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风声,雨声,总是秋声;声声入耳,一曲心声而已。历史的垂戒,凭吊的感喟,都融铸在这首诗的意象中了。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