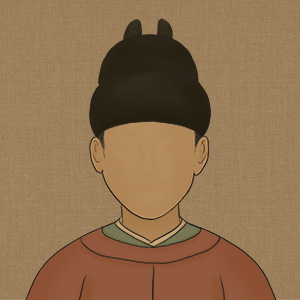虽稽具瞻意,欲全千仞高。
富贵一敝屣,功名两鸿毛。
独知退为乐,可怜夸者劳。
虽稽具瞻意,欲全千仞高。
富贵一敝屣,功名两鸿毛。
独知退为乐,可怜夸者劳。
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
上片先写夜景。“暮景萧萧雨霁”两句写玉宇在暮雨初霁之后的恬静、幽美和辽阔。“云淡天高”让人体味出阔大,而只有在静境中才会感觉到“风细’。前句的“萧萧雨霁”作为时间背景也烘托了后句的环境氛围。正是“萧萧”雨声之止才让人更鲜明地体察到“云淡天高风细”之景。下面三句紧承“暮景”二字,着力描写月色,“正月华如水。金波银汉,潋细无际”。夜空中,明月与银河交相辉映,波光闪闪,在这如水的月色中,天地如同浸入水中的玻璃世界。“月华”、“银汉”原本既是博大又壮丽的自然意象,词人在这里更以“潋细无际”四字来有意识地突出它们的浩瀚与无限。柳永是善于描写月色的,像流传千古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寒蝉凄切》),融情入景,在一弯残月中寄托了万种离情;而《倾杯乐·皓月初圆》一词又在“皓月初圆,暮云离散,分明月色如晴昼”中写尽了女主人公的离愁别恨。这首词则以如水的月光多方烘托词人的怀人之情。接下来,“冷浸书帷梦断”三句写词人因冷气侵入房中而从梦中醒来,披衣来到台阶上。这三句远承“风细”二字,由自然景物写及人的认为方式,以“冷浸书帷”来体现“风细”,并修饰“梦断”,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词人因难耐月夜的清冷之气,而从梦中醒来,其实不然,下面一句“披衣重起”的“重”字暗示了其中端倪。“重”是又一次,再次的意思,说明词人在这一夜中已不是第一次“梦断”而起。那么,词人为何一次次地从梦中醒来?不停打断他梦境的又是什么?
过片首句继续写景,“素光遥指”,但“遥”字已透出念远怀人之意。“因念翠蛾”三句道出了上片词人梦断重起的真正原因,所思的女子远在千里,音讯难通。一同沐浴着如水的月光,“杳隔音尘”的她显得若近若远,若即若离,这正契合了词人此刻思之而不得的惆怅。接下来一句“相望同千里”,远承“月华”,近承“素光”,从双方着笔,同望明月,借月传情。典出自谢庄《月赋》的“隔千里兮共明月”,又与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柳永不是苏轼,他是没有苏轼的旷达的,所以他“尽凝睇。厌厌无寐。渐晓雕阑独倚”,一直注视着夜空中的明月,孤独惆怅,难以入眠,天色将明,仍独倚雕阑,其内心的哀伤由此可见。
全词以明月为主线贯穿情思,虽叙相思,却逸怀超尘,语言清雅,乃柳永词中之佳作。
批判现实主义,从词牌开始就是在痛骂当权者,醉太平,粉饰太平罢了,社会矛盾如此尖锐,朝廷还纸醉金迷,难怪元朝90年就灭亡了。
堂堂的大元朝,一帮奸佞小人当权,从开河换取钱财开始就是祸害的根源,惹得红巾军造反,(红巾军好像是朱元璋参加的那支武装,后来做大了,就不多说了),法令又滥又重,弄得四海之内怨声载道。穷的人就差吃人,有钱人能更有钱,那朝那代有这种现状。官贼一体,苦到最后的还是老百姓。
通篇在控诉社会现实,但更有些像战斗檄文,号召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广大受苦群众去造反。
这首诗通过一对灾民夫妇推小车流浪情景,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悲惨的明末流民图,表现诗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这首诗采用新题乐府形式,以白描手法真实而简练地刻画了一对灾民夫妇形象,悲切凄惨,哀哀动人。
这首诗是作者导演的一幕饥民流离剧: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前台,已是薄暮时分,远远望去,从黄尘纷扬的路上,出现了杂沓而来的独轮车。全台静默,只听见车轮辘辘之音由远而近,终于有一辆来到了前台——分明是一对疲惫不堪的夫妇,女的在前拉扶车把,男的在后勉力推行,车上大抵是些锅盆、铺盖之类,自然还有几个面呈菜色的小儿女,这就是开篇三句展现的景象。“班班”叙小车之多,可知流离者非止一家。向“晚”而“黄尘”未歇,正是久旱不雨所造成的。寥寥几句,展示饥民流亡景象,宛然如在目前。
接着三句,可以视为这对夫妇的凄惶唱叹。“出门茫然何所之?”咏叹当日离家情状:瞻念前路,旱情茫茫,离家出走,又能逃往何处。“青青者榆挽吾饥”,叹息夙行夜宿,沿途竟无粒米进肚,只能采食榆叶充饥。榆叶椭圆而小,故能抵御久早。“愿得乐土共哺糜”,则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之语,讥刺统治者“重敛”,害得百姓纷纷逃亡,欲寻找一片“乐土”安居;二是汉乐府《东门行》,叙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铤而走险,妻子啼哭牵衣劝阻,有“他家但愿富贵,贱妻与君共哺糜”之语。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句,含蓄地指明:饥民之流离,岂止旱灾所致,更有统治者横征暴敛之故。若非如此,则家存蓄积,又何惧眼前之旱。而这对夫妇所企望的“乐土”,又不过是求得一点薄粥(糜)糊口而已,可见愿望之低微。
随着出现的,是一个“喜剧”式场景:“风吹黄蒿,望见坦堵,中有主人当饲汝。”蒿而称“黄”自然也干枯了,不过,它们大约长得较高,一度挡住了视线,恰好一阵晚风吹来,终于让这对夫妇“望见”,前方竟有一带院墙。此句一本作“风吹黄蒿见坦堵”,施蛰存先生以为“有一‘望’字较佳”,大约带有无意中望见的惊喜意味,更觉传神。
“中有主人当饲汝”,便是“望见坦堵”后的微妙对白:既是院墙,想必是村巷、人家。虽然他们也未必宽裕,但给口稀汤喂你,大约总不是奢望吧。一个“汝”字点明,说话者当是在前的妇人,而且从慈母心理上说,这“汝”亦应指车上颠簸已久、饥肠辘辘的小孩而言。全诗至此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连那台上的“灯光”,也仿佛柔和了起来。
“叩门无人室无釜”,则是整个剧情的转折。只是在舞台上,应该伴有一连串动作:先是夫妇奔到垣前,然后是怯生生地逐家“叩门”,但毫无反应;随手一推,门竞没有上栓,“吱呀”一声推开,夫妇俩踏进门槛左顾右盼,最后相顾愕然:偌大一个村巷,竟然空无一人。不仅空无一人,就连一个举炊做饭的釜锅也不存——显然他们也因绝粮,而家家户户逃亡了。这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却又意味深长。走到哪里,都是村巷空空,可见“饥民流离”状况很普遍。
幕布是在这对夫妇“踯躅空巷泪如雨”中落下的——他们携儿带女,从“黄尘”中挣扎而来;在“望见坦堵”的时刻,也曾萌发过一线希望;而今希望全已破灭,还能到哪里。村巷空寂无声,暮色中惟闻这对可怜夫妇的呜呜涕泣之音;作为回应的,只有那身处黄蒿中小儿女的惊惶呼唤。
这首诗,采用的是乐府民歌式的叙事体,这类叙事之作,大多篇制短小,结构却别具匠心,往往大刀阔斧删去背景,甚至也不交待来龙去脉,只截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断或一幕场景,以传神的人物对话和细节刻画,表现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
《小车行》是陈子龙自作的“新乐府”,从精神到手法,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于继承之中,又有创新:在表现一对夫妇的流离情状时,还注意勾勒“班班”众车的背景和氛围,这就起到了以一概百、以少见众的效果;在简略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景物描写和情节转折,便在短制中翻出了波澜;最后以“踯躅空巷泪如雨”收结,留不尽凄怆于诗外,又带有抒情诗的意味。